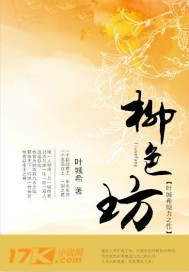天刚蒙蒙亮,皇太后的鸾凤殿便涌满了人,皆是今日要参加晋位之席的采女们。
十二人分为两番,六人一组,呈梯形座位排次,每关胜出者记一分,无出彩者不计分,未胜者扣一分,最后记满三分者则成功晋位。
说是商议着晋位的理由,不过是为了子珏不近女色之事填补缺漏罢了。
众人皆知子珏不近美色,那么这些采女,宫人,亦或是后妃则无从怀有子嗣。
既无子嗣,又无机会讨得子珏欢心,那何来机会晋位?
若是不晋位,此次轮回,每年一次的选秀,岂不是皆为采女?
若是如此,还有哪家官宦愿将女儿送出,来讨这一生的独自伤怀?
故太后设下此席,为的就是世人切莫因子珏的怪癖对这朝歌皇城,对这朝歌的君王产生诟病,继而动摇其君位。
要知道,一个君王可以无学识,不通晓军理,却不可不得民心。
若是失了民心,只怕无法继续在这龙椅上久留下去罢。
太后是子珏的亲生母亲,自是要为之将来好好思虑一番,尽管子珏已经称王,却也不可视前途渺茫才好,做母亲的自然要为自己的儿子铺好前路才是。
第一关:琴
各位采女根据自己所须乐器提前一天上报给决事司,将由那里的总管为其采办。
卿瑶递上去的则是筝,花离递上去的则是笛,从小看着旌尘吹笛,姿态调子也学了些皮毛,虽吹不出调子,但装个样子还是可以的。
再加上用法术随便糊弄出一支曲子,倒也轻便容易。
斐愔递上去的则是埙,倒是少见,不过斐愔这般性子的姑娘倒也不奇怪。
卿瑶花离还有斐愔刚好分为一组,还有其他的三位小姐,分别是琵琶,箫与鼓,六人共同合奏一曲《凉州词》。
卿瑶自是早有耳闻,只是花离和斐愔面面相觑,花离就不说了,斐愔自小不问闺房之品,自是不晓得,也不曾有兴趣。
二人只得和着卿瑶的调子,勉勉强强作出一些小调。
其它三位小姐倒是如鱼得水,分工明确,刚好也是住在同一座寝殿,乐器又不同,想来早已计划好,分工明确,简约明了。
卿瑶一人带动着两人的调子,十分紧张沉重,没办法,既然住着同一座寝殿那就必定要相互扶持,至少先不可内讧,早日将花离与斐愔两人的隔阂消去才好。
说来也巧,斐愔对笛倒是稍有研究,只不过是更加偏爱埙罢了,她知晓笛的姿态和指法,可这《凉州词》抑扬顿挫,清爽简单,再看看花离这般搔首弄姿的样子倒是极不搭调了。
也不知她是如何弄出这般声响,这叫斐愔着实好奇,况且这笛的气口和花离换气的地方可以说是驴唇不对马嘴,难道是自己的研究有了偏差?
但此时也容不得斐愔胡思乱想,胡乱猜忌,毕竟自己也是自身难保,还是先顾好眼下才是。
那其他三位小姐同样也是心怀鬼胎,觅出斐愔花离二人的破绽,便加快节奏,卿瑶一人倒还能勉强跟上,那花离和斐愔便如脱缰的野马一般难以控制手中的调子,紧跟着也打乱了卿瑶的节奏。
三人顿时大汗淋漓,不晓得如何挽回,这时有一位年少小儿从那鸾凤殿的大门处悄悄探出头来,拿出自己的一枚玉哨胡乱吹了起来,在卿瑶自乱阵脚的前一刻打乱了整个曲子的调子。
这下那三位小姐听不见彼此的节奏,也乱了起来,那《凉州词》瞬间乱成一锅粥。
六人连忙跪了下来,为自己的调子乱走而道歉求罚。
那公公也高声喊了起来:“是谁如此大胆无礼?竟扰了如此重要的比赛进制?”
“我!”那年少小儿蹦蹦跳跳举着哨子便跑了进来:“母亲,我这一曲《凉州词》可还动听?”
皇太后本来严肃的神情一下子慈祥了起来:“是乐儿啊!动听,自然是动听的,快坐。”
原来那年少小儿名作即墨乐,是即墨皇族最小的儿子。
“起来吧!”皇太后对那六位小姐说着:“此次琴之赛,因为乐儿打扰了众位美妙的乐音,已作平手,皆不记分。”
“谢太后。”虽然那三人觉得不公却也不好反驳。
即墨乐坐在皇太后的身边,稚气未脱的面庞着实可爱,却与这如同深渊般的皇城有些格格不入。
第二关:棋
此棋局名为“樗蒲”,“樗蒲”用的骰子共有五枚,称为“五木”,形状也很是奇怪,大致像银杏,中间呈方形,两头为尖多面体。每只骰子皆两面染黑、两面染白,有些黑面上还会雕个“犊”的图案,一些白面上则雕个“雉”的图案。这五枚银杏状骰子可以掷出十种排列组合计数。
“卢”:五木全黑,计为十六筹;
“雉”:两雉三黑,计为十四筹;
“犊”:两犊三白,计为十筹;
“白”:五木全白,计为八筹。
以上这四种称“贵彩”,下面还有六种杂彩:“开”“塞”“塔”“秃”“撅”“捣”。
玩樗蒲棋的时候,掷出贵彩的可以连着行棋、打掉对方的棋子自己过关。
不过行酒令的时候又不一样,一般是拿两套“五木”,也就是十枚骰子一起掷,按掷出的彩数决定喝酒多少。
由于大家都希望能掷出贵彩,一把出手、十枚骰子在盘碗里旋转不停的时候,大都会忍不住高喊“卢、卢、卢”或者“雉、雉、雉”,所以“呼卢喝雉”也就成了“樗蒲”甚至所有棋类游戏的代名词。
这种棋法倒是个新花样,多出入于民间的棋局,但这皇太后要考验的就是众位小姐临场应变能力。
这些小姐们不出意外的应是都不熟悉这种玩法,多数为围棋,五子棋之局,定是会慌了阵脚。
而皇太后要的则正是这临场发挥的能力。
十二人次,分为六组,两两对弈,由专业此棋局之人接手管理,监督查看。
在这一方面,卿瑶可是吃了亏,苏老爷从不许自己随意外出与他人进行博弈,更何况还是这种玩法。
但花离和斐愔二人不同,斐愔从小便时常偷偷与交好的侍卫一同钻研此类棋局,而花离又刚好被分为与斐愔一组,用法术照猫画虎则可轻而易举糊弄过去,哪怕不会赢,倒也不至于扣分。
第一组便是斐愔与花离,二人互不相让,花离则使用法术,跟着斐愔的步子走,她早就看出斐愔颇懂此等棋法,便依样画葫芦的紧随其步调出棋。
此时斐愔心中却仍然存有疑问,花离出棋之法表面杂乱无章,实则步步为营,以为花离也同样钻研其棋局章法,以为这就是花离自己的谋略。
其实不过是阴差阳错之下,用法术跟随斐愔的步子出了些小差错,这才营造出颇有城府的假象罢了。
而花离通过观察斐愔的神情与那焦头烂额,沉不住气的样子得知,自己这步棋走的是对的,便镇定自若地继续随着斐愔的步子。
最终利用斐愔难得的多疑赢了此棋局,而卿瑶的对手恰巧也不擅此种棋局,便双双平局,仅花离一人得到一分,可谁曾想到,花离连自己是如何赢得都不知晓。
乐儿却是发现了其中的端倪,看出花离并非简单之人,饶有兴趣的笑了笑,竟如当初颜凌认识小羽一般。
第三关:书
“书”则为书法,这对所有小姐包括花离都不在话下,自是大笔一挥,有撇有捺,一张纸上,便赫然一个大字苍劲有力地摆在那里。
花离也用法术巧妙地结合起了其它几位小姐字体的精华,写了一个旌尘的“尘”字。
而卿瑶的字则是别具一格,小巧玲珑,字迹娟秀,在偌大的纸上提上了一副《琵琶行》,更是出彩。
斐愔则犯了难,自己从未练过书法,那砚台上的墨汁更是弄得到处都是,大家闺秀之气顿时消散无疑。
此关最终只给花离与卿瑶记上一分,其它记为平局,斐愔则需扣掉一分。
第四关,也就是最后一关:画
十二人同时进行绘画,皆画自己心中所想之人。
许多小姐皆画了自己的父亲或是母亲,还有几个则画了素未谋面的皇帝,模样同子珏相差甚远,差点让乐儿笑出声来。
而斐愔则画了自己儿时的玩伴,卿瑶则画了旌尘。
可花离却画了一位身着藕色斗篷的公子,相貌堂堂,腰间还别着一枚白玉,身畔周围还飞舞着一只小蝴蝶。
卿瑶早早画完,因为旌尘的模样早已刻画在了自己的心中,提笔便可画出。
左看右看都看不出花离画上的人是旌尘,不禁感到疑惑:“她喜欢的不是萧落吗?这白面小生又是何人?”
其实此人就连花离也不识得是谁,但好像很早便见过,却又好像从未见过,但每逢忆起或在梦中遇见此人时心中都有别样的感触,或是幸运,或是不舍,或是惋惜,但却始终想不起他是何许人也罢了。
十二人站成一排,皆高举自己的画,浓墨重彩却又恰到好处,乐儿亲自下来点评,许给那些画自己父母的一分,又看了看那几个画了皇帝的,不禁问道:“你们又不曾见过我皇兄,怎知晓他如此俊朗?”
“王上之事迹我们早有耳闻,定当如此,不曾偏差。”那些画了皇帝的女子阿谀奉承着,着实让乐儿瞧不过眼。
乐儿转身又看向斐愔,点了点头,示意记上一分。
但却十分中意花离与卿瑶的这两幅水墨画,悄然展露笑颜。
斐愔本就落后,更何况刚才还扣了一分,当然咽不下这口气,于是辩驳着:“我们画的皆是父母玩伴,或是王上,到你这怎就画上了俊俏小生,已有心上人还入宫来,怕是有违规矩。”
还没等花离反驳,乐儿便帮着辩解:“诶?小姐如此说就不对了,谁人不知谁人不晓我大皇兄不近女色?此次纳妃不过就是走个过场,小姐莫不是当真了?有心上人又有何不可?切莫因为我大皇兄背上了个活寡妇的臭名才好,倒像是小姐这般可危险了,小心因为小姐让大皇兄背上了昏君的名号。”
“斐愔失言,还请三皇子恕罪。”斐愔知道自己言语有失分寸,连忙跪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