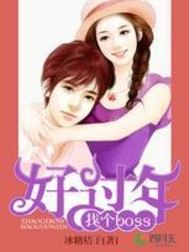很难想象,这个年代还有人会选择写信这种方式,更加没有办法让人相信,这种方式会出自凌峰之手。
回到家,按照警局那个小伙子给我的顺序,我展开了最上面的一封。
潘林子:
很难相信我会写信吧!写下这行字之前,我其实也不敢相信,但我的工作实在特殊,我没有办法去告诉你太多具体的事情,有一天如果你看到了这封信,那说明我的同事已经帮我整理好了遗物,并把它交给了你。
虽然早就决定了要与你分手,但这并不妨碍我继续爱你……
我坐在书桌旁,开着一盏台灯,在黑暗中点起了一盏光明,我看着凌峰写下的一笔一画,想象着他曾经带给我的点点滴滴,回忆,如潮水般向我袭来,其间夹杂着复杂的情感。
温暖、感激、愧疚、失落……各种味道随着视觉在字符上的掠过,狂魔乱舞。
好像厨房里有什么动静!
我放下手中的信纸,打算去厨房看看,我竟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危险的行为。
刚准备打开厨房的灯,我的耳朵开始剧烈地耳鸣,感觉有什么东西重重地砸在了我的头上,眼前的黑暗随即变得模糊起来。
我听到背后有脚步声,小心翼翼,但却又有些沉重,然后便人事不知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睁开了眼睛,发现自己躺在厨房门口的地板上,我的头很痛,甚至有些眩晕,仿佛这一切有一些虚幻。
我努力站起来,跌跌撞撞走到书桌旁,找到了我的手机,报了警,之后便半躺在沙发上等着警察上门。
晚上11点34分,警察来了,我把我的经历告诉了一个穿着警服,自称姓詹的中年男子,给我信件的小伙子向我投来了关切的眼神。
“林子姐,你没事吧?”
“头痛算不算有事?”
“你现在有力气四处看看吗?屋里子收拾得很干净,没有盗窃的痕迹,需要您再做最后一次确认。”
“信,那些信不见了。”
“你是说下午我给你的那些?”
“没错。”
我当时把信放在书桌上去了厨房,还用手机压在了上面,但手机还在,信却没有了。
“可对方拿那些信做什么?目测就是些情书罢了!”
我瞟了小伙子一眼,他连忙解释道,“对不起林子姐,因为前辈的身份特殊,大局着想,在詹老师的监督下,我快速看完了信里的内容,确保没有泄密,才通知您过来的。”
“你们这是侵犯公民隐私。”
“看来没有什么大碍了,不过待会儿还是要去医院看一下。”
说话的是詹警官。
“希望你可以理解,凌峰的工作特殊,同时也出了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必须对他的东西做严密调查,以免泄密。”
“那你们可以不用交给我呀!”
可能是头痛的关系吧,我觉得自己变得有些暴躁,胸闷得慌。
“他的事情已经有定论了,况且这些只是私人信件,我们没有权利隐瞒您。”
“定论?什么定论?我是他女朋友,他的安危,你们也没有权利隐瞒我。”
“是前女友吧!”
“哦,忘记了你们偷窥过我的信。”
詹警官尴尬地点点头,仿佛是默认了我的控诉,也可能是不想再跟我逞口舌之快,“他已经死了,我们尝试过很多种方式想要联系他在国外的母亲,可一直没有联系上,正好,如果你能联系上,辛苦你也给她转达一声。”
我总觉得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直到亲耳听到“死”这个尖锐的字眼,从一个衣冠楚楚,满身烟气的中年男人嘴里说出来。
我的眼前有些眩晕,胸闷地无法呼吸,胃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翻江倒海,喉咙一热,便吐了出来……送到医院才发现,是轻微的脑震荡。
“你叫什么名字?”
“李欢。”
接触了这么几次,还在我面前抹了一场眼泪,我竟在此时才知道小伙子的名字。
“我舅舅家小狗也叫李欢。”
“我想那条小狗一定长得贼帅。”
“谢谢你陪着我,不过我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你可以回去了。”
“那可不成,医生说了要观察至少一个小时,现在才过去了18分钟46秒。”
“我死不了。”
“我知道,但这是任务。”
“任务?”我突然一肚子火,“就是你们这些所谓的任务,害死了凌峰。”
“我原本以为前辈是个英雄,没想到,我也是才知道的,他背叛了组织,被我们的同事当场击毙。”
“这话听起来怎么比说他死了还不可信。”
“詹警官不会骗我。”
“也许你的詹警官也是被骗了。”
“那更不可能。”
“为什么?”
“谁会拿自己的命来骗人?莉莉姐回来了,是她开的枪,她也差点死了。”
“何莉莉回来了?你见到了她?”
“隔着玻璃见到了,受了伤,在ICU。”
凌峰背叛了组织,何莉莉开枪杀了自己的师傅凌峰?何莉莉明明就喜欢凌峰,师徒两个向来关系都不错,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些信,到底里面写了什么?”
李欢看着我,一脸疑惑的样子,“你没看?”
“还没来得及看,就被打晕了。”
“那可惜了,看上去是真的很爱你,连我这么个大男人都被感动了。”
“如果只是情书,为什么会被偷?”
“我从头到尾看过,詹警官也检查过,如果真有什么机密,肯定不可能交给你。”
“也对。”
“那只有一种可能。”
“什么?”
“偷信的人并没有看过信,以为里面写了什么。”
“除了你和詹警官,还有谁知道信的存在?”
“你的意思是……”
“你想呀,偷信的人以为信里写了什么,但首先得知道有这信的存在呀!”
李欢若有所思,然后拨通了电话,我猜他打给了詹警官,可能是怕我听到什么不该听到的消息吧,他拿着电话径直走出了病房的大门。
很明显,这个人一定就是警局的人,要不然哪里会那么巧,我下午才拿着信回来,晚上这信就被偷走了。
我隐隐觉得,整件事情并没有他们说的那么简单,甚至凌峰的死,也是疑点重重,因为我压根儿就不相信,一个对遵纪守法执着到连亲生父亲都可以不认的警察,怎么可能轻易作出背叛组织的行为。更别说企图杀死朝夕相处的同事,最后被同事反杀。
这一切怎么听都觉得是那么玄幻。
这天晚上我回到家已经是凌晨3点过了,李欢坚持要守在楼下确保我的安全,说这是詹警官的命令。
既然信里什么都没有,偷信的人必然知道我不是个威胁,因此便不会再加害于我,我不知道他们在担心什么,总觉得这个小伙子看上去稚嫩,心里却藏着很多事情。
这件事情之后,我便患上了多疑症,也不知道这算不算脑震荡的后遗症。
我总觉得有人在跟着我,放在家里的东西,也总觉得被人动过,为此,我给李欢打过电话,希望得到警方的帮助,詹警官和李欢都亲自过来过,也蹲守过几天,都没有什么发现,更没有出什么事,便陆续都撤了。
我以为自己脑子被打坏了,专门去医院挂了脑内科,医生却说我恢复得很好,让我百口莫辩。
贺菲带着影儿去了欧洲旅行,秋若一的公司在做IPO的最后一战,大家都各自忙着,我实在不忍心在麻烦了警察之后,又去给我的两个闺蜜添堵,想来想去,可能是最近事情发生得有点多,心里也压抑,便去了一个自认为可以缓解压抑的地方——监狱。
和许多其它城市一样,这座城市的监狱建在城外,山清水秀,空气清新,我见到了岳然。
监狱果然是一个足以让人改头换面的地方,明明就是个阳光大男孩,却已经被修炼得不修边幅,满脸沧桑。
一路上我一直在想,到底应该如何告诉岳然,凌峰去世的消息,即使此时此刻我发自内心并不相信他真的死了。我编了好多说辞,中国古代行文里的起承转合被我编的天衣无缝,但临到岳然面前,却一个字也修饰不出来。
“他死了。”
“谁?”
“凌峰,你的哥哥。”
“怎么死的?”
“说是背叛了组织,被同事击毙了。”
岳然不屑地笑了笑。
不知为何,我也笑了,于是我们两个就这样看着彼此,笑出了泪花。
“你要照顾好自己。”
“你知道我会的。”
“我,我哥,念叔,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你出事。”
“你是知道的吧?”
“知道什么?”
“这所有事情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
“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
我看着岳然,我知道他一定知道些什么,要不然面对凌峰死亡的消息,怎么可能会如此淡定,只是我不知道,到底是在哪个节骨眼儿上,岳然也加入到了这场巨大的阴谋当中。与此同时,我也知道他的心意,可能是出于保护吧,他,准确地说是他们,从一开始就打定了主意要瞒着我。
无所谓了,前路茫茫,我看不清楚,但只要他们清楚,我便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