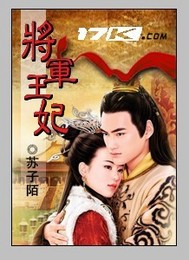如娇莺初啭般的声线传入耳畔,却叫林焱讶异地挑眉,稍一沉吟方才道:“你言下之意莫非是外头掌权者传召?”他顿了顿又即刻否定道:“萧贵妃掌六宫事宜,如今出了梁美人这一档子事儿已是忙得焦头烂额不可开交,如何有心思理会你?至于旁人,瞧你又是侍奉这宫闱中最无权无势无前程的主子,更是敬而远之。”
他全然一副不信薛海娘所言的模样,环着双臂轻倚着朱漆梁柱,似笑非笑地瞅着视线内笑靥如花的人儿。
薛海娘信步上前走至玩世不恭的少年跟前与他四目相对,黑曜石般的瞳仁倒是叫她脑海中浮现出另一双与之极为相似的眸,同是浓稠得如同化不开的墨一般,然,前者的浓稠中蕴着星辰烁闪眸华,而后者却是静如止水,难见波澜。
“清惠王殿下想来你亦是不陌生吧……实是不巧,上回萧贵妃诞辰上我与梁美人合力献艺,清惠王赞叹我指下的筝好似活了一般,丝竹之乐宛若天籁,而今难得入宫又恰巧与我轩阁会面,便知会我晚些时辰寻个空隙往他暂住的紫竹林陶然居去一趟,清惠王殿下天生贵胄,我自是不敢有所异议,忙完了轩阁的活计后便去了陶然居一趟……至于你方才口中所谓对梁美人忠心不忠心的,我实在疑惑,不知林焱你何出此言?”薛海娘转动着狐狸般狡黠而魅惑的眸,密而卷翘的双睫如蝉翼般随着翕动的唇上下扇动。
林焱略显怔忪,好似难以相信竟有如此善于圆谎的人儿,她以为将清惠王殿下搬出来便可化险为夷?
她便不怕事情有所败露?
清惠王虽说温和随性,可无论换做是谁,在如此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被拉出来成了旁人的挡箭牌,饶是再温雅之人也会愠怒,更枉论晦暗难测的清惠王。
林焱也不知因何缘故,竟是一腔愠怒涌上心头,剑眉微蹙,上前不留余力一把扣住人儿的纤细皓腕,也不理会人儿因这突如其来的钝痛拧起的黛眉。
他低沉醇厚的声线此时此刻蕴着滔天怒意,扣住薛海娘纤纤皓腕的指尖因用力过度而泛白,“你可知那南叔珂是何人。你以为瞧着他今日好说话了些,瞧着温和了些便是无害之人?你可知他昔年镇守边境时何等杀伐决断、狠辣残戾。你薛海娘于他而言便如区区蝼蚁般,稍稍一碾便回天乏术,你胆敢如此编排于他?”
钝痛自皓腕透过肌理传入四肢百骸,薛海娘痛得蹙眉,然艳若桃李的玉容却仍是笑靥如花,仰面与那施加钝痛之人四目相对,“何为编排?若林焱公子不信奴婢,大可现下随奴婢往陶然居去一趟。”
闻言反倒是林焱怔了怔。紧扣着佳人皓腕的指松了些,指节亦是不似原先那般因施力过度而泛白,他入鬓剑眉稍稍舒展了些,可眉宇间仍可见褶痕,“薛海娘,你莫要仗着我与殿下一而再再而三的容忍愈发肆无忌惮。”他狠狠地将佳人皓腕一甩,面上尽是不忿与嫌恶。
薛海娘原就因方才长跪厚积霜雪上,双膝酸楚异常,林焱又是习武之人,手劲原就比寻常人大上许多,如今他满腔愠怒又是狠狠一掷,薛海娘一时难以稳住身形,步伐微踉,若非脊背恰巧倚上雕栏,定是要狠狠摔在地上。
林焱原是打算将薛海娘甩开后便转身离去,却不曾想那看似称不上羸弱的人儿,竟是难得孱弱了一回。
视线自她苍白狼狈的玉容上往下扫视,随即敏锐地捕捉到她好似浸了水的斗篷,因是玄色,他起先还未察觉。
薄唇翕动,原是唇际的关怀之语却随即咽下,心下暗忖许是更深露重又因方才下雪沾上了雪花之故。
薛海娘敛下心神,揉了揉白腻如玉的皓腕上显而易见的淤青,莞尔笑道:“请恕奴婢对您口中,您与殿下的一忍再忍一无所知。”
林焱无意再与她多言,而薛海娘也实是瞧不透,藏匿在他瞳底深处的异样情绪,唯有怔然着目送着他转身离去。
拖着疲倦酸楚的身子回至西苑,褪下早已被霜雪浸湿的斗篷与外衫后,披上貂绒大氅,待身子暖了些许后,方才走至外室轻推门扉,正欲跨过门槛之时,眼角余光瞥见一侧极为显眼的藕色貂绒大氅,略微怔忪,她记着方才进来时尚且未曾瞧见这藕色貂绒大氅……
寻思片刻,心头便好似有答案隐隐浮现。
偌大轩阁,可女子却仅她一人,而她又并无这般娇嫩鲜艳的衣裳。
薛海娘上前将其拾起,掸了掸上头不存在的灰尘,轻抿的红唇勾起一抹浅笑。
简单洗浴一番,感觉到已然洗尽身上乏倦,薛海娘方才换上绸衣绸裤倚在热坑上,如此舒适时刻,薛海娘眼前却始终浮现着方才那极尽羞辱的一幕,挥之不去。
次日辰时一刻,薛海娘拿捏着时辰起身,洗漱换衣后便往膳房取了份例早膳端至主殿搁置好,临走时透过珠帘瞧见塌上纱幔仍是垂地,便蹑手蹑脚离去。
简单用过早膳后,薛海娘便按照昨晚想法前往乾坤宫请安。
乾坤宫历来皆由御前侍卫巡视,且守卫森严,乾坤宫外可见侍卫看守,乾坤宫内皆有内宫侍卫值班,再入主殿前尚且有乾坤宫侍人看守,若来人并非贵妃传召而来,必得由侍人入内殿通报,经贵妃允准方能入主殿请安。
薛海娘先是向乾坤宫外看守的侍卫道明身份,在瞧见意料之中的嫌恶眼色后,她仍是一再坚持求见萧贵妃,侍卫无法不得已才向内殿看守的侍人通报了一声。
结果,自是薛海娘意料之中的事儿。
那侍卫一脸诧异出来,道了声萧贵妃准她入殿参见,薛海娘方才福身道谢,款步入了内殿。
梁白柔遭禁足一事实在蹊跷,她若是想要晓得其中具体,也唯有进这乾坤宫,会上一会这执掌六宫、形同副后的贵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