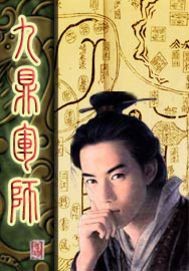天还没亮,大单于冒顿营里的胡兵都已钻出了帐篷,一队队胡兵生起了柴火,将串成串的羊肉架在火堆上烤。肉串上大滴大滴的羊油不时滴入火堆中,‘滋’地一声响后即化作一朵跳动的火焰,发出浓郁的羊膻味道。
南宫本能地意识到胡兵有行动,他摇摇昏昏发沉的脑袋,伸腿踢了踢还倦在地上睡觉的兵士,低声说道:“告诉兄弟们都精神些,胡子要动了。”果然稍后便有两个胡人提着木桶走过来,南宫不由问了一句:“是不是又要移营了?”那两个胡人瞪了他一眼,倒下桶中盛着的冷羊肉冷着脸扬长而去。南宫心中暗骂,伸手抓起一块羊肉,狠声说道:“兄弟们,吃他娘的。”
大单于冒顿已经周身结束停当,对站在身边的军师用汉话说道:“军师,本单于去了,两个时辰后你让右贤王领着他的万人队分成两翼随后接应,破虏军只有几千人,用他的万人队足够用了。”那军师低眉答应一声,却用胡话复述了一遍冒顿的命令,冒顿点点头带着卫兵大步出帐,那军师微微侧转头皱皱眉头后,嘴角处却显露出一丝阴笑来。
胡兵们已经吃饱喝足,见大单于出了营帐,两名千夫长大声喝令,顿时一阵人喊马嘶后,两千骑兵便已整装待发。冒顿仰身对着尚未逝去的一弯淡月,嘴中念念有词,稍顷后突然拨出腰中的弯刀对着胡兵们一声大喝,等两千名胡兵高喊着回应后,纵身跳上了战马。
荒原上巴根草的生命力令人惊叹不已,原本才刚刚吐出的一丝新芽,一场雨水过后,不到两天功夫就毕剥着拨出新节,盘根错节地铺成了大片的草甸,从里面不时冒出一两只野兔的脑袋,竖起耳朵警惕地四周张望。
离杜城东南五十里处有一个地势平缓的小山坡,坡顶上除了随处可见的巴根草,还伫立着五块光秃秃的大石,小山坡因此得名五石坡.
上午巳时刚过,五石坡往日的宁静被穿梭般一队队斥候打破,斥候中既有鑫军的,也有胡兵的。向来见面就要打起来的斥候们,今日却各司其职,互不干涉。坡顶是这一带的制高点,斥候们策马冲上坡顶,极目四望,能望及几里之外。
孙旭东带着胡校尉的两千破虏军已到了离五石坡不足十里之地,为了在胡子面前显示大鑫国的军威,上自破虏将军,下至骑甲兵士,无不都是衣甲鲜亮。只是临行前蔡轮对兵士们嘱咐了无数次,路上时请分外小心身上的衣甲,因为这身行头都是他从各营中好不容易才凑来的,弄皱巴了回去可不大好交差。
胡安丝托骑马紧跟在孙旭东身后,身上已换回了自己雪白的胡装,先前破损的地方已缝补好,浆洗得一尘不染。不时抬眼看一眼孙旭东的背影,让她感觉不到一点就要回家的兴奋,心里只希望这条回家的路永远都走不完。
头一次在荒原中看到大片的绿色原本让孙旭东有些新奇之感,不时回头望一眼胡安丝托,想起就要和她分手了心底不觉大是忧闷。忽然走在前面的毛怀猛地伸直了头颈,吸溜着鼻子像是嗅到了什么,转头满眼兴奋地对孙旭东说道:“大将军,有狼群!”
毛怀是荒原中的猎户,从小就对猎物有着天生的敏感。正在烦闷中的孙旭东闻听只想正好借着散散心,“胡校尉带着队,咱们杀狼去!”一把抢过边上亲兵背着的长弓和箭壶,两腿用劲一磕马蹬,跟着毛怀向左前方疾冲而去。
吸足了雨水的荒原还有些打滑,战马被紧催却也顾不得了,翻飞的马蹄将地上的泥土和草根撂得老高。孙旭东百忙中先背好箭壶,马缰绳系在马蹬上,两腿用劲夹住马腹,稳稳坐在马背上,左手持弓右手从箭壶中摸出了长箭。
下了一个土坎果然前面出现几个缓缓移动小黑点,毛怀经验丰富,转头大喊一声:“大将军,标下绕过去包抄!”即带马缰往左一带,孙旭东点头会意,右手长箭在马屁股上猛击一记,紧催战马径直向着黑点冲去。
七匹凶猛壮硕的荒原狼刚刚进行了一次小型聚餐,肚子还只吃得半饱,呲着牙正在四处搜索着能填满另半个胃的猎物。全身雪白的头狼最为精神,第一个发现了远处的动静,低嗥一声,几匹狼顿时跟着警觉,伫立不动抬着头望着疾冲而来的战马。片刻之后,头狼忽然长身跳起,嚎叫出极为凄厉的嗥声,竟像是百万军中的大将军发令一般,果然身前三匹荒原狼闻声跟着短促地低嗥了一声,小跑着迎向战马。
眼着的黑点越来越大,慢慢变成了三只荒原狼。孙旭东坐直身子,右手长箭搭在弓弦之上,嘴中却继续呼喝着催马向前。
三只狼开始加速,从四脚逐一离地的小跑开始两腿同时离地的纵跃,它们是经验最丰富的荒原猎手,知道在什么时候应该用力,什么时候应该冲刺,才能发挥出最后的致命一扑。
不到一百二十步的距离上,孙旭东两脚踏牢马蹬,侧身在马背上站起,张开了长大的步弓,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动作,除了足够的臂力还要很高的身量才能办得到。当眼前跳跃着冲击的狼跃起的一瞬间,孙旭东右手手猛然松开,被紧绷着的弓弦一声长呤,将锋利的长箭闪电般送进了刚刚跃起的狼头!
剩下两只狼见同伴哀号着摔倒,最右边的一只狼竟稍有迟疑,但中间的一只灰狼却更加勇猛,张嘴翻唇露出尖尖的獠牙,尖号着继续向前。
右手向身后划过一道弧线,孙旭东迅即在箭壶中摸出了第二枝长箭,大吼一声,步弓再次张开,瞄准了中间奋勇向前的灰狼,稳稳松开了右手。不到八十步的距离上步弓的杀伤力是惊人的,两面开刃的箭簇带着箭杆从灰狼的颈下钻入,直没至箭羽。
两只狼的惨叫声让右边那只狼的意志彻底崩溃了,它不再迟疑,向右掉转方向将在后面掌握平衡的尾巴紧紧夹起,极坚定地一溜烟似的逃了开去。
雪白的头狼怒不可遏,再次伸直颈发出嗥叫,两只前爪在地上挠了几把后,硕大的身躯像离弦之箭般往前冲出,身后三只母狼同时对头狼的勇敢引吭高歌,只是歌声未歇,一支长箭疾飞而至,从叫得最响的一只母狼的头颈处洞穿,正是毛怀抄到了土坎之后。
孙旭东两箭射倒两狼,胸中豪气大生,张嘴长叫。眼见冲来的这只狼浑身雪白,真是平生仅见,孙旭东不由大是兴奋,右手一带马缰绳,想让跑歪的战马迎向疾冲而来的白色头狼,战马一声忽律律长啸,两只前蹄向左踏出,后腿刚刚抬起,落地的两只前蹄却被湿泥滑倒,偌大的马身顿时倒向一边,将正站在马上高叫的破虏将军狠狠地摔在了一个土窝子里。
孙旭东被摔了个措手不及,左手长弓拿捏不住被甩在了一边,慌乱之中只得扭身以腰臀着地,只觉勃颈中颈椎骨炒豆般连响,头颈立时僵住。幸好身下土窝子里有厚厚的巴根草甸,虽被摔得身冒金星却未伤了筋骨。
那头狼正在疾冲中,眼前发生的一切竟令它一时不知所措,先是对着倒地的战马冲击,忽然扭转身向倒在地上的孙旭东扑来,片刻之后凌空跃起,开张血红的尖嘴咬向猎物的脖颈。
孙旭东大惊失色,壮硕的头狼足足超过两百斤,真要被它扑倒再难翻身。顾不得脖颈间的刺痛,拚死力向边上滚了几滚,电光火石间堪堪躲过头狼的一扑,一身借来的将军服色却已全是泥花,狼狈不堪。
头狼灵动之极,一扑不中迅即转身,嗥叫一声,对着正想坐起的猎物再次凌空扑出。孙旭东不禁心中大骂毛怀,此番却再也无力滚出,两肩被头狼扑住向后倒地,紧接着鼻中只闻得一股腥气,头狼血红的舌头已伸到了眼前。孙旭东奋力伸出左手,死死抓住头狼下腭的皮毛,入手处只觉光滑之极,急忙翻转手指关节紧紧顶在头狼咽喉之中。
头狼发出低沉的呜咽声,舌头上腥臭的口水直滴在孙旭东脸上,孙旭东此时情急拚命,只扭动头脸让双眼避开,扭动中眼睛却已瞟见从箭壶中四下散落的长箭,但此刻右手被身子压住无法得出,只得左手手指关节拚命向上顶出,一心只想让头狼喘不过气。相持片刻后,孙旭东只觉那狼劲力大得出奇,比先前在前山杀死的那只狼要力大得多。他咬紧牙关,忍着钻心般的疼痛,使出吃奶的力气将左手指骨向狼下鄂骨顶去,头狼大概被顶得难受,抖动着头颈稍一收劲,孙旭东只觉身上一轻,右手迅捷握住一支长箭,抬手**头狼口中。
头狼嘴中鲜血如注,吃痛不过开始拚命向后缩身。这回孙旭东抓住它下颚的左手不再用力外顶,却死死往回拉,大口喘着粗气,任凭腥味极重的狼血淋个满头满脸,右手用尽力气将长箭一寸寸往头狼嘴里伸。头狼用尽全身力气不住挣扎,两只后腿在地上跳起,抽搐着蹬在孙旭东的下半身上,尖利的狼爪将他的马裤划得稀烂。
耳边终于有了一阵杂乱的马蹄声,快到尽前时孙旭东右手的长箭已被他**了大半,那头狼已只剩抽搐,嘴里的血也尽流光。孙旭东大叫一声,两手一齐用力,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将头狼推向一边。
“将军大人!”原来是胡校尉有些不放心,还着几名亲兵过来看看,先前只因一人一狼倒在土窝子里他们并没有发现,只是看见孙旭东那匹已站起的战马才跑了过来。扭头见倒在地上血人一般的孙旭东,不由大惊,几人跳下马,疯了一般飞跑过来。
孙旭东大喘着气,用力地答应了一声。“将军大人,没事吧?”胡校尉不及喘气,上来一把抱住满身是血的孙旭东,孙旭东坐起来猛喘了几口气,摸了一把脸上的血,不禁心有余悸:“奶奶的,这只狼真够狠的,快,快,你们赶快去看看毛怀,他那儿还有三只呢。”胡校尉转声下令亲兵赶紧去土坎子那边看看,自己却仍是搂着孙旭东不放。
毛怀也是吃了战马的亏,一箭射倒一只母狼后,正打算再次开弓,那战马却被扑上来的两只狼惊了,只是不肯上前不停在原地打转,毛怀破口大骂,等跳下马时两只狼已到身前,只得丢了弓箭抽前腰间的铜剑以一博二,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将两只已怀有狼崽的母狼杀死。
毛怀跟着胡校尉的亲兵到了孙旭东身边,他看了一眼倒在地上的白色头狼大吃了一惊,丢了大将军不顾,蹲在那只狼边又是摸又是看,半晌后才大声说道:“大将军,你杀死的这只狼是银狐狼,这。。这。。这可太好了。”
孙旭东故作镇定地哈哈一笑,“本将军当年曾空手力屠四狼,这几鸟狼算个啥?”嘴中吹些大气,心底还是有些心虚,他知道,方才如果不是万幸一把就抓住了那枝长箭,自己这会儿已不能说话了。
“不是,大将军误会了。”毛怀一脸惊喜之色大声说道:“银狐狼极少,标下在荒原中从来都没见过,只是听人说起过,银狐狼在狼群中一定是头狼,最是凶猛,胡人称为狼王。听老人们胡人见了银狐狼要先膜拜再猎杀,在胡人中除了月亮神,就是能猎杀银狐狼的勇士是最受敬重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