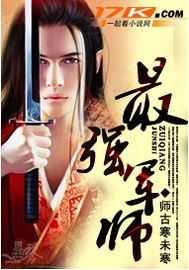伯齐听完孙旭东的禀报,两眼呆直,喉结动了动却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木然接过孙旭东双手呈上的一小方白丝绢,只见上面写着:营地已露,鑫军夜袭,速移。未尾虽然没有署名,但蚕头燕尾,一笔端庄的小隶书正是和余的笔迹。伯齐只觉天旋地转,一时被人欺骗、被人玩弄、被人利用诸般感觉齐袭而至,让他这个向来自视甚高的鑫国太子只觉心中要炸开一般,强忍着腰间的酸痛,猛然站起身,双手发疯般撕扯那方小绢,嘴中语无伦次:“是猪,是狗,不,都不是,是猪狗不如,天哪,你怎么会生出这种披着人皮的畜牲来?”
在身边和自己亲近了十几年的人竟然是奸细,这种强烈的反差孙旭东虽然没有经历过,但可以想像到伯齐此时的感觉,是以只是静坐看着伯齐发泄。门外守护的侍卫听见动静刚刚伸进头,被伯齐炸雷般的一声“滚出去!”,吓得白着脸缩了回去。
那方小绢甚是结实,任凭暴怒的伯齐左撕右扯仍是完好如初,白底黑字刺激得他更加恼怒,嘴中一边怒骂,一边两手将丝绢一把团起,扬手想掼在地上时,自己却咕咚一声栽倒在地。
孙旭东大惊,连忙招呼门外的侍卫将伯齐抬上卧榻,见他脸色灰败,已不省人事,急忙伸出拇指掐住他鼻下的人中,吩咐侍卫赶紧去找郎中。
伯齐嘴巴大张喘着粗气,孙旭东斜坐在卧榻边握着他稍稍有些发抖的手,忽然心中一动,趴下身去看伯齐的大张着的嘴。
不到一刻功夫,那位尖嘴猴腮,杜城排名第二的郎中背着诊箱急急进了卧房,郎中路上便已闻知此番要救的是太子,心中激动不已。在孙旭东连声催促下,看了一眼躺倒的伯齐后便抖索着打开诊箱,取出一支近两寸长的银针,趴在伯齐身上取穴。
也不知是因为紧张还是一路急跑的缘故,那郎中左手掐住了伯齐的穴道,握针的右手却颤抖着不听使唤,针尖来回晃动半晌只是不敢下针。孙旭东大急,这种中风症候救晚了不死也得瘫,不禁连声催促。那郎中头上也见了汗,就见他忽然丢了手上的银针,身子坐正,闭上眼睛后抬手狠狠抽了自己一个耳括子,急急睁开眼重新取了针,这回竟真有如神助,左手一经掐住穴道,右手银针随即刺入,动作迅捷之至且方位不差豪分,片刻之间就在伯齐脸上下了十几针。一边看呆了的孙旭东松了一口气,看了一眼郎中脸上清淅的五指印,心中险些失笑,这郎中镇静之法倒也奇特。
郎中缩着肩膀右手两根手指握住刺入伯齐人中穴位的银针针尾,手指不住捻动,两只小眯眼发出贼亮的光紧盯着伯齐的脸,移时过后就见伯齐脸上渗出一丝血色,鼻中长哼一声后眼皮一跳徐徐张开了双眼,郎中出手如风,迅即就将伯齐脸上的银针一一取下,满脸得意之色瞟了一眼孙旭东。
“太子爷。”孙旭东上前一步,见伯齐形容惨淡,两眼中原本神采奕奕的眼神不再,心中实有些出乎意料,没想到和余之事给伯齐带来的打击如此之大。
伯齐苦笑一声,轻声说道:“君武,伯齐失态了。”伯齐没有使用本太子,而是自呼其名,让孙旭东颇有受宠若惊之感,在一个礼法高于一切的时代,这种转变只能是表明伯齐已将他真正视为心腹之人。激动之余,更觉旷司虞言之有理。
“太子爷只是急怒攻心,一时昏厥,并无大碍。小人开个方子取了药便送过来,保管您无事。”郎中见伯齐能开口说话,心中不禁沾沾自喜:老子虽非王医,却救过太子爷。这杜城第一的金字招牌谁再敢跟老子争?只是回去之后是用红木做块牌子还是用楠木呢?
“有劳郎中先生了。今日本太子昏厥之事,还望郎中先生守口如瓶,不知可否?”伯齐确实并无大碍,在孙旭东搀扶下已坐起了身,眼望着郎中问道。孙旭东知道伯齐虽贵为鑫国王储,但四周政敌环伺,危机四伏,真实情形是如履薄冰。王储的身体好坏向来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伯齐如此小心并不过份。
伯齐的话却将郎中心中的金字招牌砸得粉碎,郎中虽是大失所望并不敢多嘴,答了一句颇为有名的“打死都不说”后跪着磕了几个头辞了出去。伯齐自己坐正了身子,心中平静了许多,看了一眼孙旭东后道:“君武大概在想,伯齐真不济声,竟被小小一个和余弄得昏厥倒地。”
“标下不敢,那和余坏了太子爷许多大事,确实可恨。现在想来,标下初赴杜城时,消息肯定也是和余透漏给胡子的,差点就让破虏军全军覆没。”
“嗯。和余可恨不光是坏事,想我伯齐对和余比世子都要亲近,自觉对他知根知底,事事寄以心腹。嘿嘿,没成想他竟然是个。。。是个。。唉!”伯齐说到此,心火又起,却一时找不到解恨的词来骂,闭着眼长叹了一声,稍顷过后,眼角中沁出两滴清泪。孙旭东这时才知道,对伯齐来说,和余的可恨不光是吃里扒外当奸细,更为可恨的是,和余不但将向来自负有知人之明的伯齐打倒在地,还踏上了一只臭脚。
“君武,和余既是奸细,上回你夜袭马陵峡,他为何不报与胡子?”伯齐睁开眼,稍带疑惑地问道。孙旭东微微一笑道:“标下开始有些怀疑和余时,就是被此事迷惑。”
“哦,那你从头说说看,是如何疑到他头上的。”
“是。最初神机营兵士毛怀向标下提起说,太子爷的营中不知为何养了不少猎狗,标下便令兵士打听,才知您营中养狗不过是作猎獾配药之用,便未放在心上。直至那日太子爷您问我军中送信用用信鸽之事,和余在边上听标下回话时,标下却发现他面有愕然之色。”
“嗯,嗯。”伯齐眼中一时精光大盛,插言道:“我记得你当时回说是鸽子、狗一类的性畜只要训练得好了,便可做些送信、寻物之事。”
“正是。和余自己就是训狗之人,标下说的他自然知道,却为何要假装不知且面露愕然之色?标下心下便有些起疑。现在想来,和余自己就是用狗来送信,是心中有鬼之人,忽然有人在您面前提到狗能送信,自是有些猝不及防,便有些慌乱之色。”
“嗯。”伯齐皱眉点头深以为然:“那畜牲只怕是以为你在试探与他,难怪总在我面前说你的坏话,大概他也自知你有所觉察,是以先用言语离间你我。”
“太子爷所言极是。那日出城修道奴工被胡子所掳,标下和太子爷在我营中密议,当时标下曾问到过和余,却引得太子爷不快。”伯齐一听此言不由大是尴尬,抬眼见孙旭东满脸肃然,并无取笑之意,便苦笑道:“伯齐向来自视甚高,那日做了有眼无珠之事,还替那畜牲说理,惭愧呀!”
孙旭东一直是按着自己的思路在说,听了伯齐的话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话让伯齐有些难堪,忙拱手道:“太子爷不要自责,和余心思缜密、手段阴狠标下也领教过,实非常人能猜度得出。”
“是啊,天不长眼,竟生出这畜牲来。”伯齐恨恨不已,咬牙说道:“那时你就知是和余在捣鬼么?”
孙旭东摇摇头:“也是标下愚钝,当时太子爷言语间对和余呵护有加,标下就是疑心他也只能放到一边,况且还夹着很难说得通的马陵峡夜袭之事。那日送走太子后,标下心中烦闷便想到神机营去看看正在养伤的营监,正好听得毛怀在里面说起在集市上杀狗之事,标下忽觉豁然开朗,将前后之事连将起来,方才窥清了和余的阴谋。”
“哦?怎么说?”伯齐对中间的事却一时还难以理得开,饶有兴味地问道。
“和余和胡兵之间一直用狗来互通消息。那日标下和毛怀在集市之上,将和余用作送信的狗一古脑儿全杀了。当晚标下和太子爷商议之时,和余虽在,却一时找不着替用之物,这才使得三日之后夜袭马陵峡的消息无法送出。太子爷,马陵峡一仗实是胜得侥幸啊。”
“这个不对吧,我记得我们商议三日后才袭的马陵峡,这中间既有如此重大军情,和余为何不亲自送出消息?”
“胡兵在大荒原之上,几乎每日都会迁营,从不在一地久驻,是以即便是和余,也不知胡兵哪日会驻在何地,就是想送出消息也不知往何处去。狗这东西极具灵性,且有一样特别的本领,即是鼻子灵敏之极,靠着气味便能找到应去之地。因此与和余通消息的胡兵,迁营之时只需沿途留下有气味之物,狗便能找得到。”
“哦。”伯齐长哦一声,恍然大悟,冷哼了一声却苦笑着说道:“难怪那畜牲每日里让几只狗吃得比兵士都强,原来有此大用。”
“正是。太子爷,标下还有两事要请太子爷恕罪。”
“哦?君武无须顾忌,但说不妨。”伯齐得知了事情的真相,反而立即平静下来。此时对孙旭东很是有些佩服,看哪儿都觉得舒服,一挥手大方地说道。
“多谢太子爷。第一件是今早标下所称神机营兵士报回胡子大单于驻地乃是标下妄言,实为引蛇出洞之计。未能先与太子爷商议,还请太子爷恕罪。”
伯齐闻言一怔,谎报军情实是大罪,但一转念破虏将军如此做,只怕也是因为自己始终在庇护着和余,万般无奈之下才出此下策。微笑着说道:“虽是谎报军情,却也立下大功,这事尽可不提了。还有一件是何事?”
“和余被制自撞剑尖而死,以致此事颇难善后,标下也是难辞其究。”
“哦,以君武看来,和余如是没死,此事该如何善后?”
“自当让他供出幕后主使之人,另外还需挖出他手下的同党。”
伯齐看了孙旭东一眼,缓缓说道:“君武,和余死得极是该当,若是此时还活着,那我们才真是难以收场啊。”看着孙旭东愕然,伯齐却不理会,高声叫来门卫守护的侍卫道:“本太子和君武将军有要事相商,传令,屋中所有人等,包括你们一律退出去,不得招呼不得入内。”
孙旭东一看这阵式,只当是伯齐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对手下人变得十分戒备了。却只见伯齐面带狰狞,咬牙低声说道:“今日下午,我便下令所有侍卫到你营中,只说是习练三日弓箭。待起更时,你亲带亲信之人将他们嘴全都堵上,绑出城后挖坑埋了。此事做得机密些,听清了?”
孙旭东闻言大吃一惊,伯齐不加讯问便集体活埋,上百名侍卫中间肯定会有人被冤杀,这可有些法西斯的味道。望着伯齐满脸的杀气,孙旭东一时不知如何作答,心乱如麻、矛盾之极。伯齐心中暗哼了一声:虽是智勇双全,只是火候还是稚嫩了些,还须得多经历些风浪。于是叹口气说道:“君武,凡做大事者不可拘小节,妄行妇人之仁,必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这个你要记住了。”
孙旭东低头思忖,伯齐所说不无道理,和余手下侍卫中肯定有他的同党,但和余已死,有谁会主动出来承认自己就是和余的同党?既是无法甄别得清,不如一锅烩了干净。可是真要自己亲手坑杀这百余名侍卫,孙旭东却大觉不安,因为他相信百名侍卫中应该大多数都是辜的。正是犹豫不决,忽然想起方才在伯齐嘴中看到的金牙。抬头望望伯齐,只见他满脸都是殷切,终于狠下心,咬着牙点点头。
伯齐一直紧盯着他,见状心中大慰,心中默念着和余临死前说过自己太子当不长的话,稍顷过后才说道:“至于幕后之人,不追也罢。君武,现下我跟你说了你也不懂,许多东西只可意会却不可言传,等时日久了你便会自知。好了,和余之事就不要再提了,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一去,我军势必不会再如先前那般处处被动,君武,你可有什么打算?”
孙旭东对未能生擒住和余确实惴惴不安,更不能理解伯齐为什么一反除恶务尽的常理,而不追究主使和余之人。尤其听伯齐方才话中之意,竟像是死和余比活和余更强,实是有些不可思议。但伯齐既然说了日后自知,就算心中存着老大的疑惑却不好多说。孙旭东刚刚见识了伯齐行事狠辣,原来想禀报胡安丝托之事不免变得有些犹豫,转念胡安丝托毕竟牵涉到军国大事,迟疑再三后还是和盘托出。
原来以为伯齐闻之会喜出望外,他从政几十年,不可能不知道像胡安丝托这种身份的重量。但大出孙旭东意料的是,伯齐闻听后只是淡淡一笑,恬淡地说道:“这月明公主可以有大用啊,起码可以保我大鑫十年没有边患。”
伯齐如此小看胡安丝托,不禁让孙旭东心中有气:只保十年,伯齐未免太小家子气。肃然说道:“太子爷如依标下所言,标下可让月明公主保我大鑫永无边患!”
********************************************************************************************************************************************
夕阳西下,血红色的阳光照在杜城城楼上,让冰冷的青灰色城楼变得很有几分暖意。城墙上正带着兵士巡哨的副将黄震走到垛口前伸头眺望,一阵风沙吹过,黄震眯了两眼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再次睁大眼时,就见远处有马队掀起阵阵尘土,连忙令亲兵道:“传令,先拉起吊桥,前方像是有胡子骑兵活动,待看清了再关上城门。”
来的约莫是胡兵的一个百人队,黄震见胡兵人数少,没有下令关闭城门,只是戒备着防止后面还有大队胡兵。百人队在鑫军长弓射程外驻马停了下来,就见中有两名胡兵摘下背上的长弓,对着城墙上拉弓搭箭,鑫军兵士领教过胡兵的箭法,急忙将头缩在垛口下,只用一只眼瞟着胡兵的动静。稍顷过后,就听长箭破空之声骤响,随即城楼上粗大的木柱被两支长箭猛然射入,长箭余劲未衰,箭杆急剧抖动,发出嗡嗡的声响。近处的鑫兵不由咋舌,距离已过百步,胡兵长箭余势还能如此劲道十足,确实令人佩服。转头再看胡子的百人队,已拨转马头风一般地向荒原冲去,翻飞的马蹄掀起漫天尘土,片刻之后待灰尘散去,百人队已是全无踪影。
“呸。”黄震喑骂一声,胡子真是来无影去无踪。兵士们已拨出了木柱上的长箭,却见两支乌木制成的箭杆上都包着一块绢,兵士们急忙取下交给了黄震。胡子还会来这一套?黄震接过一看,只见是两个用青绢做成的书封,上书着几个汉字,呈:鑫国太子伯齐谨启。一笔遒劲的隶书极有精神。
事情的真相事情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