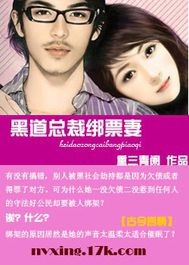见王剪斗然间像是换了一个人,孙旭东心下大慰。他虽然知道是和余在设套,但并不知内情,也是在胡乱猜测,此时心中便有隐隐不安,自己没有先会会那位名叫茯芹的女子,不光是虑事不周,还透着对生死兄弟的漠不关心。这时自责已是无用,当务之急是要稳住王剪,两眼紧盯沉声说道:“王剪,再到中军帐先将口供翻转来,然后慢慢照实说就行,再拖得个把时辰,本将军就可救你。”
转过弯的王剪神情已是大异,点头答道:“标下明白。”
“嗯,这才真是好兄弟。只等此事一过,咱们弄清了情由,本将军自会替你作主。”孙旭东许了一个颇为含糊的愿,王剪却是先入为主,只当大将军要替他和茯芹的事儿作主,咧开大嘴道:“多谢将军大人。”
两人出了帐篷,孙旭东皱着眉头对旷校尉说道:“司虞,这和余阴一句阳一句,要杀王剪只往太子头上推,我心下真有些吃不准,莫不真是太子爷的意思?”
“非也,太子爷真要杀王剪等不到这会儿。和余这是在借此离间你和太子爷,不用介怀。”旷久历世事,经验比之孙旭东丰富许多,一眼就看穿着和余的鬼把戏。孙旭道闻声点点头:“我也觉得太子爷好像对王剪之事并不在心,只是这和余在其间捣鬼。司虞,还有一事,咱们今日要捉的鱼估摸着此时才出城,等小轮子他们得手最快也得个把时辰。呆会和余回来见王剪翻供,必定要找酒店掌柜和那女子对质。烦劳你亲自跑一躺,将他们两人不拘哪里藏匿起来,让他找人不着就行。”
“嗯,我看不会吧,只要王剪死不认帐,就是和余找人来对质,拖个个把时辰也不是难事啊。这当口要是被和余的人发现了又要多事了。”
“不是,王剪才从坑里面爬上来,我是怕他突然见了那女子,心神大乱又着了道儿。和余嘛,高兴不了多少时候了。”
旷一生从未经历过男女之事,闻言大是不解。此时时间仓促孙旭东也不便作过多解释,重叹了一口气说道:“司虞快去,别看咱们好不容易才劝说住了王剪,那叫茯芹的女子若是真要害他,对质时说不定几个眼神就会让王剪重新跳回坑里去。”
旷听着不禁头大,不就是自己见过的一个弱小女子么?会有这么大的法力。不过见孙旭东煞有介事的样子知道不是玩笑,点头道:“好,既如此,我将他们两人带到我营中便是。”说罢转身带着人急急出了中营而去。
和余的手下乘着孙旭东外出,几人逢着头正在低声商议,见孙旭东大步进了帐,内中一名侍卫拱手道:“将军大人,那王屯长被带去多时了,想必水也喝了,是否请大将军下令,还将人犯押到大帐中来?”孙旭东瞟了他们一眼,脸上满是惊诧神情:“莫非你们信不过本将军,只当本将军要包庇本营军官?”
“这个标下们不敢,只是人犯带去久了未免有些不便。”那侍卫见他倒打一扒,心中暗骂,但此时在人矮檐下只得低头。
“哼,不敢只怕是未必吧,只要看你们的情形就知你们言不由衷啊。呵呵,方才你们和校尉不是说了吗?我破虏军的军纪可是你们校尉大人平生仅见哪,哈哈哈哈”此时形势逆转,孙旭东不由有些得意,先拿和余手下的小角色出出方才胸中憋闷之气。“你们也不用嘀咕,来人,带几位侍卫大人到神机营去将王屯长带到大帐来。”
和余亲自出马将一众人送出了城,脚不粘地地立即赶回了破虏军中营。进了中军帐见人都在,正想将悬在心中的石头落地,却见自己的手下正一个个朝他挤眉弄眼,立时情知有变。他是胸有城府之人并不动声色,嘿嘿一笑坐了下来:“将军大人久候了。我看,咱们也不用多审了,这就请将军大人下令行刑吧,标下还急着赶回去侍候太子爷呢。”
“为我破虏军之事,耽误校尉大人了。”孙旭东微微一笑,转头问台下跪着的王剪道:“王剪,你强入民宅,奸**女可是实情啊?”
“标下所犯是实情。只是标下另了隐情要报。”
不用听王剪所说,只须看王剪的神情和余就知已作了手脚,心中大是恼怒,回头狠狠盯了一眼手下人,几人见了他刀子一般阴狠的目光,局促着低下头。
“哦,既然另有隐情,你如实说来。”见王剪已复常态,孙旭东放下了心,打足官腔将声音慢慢拖得极长。
“是。标下并非是强入民宅,那晚实是茯芹妹子叫住标下后一同入的酒店。。。。”
原来是要翻供!和余心中冷笑不已,老子做成的铁案还能让你们轻易翻了供?听王剪和孙旭东两人翻来覆去像是演双璜,只是说那女子乃是自愿,并非王剪用强,心中大为光火,不等王剪说完,冷冷插言道:“将军大人,人犯既要翻供,也不能听他一面之辞。依标下看这王剪确实是个无耻小人,方才众目睽睽之下自认死罪,不过一刻的功夫又说是人家自愿,如此反复小人所言实不足信。”
和余说话时两眼紧盯着孙旭东,气急败坏的表情坦露无疑,尤其说无耻小人时的语气明明就是指桑骂槐。大帐中形势大变,稍有头脑之人就可看出来,帐中破虏军兵士无不喜动颜色,闷着葫芦嘴儿偷笑,先前那份担忧和紧张自是一扫而光。只王剪被和余骂作无耻小人,心中大怒,抬着头对他怒目而视,如不是孙旭东目光阻止,早已破口大骂。
孙旭东此时心中大是高兴,对着和余笑吟吟地问道:“那依着校尉大人,该当如何啊?”
和余冷笑一声:“当然是找苦主和那晚抓住王剪的桑都尉来对质,是自愿是强奸,让他们当面撕捋清白不就成了?”
孙旭东抱定了一个拖字诀,按估摸的时间蔡轮得手应该快了,再说旷校尉已去了多时,此时不再担心:“和校尉所言极是,王剪,本将军这就派人去将苦主找来与你对质,你可要想好了,狡辩抵赖可是要罪加一等。”
王剪听说要去找茯芹脸色竟为之一变,孙旭东说话时两眼一直紧盯着他,见了不禁暗暗将自己夸了一通:幸亏让司虞藏了他们,真来了不知这愣小子还会怎么样。
“来人,你们到杜记酒店去将杜掌柜和那名女子带来。哦,和余校尉,你看是不是要派两个人跟着一起去呀?”和余原本见孙旭东有恃无恐、神定气闲的模样,心中起疑:难道这么一刻功夫,他们连杜老儿的手脚也做了?听了孙旭东的问话后才定下心来,撇着嘴冷笑道:“杜掌柜此刻如还在杜记酒店,只怕早就让人害了。来人,你们带着破虏军的兄弟们一起,去城西明堂将两位苦主接来。”
“标下遵令。校尉大人,是否传桑都尉一同前来?”
“这还用问?速去速回,正事都给耽误了。”和余怒斥了一声,冷眼瞟了一眼孙旭东,此时双方脸皮已近撕破,和余满脸神情倨傲之极。
城西明堂?孙旭东闻言一怔,稍思忖后立即明白了,和余怕破虏军灭了苦主,是以不知几时将原来在杜记酒店的两位苦主弄到城西明堂去了。孙旭东望了和余一眼,心中对他心思缜密很有些佩服,以此人所具心机,即便是生活在两千年后,在那个到处是忽悠人的世界里,也是忽悠别人的主儿,难怪能玩弄伯齐于手掌之中达经年之久。
和余的手下带着孙旭东的亲兵出营不久,旷校尉便急急赶回,让亲兵去禀报大将军让他出帐相见。孙旭东闻报也懒得和和余打招呼,急步出了帐和旷一起走到较场旁问道:“司虞,是不是人没找到?”
“正是,店中只剩两个厨子和伙计,问他们他们也不知道。”
“嗯,人让和余先弄走了。这家伙,委实太狡猾。司虞不是派人看着了吗?”
“哦。是啊,看守的人看住了大门,我估摸着那两人是从后门走的。”
“和余的人去带他们去了,唉,我真有些担心王剪在那女子面前抗不住。”孙旭东望望天,和余步步占先,确实是个角色,孙旭东不由暗暗担心,已近午时初刻了,摸了摸颈中的牙印后说道:“只盼小轮子他们早些得手便一切都妥了。”
蔡轮趴在枯黄的草甸里,嘴里衔着一根巴根草咀嚼着,两眼却紧盯着眼前开阔的荒地,手中不时有意识地牵动一下结网的绳头。一刻过后,两眼被满目的枯黄弄得有些干涩,他轻声招呼了一声庆儿:“过来,帮我抓会儿绳头,老子得去撒泡尿。”
蔡轮爬起身往后走了几步站定,刚掏出家伙,就听庆儿尖细的声音:“蔡头,别撒了别撒了,来了,来了。”蔡轮一激灵,正要泄出的尿液一把便蹩了回去,家伙都不及收好,猛地趴倒在地,急急向庆儿那边爬过去。
“就是他,总在我店中吃酒,烧成灰小人都认识啊。你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我侄女才许了人家就让你糟蹋了,你让她以后怎么再见人哪。”杜掌柜一进中军帐就一把鼻涕一把泪水地闹将起来,手指着王剪骂声连天。
孙旭东并不看他,只打量着刚刚进帐的茯芹,就见她样子有些惊慌,尤其她见到地上跪着的王剪后,眼神一跳,即别过头去。时间太短,孙旭东看不出茯芹眼神之意。
“大将军,苦主已到,可以继续审了,过了午时三刻人犯还没处置掉,标下也不好到太子爷那儿交差。”和余心一横,今天是豁出去,公然矫了伯齐的令,不杀王剪誓不罢休。
王剪毕直地跪在地上,偏过头去看见了茯芹,一时大是激动,颤抖着喊道:“茯芹妹子。。。”茯芹听到喊声,微微抬头看了一眼王剪,两人对视约有移时,将台上的孙旭东心中已是大喜:这女子一定对王剪有意,因她眼神中除有几分柔情,另有几分无奈。
这三人一来,大帐中情形迅速又倒向另一边,除茯芹低着头一言不发外,同来的桑姓都尉先指手划脚地叙说了一番,那杜掌柜则声泪俱下地在一旁帮着腔,两人似久经训练,配合得默契异常。两张嘴下,王剪立时便成了一个是人皆可杀的大色魔。王剪奋力争辩,听杜掌柜哭着说了一句“污了我侄女名节。”当即脸有愧色闭嘴收声。那杜老儿甚是见机,即将那句话当成杀手锏,此后逢王剪出声争辩便来上一句,王剪立即住嘴,效果极佳。
孙旭东被弄得心烦意乱,眼见已过了午时了,除了眼前之事,心中更是牵挂城外的蔡轮怎么还没信儿,否则早就可掀将台发威了。眼见王剪眼中又是迷茫之色,不禁更是焦燥。
和余又高兴了,对桑都尉投去了无数个赞赏的眼神,见争得差不多了出声说道:“大将军,标下看没什么好说的了,人家苦主当面指实,王屯长也没有辩驳。天已这般时分了,再不行刑标下真的无法回去向太子爷交待了。”
“这个。。。王剪,你真的没有辩驳了吗?”只没想到王剪陷得比自己想像的还要深,孙旭东狠不能下去踢他两脚,一个大男人如此放不下,做情种也不能做成情痴啊。
和余见孙旭东分明是想赖着不杀人,自己本就是假传了太子爷的令,时间再拖长了,万一太子爷找个人来问一下就大事不好,是以阴沉着脸出言相逼:“大将军如果不想斩杀自己手下,那还是由标下将他带回太子营吧。唉,太子爷本就是多此一举,本想送个人情给人家脸上贴金,谁知啊。。。”
孙旭东听着不由怒火中烧,看来王剪这条命只能交于那女子了,伸手握住虎符猛拍将台大声吼道:“本将军问案,不得本将军问,哪个再敢多嘴亲兵上前掌嘴,听清了吗?”
“标下遵令。”两名膀大腰圆的亲兵捋了捋袖子伸着脖子大声答道,大帐中众人被大将军气势镇住,各人偷看了一眼亲兵蒲扇般的大手,屏声息气地站着,只和余冷笑一声,坦然翘起了二郎腿。
“王剪,本将军问你,你若真是黑了心污了茯芹清白,该当如何?”
“标下该死。”王剪跪直身子响声昂然答道。
“好。本将军再问你,若是茯芹跟人合伙要陷害你,你又该当如何?”
王剪转头望了一眼茯芹,就见她也正神情热切地目视着自己,只是见了自己的眼光后即低头躲闪,王剪心中一痛,转头大声答道:“若是茯芹妹子要标下死,标下也愿去死。”
王剪的话除了孙旭东,帐中之人无不大吃一惊,可眼见王剪昂然说来掷地有声,自非假言,即是和余也无不悚然动容。
“好,这才是我破虏军的男子汉。”孙旭东一拍虎符大声喝道:“来人,将王屯长绑在帐外旗柱之上,十步外弓箭手万箭穿心。”说罢眯着两眼紧盯着茯芹。
“标下。。标下。。”亲兵疑是听错了,迟疑着不敢上前。孙旭东又一声暴喝:“聋子吗?将王屯长绑在帐外旗柱之上,令弓箭手十步外万箭穿心。”
王剪在两名亲兵扶持下坦然站起,转身望着惊吓成一团的茯芹一笑,大步出帐,正掀帐帘时,就听一声尖细的声音急切叫道:“将军大人,王哥。。王哥。。是冤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