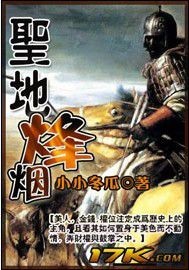王剪性格爽直,却不是惹事生非之人,太子营巡城兵士怎会抓他?孙旭东心下有些焦躁,在军帐中不停踱步,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两刻过后,旷校尉进了破虏将军的中军帐。孙旭东听旷说了情由心中大惊,问旷道:“那酒店中的女子司虞问过了吗?”
旷点头道:“他们将王剪带走后,我过去问了,那女子一直哭哭啼啼不说话,只是她大叔,就是那酒店杜掌柜一口咬死是王剪冲进酒店祸害了他侄女。”
“就在酒店之中?”
“正是。君武,此事大有蹊跷。”旷回想着那酒店杜老掌柜的神态,皱眉说道。
“嗯,司虞说的是。巡城要到起更之后,半夜了那女子竟然还没歇息?”
“不是,和王剪一起巡城的队率说是那女子自家叫住王剪的。”
“哦,这么说,王剪和那女子相熟?”
王剪喜欢杜记酒店里的一名女子,旷自然也知道些,当下又对孙旭东说了。
“设套?”孙旭东听罢了前因后果斗然警醒。旷校尉略作沉吟后点点头:“王剪虽然年少,但心性极正,若不是那女子勾引,不会做出这种荒唐之事。尤那杜掌柜说话时支支吾吾,甚为可疑。君武,这套虽设得拙劣一望可知,却甚是难解,显见是冲着你来的。夜入民宅强奸民女,按军律就一个斩字,王剪难逃一死不说,破虏军从此在杜城名声扫地。奶奶的,外面就是胡兵,有能耐不到外面使却在窝里斗。”
“嗯。那依司虞这见,背后设套之人是谁呢?”孙旭东沉吟了半晌后点点头迟疑着问道:“你觉得会不会太子伯齐?”问这话话他心中却是极为烦闷,为和太子之间隐隐的隔膜而有些不安。
“什么?”旷惊声问道,紧盯着孙旭东肃然说道:“君武想到哪里去了,太子爷要整治破虏军何须设套?你真是糊涂了。”孙旭东和旷的关系很特殊,孙旭东既是旷的上司又是他的弟子。平日在军中旷从不摆司虞架子,似今晚这般厉声说话真是头一次,不由让孙旭东有些吃惊。
旷见孙旭东愕然,也觉自己有些失态,放缓声调道:“君武,景大将军派咱们破虏军到杜城,就是为了帮着太子靖边立功,咱们既为辅保太子就当事太子以忠,如何敢轻易相疑?”
孙旭东被旷校尉问得呆呆发怔,事太子为忠?自己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骨子里不可能有古人对君王那般的赤诚和忠心他是知道的。但还是觉得哪里有点不对,但到底是哪里自己一时又说不出来。自从到杜城之后,和老司虞除了有军情相商之外,两人几乎就没谈过别的。孙旭东暗骂自己糊涂,很多事都是当局者迷而旁观者清,在这个世界里,旷司虞是自己最为贴心之人,为何竟蠢到不曾与他相商?
旷默默听完孙旭东对伯齐的诸多猜忌之言喟然长叹一声:“嗨!今日之太子即明日之鑫王。君武,自古君可疑臣,臣不可疑君,既保之则忠之。依我看太子瑕不掩瑜,虽处危位仍力持变法强国之议,仅此一点就非他国太子可比。对你更是言听计从,实为不可多得之明主。难道你忘了孙先生之言,大鑫国要想变法图强,少了太子这个龙头终是一场空。你所言皆为小事,日子久了太子自能识得人心。倒是似你这般猜前想后、患得患失,是为侍君之大忌啊。”旷说着望着孙旭东,见孙旭东仍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知他年纪尚轻阅历亦尚浅,并不足以应付这些很难说得清的东西。稍作沉默后沉声说道:“君武,是你想得太多了,有时最大的敌人莫过于心中之敌。还记得邺城的斗士场么,此刻你就是在场上挥动短剑的斗士,而太子正是坐在席上将宝都押在你身上之人,你还不懂吗?”
旷的语犹如在孙旭东头上响了一个惊雷,稍作思忖心中幡然大悟。他望着旷冷峻的眼神大是感激,不是至亲之人是不会说出这样的话的。站起身对着旷恭身行了一个大礼:“多谢司虞指教,司虞之言令君武如醍醐灌顶,是我杯弓蛇影将事情想左了。”
旷轻点点头扶起孙旭东说道:“当年大忌王一统天下,以仁法治国,大小诸侯谦恭礼让,国中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安居乐业,四海之内无不歌舞升平。可惜,咱们却都没赶上那样的好时光。”旷说着微微昂起头,心中想象着天下太平、百业兴旺的大忌王朝悠然向往。稍后苦笑一声:“如今天下纷乱弱肉强食,上有诸侯为争田霸地,各国穷兵黩武,连年兵患不断;下有贵族世家的黑心盘剥,将平民百姓的血汗榨得油枯灯尽兀自不松手。一逢荒年,奴隶们被禁锢在封地,饭都不准出去讨,只能是易子相食,惨不忍睹。。。。为打仗,不满十五岁的娃娃也被征入军中充作军士,你看见太子营中的娃娃兵了么?”向来冷竣的旷司虞话说至此时长叹了一声,悲天悯人的神情溢于言表。稍停接着说道:“天下平民百姓没有一日不盼着天下一统,过上安宁日子。我虽非鑫人,但纠纠大鑫共赴国难这句话却让我甚为感动。当此乱世,君武,正是你立大志,成大业的最好机会啊。心怀坦荡,一心辅保伯齐,救天下苍生百姓于水火之中才是正途。”
孙旭东虽觉得有些被旷误解,但他的话确实是金玉良言,心怀坦荡四字更是一语中的。孙旭东此时已经知道了和伯齐的隔阂所在:自己并没有真正融入到这个时空,用现代人的思维来取代古人的思维没有隔阂那才叫怪。正是自己经常用着不合时宜的思维胡思乱想,才导致和伯齐有了本不该有的隔阂。想通了此节,孙旭东一扫心中烦闷,对旷呵呵笑道:“多谢司虞教导,君武明白了。”
旷对孙旭东甚为了解,眼见他神情轻松知他心结已解大是欣慰。却又皱着眉头问道:“王剪的事怎么办?不想法这可就是个死套。酒店的掌柜和那女子我已让人看住了,要不先将他们带过来你问问?”
孙旭东经月的疑虑一去,神清脑明。低头沉思片刻后对旷狞笑一声说道:“司虞,王剪之事先放过一旁。早天一早咱们一道去太子营,太子爷身上贴着张膏药,咱们也该替他取了。”
************************************************************************************************************************
南宫的轺车队总算是爬过了梧城外的大山。此时月朗星稀,轺车队就歇息在大山脚下的驰道边。在野外过夜,照例是燃起十几堆大大的篝火,兵士和驭手们围着一边取暖一边进食,待牛皮吹得累了,便钻进搭在边上的帐篷里睡觉。
李玲儿和云姑坐在最中间的火堆旁,两人吃过干粮后都不说话,望着眼前跳动的火堆各自静静想着心思。只离得稍远的火堆边不时隐约传来兵士们的说笑和驰道两边刚刚冬蛰完的虫儿正自低吟高唱声。
半晌过后云姑转头看了一眼眼波流动的李玲儿轻声问道:“玲儿姐,你在想什么呢?南宫大人说再有过两天可就到杜城了。”
“没想什么。”臆想中的李玲儿转过头来,云姑看着顿时呆了,火光下李玲儿明艳不可方物,满脸都是柔情。她浅笑后答道:“是啊,总算是要到了。”
云姑心头笼上一股酸意,更多的却是艳羡,再有两天,李玲儿就能见着她的意中人了,可自己呢?她将自己手中的断枝投入火中,转头望着火堆怔怔掉下泪来。
“咦?妹妹你怎么啦?”李玲儿只觉眼前这个比自己小两岁妹妹年纪虽然不大,却有着很重的心思,一天到晚总像有说不完的烦心事,愁眉不展。一路上对她照顾有加,除了自己大些是个姐姐之外,还有据她说她的意中人也在破虏军呢,那可就是他的手下呀。
李玲儿伸出手轻轻搂住云姑,正想着劝说几句,只听有几匹拉车的辕马惊悸地打了几声响鼻,接着便听见布在驰道两头巡夜兵士的断喝声,旋即四周忽然无数支火把点亮,将两百步之外照得一片通亮。李玲儿见机惊叫一声,一把搂住云姑钻进了帐篷。
坐在西头的南宫一跃而起,拨出腰间的铜剑后大声喝道:“快起身抄家伙围住轺车。”兵士们哪里还用等南宫下令,早都各自抄起了架在火堆边的兵器,十几人一组将轺车团团围住。
四周火把在渐渐围拢,南宫两眼紧盯着火把下的人影,直到百步开外终于看清了手持火把的都是身穿胡装的胡兵!南宫大奇,此地离着杜城尚有百里之遥,怎么有数量如此众多的胡兵出现?眼前的形式的敌众我寡大为不利,南宫稳住心神,紧握手中铜剑大吼一声:“兄弟们,今晚咱们得豁出去了,弓箭手搭箭。”
轺车队带着几十张长弓,射程可达百步之外。见主将临危不惧,兵士们虽略感惊惶,但还是立即开弓搭箭,只等南宫下令。
“南宫都尉,你们已被我们四下围定,就是插上翅膀也难飞出去了。我们只是请你们到我们的毡包里去做客,品尝一下咱们鲜香的烤羊肉和酸奶酒,绝无恶意。”靠近的火把就在鑫军兵士长弓的射程之外停住,一名胡兵用流畅的汉话喊道,声音高亢且嘹亮,轺车队中人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我呸,胡子见了汉人就杀,怎么会接我们去做客?护卫大人,放箭吧?”队中一名队率手开长弓高声骂道。南宫却更是吃惊不,小胡子竟然知道自己的姓名和官职都知道?一时竟不由呆了。
“日”一声极为响亮的弓弦响后,胡兵中一支长箭带着一族火球冲天而起,燃烧的火球在半空中发出十分耀眼的光芒。
“南宫护卫,两里之外还伏有我们一万铁骑,你们若是不从,立时便死无葬身之地。”胡兵兵士手拢着嘴成喇叭状,尽力又喊过一句话来。只稍过片刻,众人耳中就隐隐闻有杂乱的马蹄之声,方才那支被射上半空的火箭自是向埋伏在远处的骑兵报信用的。
南宫手心已出了汗,胡兵对轺车队竟似知根知底。轺车上所装皆为破虏军急需的兵器,景大将军监行前就说过,里面有很多兵器都是胡子们做梦都没见过的利器,真要让胡兵得去拿来对付破虏军,自己就是死上一万次也是赎不了罪的。
初时杂乱的马蹄声此时已如雷鸣,大有地动山摇之感。南宫满脸戚色,对兵士们猛吼一声:“亮出家伙跟胡子们拚了,死大伙儿也要死在轺车上。”心中却在急速盘算着,若是将轺车推入篝火之中能不能烧着呢?
四周的胡兵倒是显得极有耐心,仍是那名胡兵在着力喊话:“南宫护卫,我当信使过来,请约束手下兵士不得放箭。”说着就见他高举双手抱头,高一脚低一脚地向车队走过来。
“先别放箭,且看胡子们捣的什么鬼。”南宫已是算过,即使立即将轺车推入火中也不会一时就能烧着。此时是真正的心急如焚,左右为难,额头上沁出豆大的汗珠。
会说汉话的胡兵是名百夫长,到了轺车队跟前后一眼便看出南宫是头儿,竟对着南宫笑了一下才说道:“南宫护卫,我们大单于只是请你们去作客,不会伤害你们的。”
南宫却不愿在敌人面前丢了志气,哼了一声厉声说道:“咱们正在交战,无端的作的什么客?”
那百夫长皮里阳秋地一笑道:“这个我也不知,只是我们大单于说,只要你们愿意去,可以不交出手中兵器,轺车也由你们自行看管,我们不会动一根手指头的。”
不光是南宫,鑫军只要听清了的兵士无不大吃一惊,胡子大单于还真是要请客?
“我南宫又不是三岁小儿,怎会任由你信口雌黄。南宫这条命不要了,你们也休想诓骗我们的轺车去。不用废话了,让你的人放马过来便是。”看着百夫长有恃无恐的模样,南宫心中大怒,无非是一死而已,且拚了这条命再说。
百夫长冷哼了一声,眼瞟着南宫说道:“胡人说话向来作数,比起你们汉人来,要可信十倍。我们大单于知道南宫护卫是怕失了轺车,所以准你们自行看护。不知南宫大人想过没有,我们若真是要劫取你们的轺车,只需一声令下万箭齐发,你的这些轺车死人还得看住吗?”
南宫惊怒交加却又无可奈何,这百夫长所说确为实情,胡子真要抢轺车自己这点子人除了搭上性命不会有其他结果。南宫转头望了一眼长长的车队和全神戒备着的兵士们,心如刀割,
硬硬心肠对那百夫长说道:“好,如果我们跟你走了,你如何保证不动我的轺车?”
百夫长两只怪眼上翻,嘿嘿一笑伸出双手道:“就用老子的人头作保。从此刻起你们就可绑了老子,只要有人动了你的轺车,你一刀将老子的头砍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