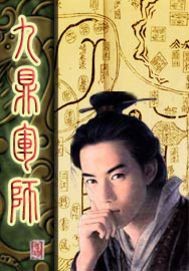“啊?胡人还有这样的规矩?”明知毛怀说的不会是假话,孙旭东还是忍不住惊声问道。
“回大将军,胡人供奉月亮神,是以怀春少女若是心中有了喜爱的男子,只需在那男子脖颈处留下自己形如月牙的牙印,那男人就非她不能别娶了。”毛怀见大将军疑惑的眼神,急切说道。
孙旭东听罢忍不住用手摸了一下自己颈下胡安丝托咬出的牙印,确实形似半月,顿时哭笑不得:原以为是自己那晚在山洞里表现的怜香惜玉博得胡安丝托的欢心,昨天一认出自己便要以身相许,却原来是这胡人古怪的规矩让胡安丝托投怀送抱的,想明白此节后不禁放声哈哈大笑。
毛怀不知大将军何以发笑,只当他仍是不信自己的话,瞪着眼急道:“标下所说千真万确。大将军不可不信。被人咬了又不娶,胡子会拿来乱刃分尸喂狼的。”
“本将军自然相信。毛怀,此事切不可告诉别人。”孙旭东忍住笑,从怀里摸出十几个钱递给毛怀:“你到集市上去买些生鸡蛋,让伙夫做好了送到神机营给小轮子他们。”
“标下遵令。”毛怀见大将军信了自己的话脸露喜色。拱手答应一声,伸手接过钱出了孙旭东的帐篷,一个人独自出大营,便径直走向城南的集市。不到一里地,隐隐就见远处有两人牵着两只巨犬拐进了一条弄堂,毛怀不由想起自己腿上的伤疤,也不知这太子到底养了多少狗,心中暗骂了一声,自顾去买鸡蛋,心中只想大将军会不会真的娶了那胡安丝托呢?
孙旭东正在帐中安排营中事务,太子营中亲兵却到了,报太子请破虏将军过营商量马陵山新修道路的事宜。孙旭东即带了几名亲兵,骑马赶到太子营中时,中军帐里已坐等着杜城令等七、八名地方官。自然是因修路要工要料,是以伯齐请了杜城令等地方官员一同前来商议。人齐后太子令和余取出了地图,伯齐胸中早有成算,名为相商其实就是让众人来领命:修路奴工及所需石料由杜城令征集;为防胡子趁修路时袭扰,守护之责即交于马陵山领军校尉朱长平。伯齐处理起这些民政来驾轻就熟,三言两语就解决了问题,效率之高让孙旭东大为叹服。
曲终人散伯齐却独留下了孙旭东。伯齐一指和余道:“君武,和余今早一路赶回,说田齐有一队辎重正在送往杜城。”
孙旭东大喜,田齐来的辎重肯定都是自己让吊大哥赶制的连弩和三棱箭簇,正是对付胡子的利器。连忙问和余道:“和校尉得着书信了吗?”
和余笑道:“不是,标下送信到梧城时在路上遇上的。押运辎重的都尉说他名叫南宫,太子爷说记得好像他就是景大将军的贴身护卫。”
“正是正是。倒要多谢和校尉了。南宫都尉离着这儿还有多远?不知几时能到?”孙旭东和南宫的交情很深,一听他要来杜城心中大是高兴。
和余皱眉说道:“远倒不是很远,只是那南宫都尉说轺车老旧,吃不住重压,赶路稍一贪多就坏,估摸着还要个五、六天的样子。”
伯齐见两人说话时貌似颇为亲热很是高兴,想起一事便问孙旭东道:“哦,君武,我听说你们破虏军中互通消息用的是鸽子?”
“正是,若非紧急军情,营中都是用的飞鸽传信。”
“标下这倒是头一回听说,那性畜还有此灵性?”和余大瞪着两眼,一副打死都不信的神情。
伯齐大感兴趣,哈哈笑道:“这么说还真有此事?鸽子也会懂人事?几时弄几只来让本太子也长长见识。哈哈。。。”
孙旭东不禁想起自己在前村放羊时那四只训练有素的牧羊犬,看来智慧总是在劳动人民当中这句话确实是致理名言。微微一笑道:“回太子爷,很多鸽子、狗一类的性畜只要训练得好了,都可做些送信、寻物之事的。” 孙旭东说着眼睛的余光一扫和余,只见和余眼中竟闪过一丝慌乱的神情。
按照伯齐的布置,第三日一早晨时刚过,杜城南门大开,第一批六百名修路的奴工肩挑背驮着修路所需的物事出了城门。带兵护送的是副将黄震手下一名都尉,骑着高头大马走在最前头,奴工周围则是两卒双手持戈,背带长弓的步甲,警觉地四下张望。
官道上走了三、四里地后,已脱出了杜城城楼上兵士的视线,那都尉不时催促着众人快行。就是这一段最为危险,再往前走上几里地,就会有马陵山的驻军前来接应。
奴工们有些背着几十斤的家伙什,自然走不快,都尉急了眼大声喝道:“作死吗?你们当这是干活磨羊工怎的?再不快些走,真有胡子来了,割了你们的脑袋去。”骑在马上两眼只找那拖不起脚的奴工,打马上去不由分说搂手就是一马鞭。
官道转过一个急弯后进了一段洼地,近千人的队伍立即走进了地平线以下。这段路并不长,也就里半路的光景。都尉更加警觉,不时四处张望,喝斥奴工的声音都被自己卡小了些,好像生怕惊动假想中的胡子。
队伍平平安安过了洼地,前面只需几十步就是上坡,都尉暗松了一口气。打马上前直上坡顶,刚刚露出头顶,耳中就闻破空之声,幸亏他逃命的经验极是老到,急速伏身低头,只觉颈下被系着都尉平帽的绳索勒得生疼,崩地一声绳索断裂,头顶上的平帽已被一支羽箭穿透,跟着羽箭跌落在地。
“胡子!”都尉狂叫一声,拨转马头又冲进洼地。身后的奴工顿时大乱,扔了手中的家伙什,转过身即向原路奔逃。都尉却指挥兵士们列成箭阵开弓搭箭,对着坡顶。
兵士们等了半天,拉开弓弦的手都酸了,坡顶上却寂静如常,并不见胡子的影子。都尉披头散发,惊疑不已,如果不是自己那顶还躺在地上的平帽,简直不相信刚才自己差点命已丢掉了。
“你慢些爬上去看看。”实在是耐不住了,都尉一指前排的一名兵士道。兵士倒也勇猛,放下手中的弓箭,紧跑几步后趴下,手脚并用渐近坡顶后停了下来,慢慢伸出头去。
“日”果然一声凄历的破空声后,兵士惨叫一声倒滚下来,一支近两尺长的羽箭穿过他的头顶,鲜血从箭洞中涌出,尚未来得及流淌随即没入干涸的荒原。
兵士们大惊失色,顾不得手酸拉开了弓弦。都尉更是惊慌失措,照经验箭法如此精准必是胡子的射雕手,问题不仅于此,若不是早已拉弓等候,不可能在兵士冒头的瞬间就将其射杀。拉弓用的是气力,即是力大如牛的人也不能拉开弓干等着,既是如此,那上面得伏有多少胡子的射雕手在轮流张弓啊。
奴工们乘着原路在往回拚命在奔逃,遇上胡子九成是要献上自己的脑袋的。不幸的是还未出洼地,前面已站着几排手持弯刀的胡子,奴工们霎时只觉未日已到,但逃生的欲望却让他们四处散开,无奈早已埋伏好的胡子三面兜上,前路尽断已逃无可逃。绝望的奴工有些忍不住惊吓,放声大哭,更有的瘫倒在地,只等胡子来割头了。
叽哩哇啦的胡子并没有屠杀奴工,却拿出了几捆麻绳,将奴工们一个一个捆绑着连成串,遇上稍有反抗的奴工,也只是翻转弯刀用刀背将他们打得头破血流而已。
最前面的都尉和兵士们被笼罩在巨大的恐惧之中,一时茫然不知所措。那都尉隐隐听得后面奴工的哭喊声,知道今日中了胡子的伏击。眼望着只见巴根草影却不见人影的坡顶,对兵士一挥手道:“快,撤回杜城。”说罢自己一拨马头,对着马屁股狠狠一鞭子当先冲了出去。
兵士们巴不得一声,闻令转身就逃。就在此时,坡顶猛然跃起两排胡子,一个个拉开手中的长弓,顿时箭如飞璜,射杀着奔逃的鑫军。
**************************************************************************************************************************
一个时辰过后,孙旭东率三千破虏军的骑甲护着伯齐到了洼地。洼地里胡兵已消失得无踪无影,地上四处散落的都是奴工们扔下的家伙什,再往前行,近两百名的鑫军身中长箭倒尸在荒地,到处都是干透的黑血,一片狼藉。倒在地上的兵士们的头都被胡兵割去,无头的尸身上大都插满长箭,被射得像刺猬一般,其状令人惨不忍睹。
“陈都尉,这可都是你手下的弟兄,怎么独独你逃脱了?”伯齐身边副将黄震面色阴冷,对着那名唯一逃回去的都尉冷声问道。
“标下。。。标下。。。骑马,是乘着。。。洼地一直向左才逃回去的。”陈都尉的头发挽在头顶,盘了一个鬏,中间却用一根断树枝儿压住,神情大是狼狈。问黄震如此发问更是惶恐,手指着自己在仓促中精选的逃跑路线颤声说道。
“你倒是逃得快,如何面对死去的兄弟?”黄震怒道。这陈都尉向来行事极是见机,大概昨晚见今日护送奴工是太子亲自交待下来的,又非军事行动想来风险不大功劳却不小,是以在黄震面前磨了半天牙才捞着了差事。
“黄将军不要过责了,若不是他逃回来咱们还不能立即便得着信儿。”伯齐皱着眉说道:“胡子变得越来越诡诈了。陈都尉,胡子没追你吗?”
“胡子们好像没骑马。”一听太子不怪罪自己,陈都尉说话立时顺畅了许多:“都用的是步卒,头前埋伏着射雕手,后面。。后面标下也没能看清。”
胡子不骑马?几人对望一眼大吃一惊。孙旭东招呼了一声陈都尉,两人打马直上了坡顶,孙旭东让陈都尉用手指着将当时情形细细叙说一遍后,回过身叫了自己的亲兵骑着马跑了一大圈。
“君武,情形如何?”伯齐问打马回来的孙旭东。
“胡子是骑马来的,马放在洼地右边一里多之处。”一圈跑下来后,所见让孙旭东顿感心惊,隐隐只觉太子身边的那只黑手又伸出来了,只是眼下人多不便明言。
奴工一贫如洗,又都是男人,胡子抢去何用?黄震大是不解,说道:“太子爷,胡子此番行事好象大是反常。您看这洼地里只见兵士的尸首,奴工却一个都没有。莫不成胡子也要修路,将他们活捉了去?”
“嗯,君武将军请下令,咱们回去再参详吧。”伯齐却见孙旭东眼光闪烁,自是有不便说之事。一把拨转马头,对孙旭东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