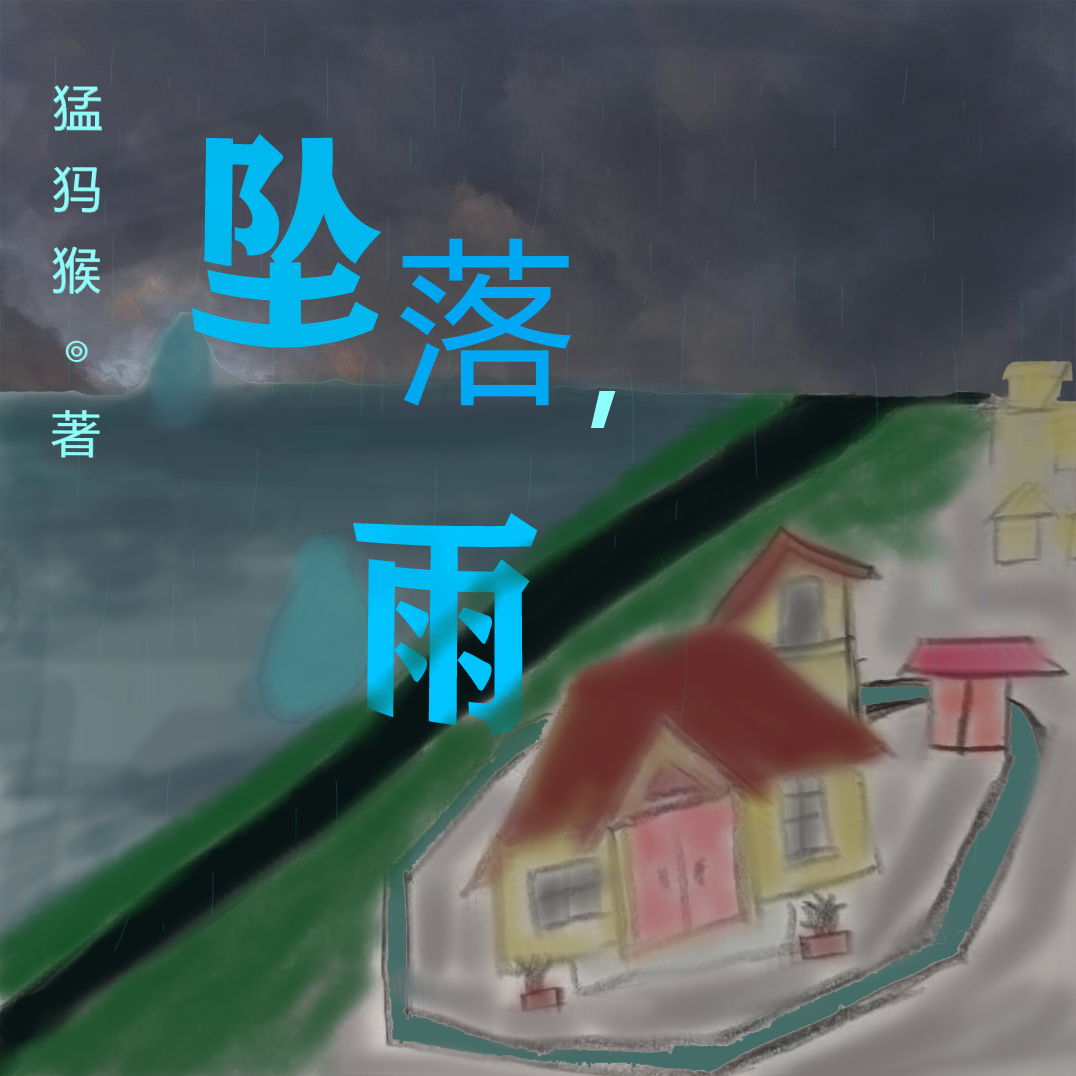景将军边上的兵士闻言立即从怀里摸出一串外形象刀一样的钱扔了过去,孙旭东一把接住,仍是老一套:“小民谢将军大人赏!”听景将军说大鑫?大鑫是什么朝代?这赏钱可象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刀币呀。这时也顾不得了,只知道自己的脸回来了,管他在哪儿都行。
景将军哈哈大笑,看了几眼地上的死狼,问道:“小兄弟,你的狼卖不卖呀?”这个问题倒还是没考虑过,不过今天晚上是不是需要住在宾馆还都不知道呢,要来何用?孙旭东爽快地说道:“将军要这几只狼,尽管拿去,不用给钱。”
“哦?”这几匹狼光是皮毛拿到市上就值不少钱,景将军见他如此大方,有些吃惊:“本将军怎能白要你的狼?你想要什么尽管说。”
孙旭东初来乍到,对本地的行市还不是太清楚,见兵士身后背着的弓看起来不错,刚好自己的土制弓断了,便指指那兵士说道:“将军要实在想给,就给我那副弓箭吧。”
“好,好弓送壮士。”景将军对身边的兵士命令道:“解下弓箭,送他。”
孙旭东接过兵士的弓箭,这是一张榆木雕制的弓,弹性非常好。弓弦用手指粗细的牛筋制成,两端套着磨制的山羊角。长箭扁平的箭镞是用青铜打制的,两边有冀,锋利异常。孙旭东弯弓搭箭,虽然不如在部队时训练用的现代弓,但是比那张土制弓要强得多得多。
景将军走到孙旭东身前,一把扯开了他身上的破羊毛袄,看了看露出的肩头,皱了皱眉说:“真是可惜。”转身对兵士们吩咐道:“扛上死狼,咱们回大营烤狼肉吃。”带着兵士们大步而去,转过身去的后背上还有两个闪动的花结。
孙旭东疑惑地看着景将军他们走远了,不知道景将军为什么会说可惜。他扒开羊皮袄看着自己的肩头,上面竟然烙着一个火红的印记。孙旭东大奇:这是什么时候留下的?
现在需要好好坐下来想一下了,他觉得慢慢有了些头绪,不是经常听说鬼魂附身吗?可能帆让我附身到一个时空滞留了几千年的地方,难怪自己的脸变了。被我附身的人从事的职业应该是一名专业羊倌,除了眼前的羊群,或许家里还有良田数亩,娇妻一人或是二人抑或是三人?对于这一身实在是拿不出手的衣着,他给自己的解释是,中国人一向是不露富的,没看见山西的煤老板蹲在地上吃‘叭叭面’吗?古人当然也不例外,说不定羊倌家还会有洋楼若干套,仆役下人若干...心中正暗自高兴,忽然想到既然有下人大约不会自己亲自出来放羊吧?想了半天不能自圆其说,不如顺其自然,走一步算一步吧,至少自己摆脱了那张让人恶心的脸就是天大的喜事,更何况证明了帆没有瞎说,只要我帮助王实现了他的梦想,将来回到那个世界上我原有的一切都会改变,这实在是让人太兴奋了。可是,我要帮助的王是谁呢?是景将军说的大鑫吗?可这大鑫实在是没听说过呀。
一个一个的问题让孙旭东想破了脑袋也无济于事。肚子咕咕一阵乱叫,他感觉到饿了,伸手摸了一下怀里,什么都没有,“这鸟羊倌,出来一天也不带包方便面。”拿起地上的葫芦摇了摇,很沉。扯开堵口的塞子用鼻子闻了闻,没有什么味道,里面应该是水。先尝了尝确定是水之后,孙旭东仰脖猛灌了一气。
抬头望天,太阳已经西斜马上要落山了。现在该到哪里去?孙旭东一筹莫展,帆也真是的,让人家来探险,探险图啊或是计划表啊总要给一张吧。这儿白天都有狼群出没,晚上说不定会有什么来呢,总不能在这儿过夜吧。
他无奈地站起身来,羊群边或坐或卧的四只猎狗见孙旭东起身也都站起来,呜咽着聚拢羊群,汪汪叫了几声后开始驱赶羊群下山。
孙旭东惊奇地看着这一切,忽然醒悟过来:这几只猎狗知道他该去的地方。孙旭东心中立时消除了那两只猎狗救狗不救人的不良记录,决定回去以后,好好弄几根骨头犒劳一下,以示奖励。连忙背好弓箭,拿起鞭子跟在羊群后面走下山坡。
猎狗驱赶着羊群上了树林边的大路后向西走去,绕过刚下来的山坡后孙旭东眼前豁然开朗,路的两边都是一望无际收割后的麦田,麦田被一条条沟渠和田埂分割成一块块的方型,远处麦田里到处都有人在放火烧割剩下的麦秸秆,空气中淡淡地烟雾弥漫。可惜中间的田埂都很窄,否则孙旭东真会以为是到了哪个建设兵团的机耕地。
前面的羊群扬起了漫天的灰尘,孙旭东顾不得羊皮袄的膻味了,蒙住口鼻紧跟在后面。五里地过后,他看到在大路右边的麦田中间有一片低矮的草房,一条从大路分叉的小路可以直通那里。
一只猎狗紧跑几步,到了叉路口前转过身站着不动,随后而到的羊群即在猎狗虎视眈眈的目光中转向了小路,孙旭东对这四只猎狗的表现大加赞叹,看来,训狗这个行当在几千年前就是我国劳动人民的强项了。下次有机会看到初中的历史老师时,可以给他也上上课。
羊群领着孙旭东进村了,放眼一望,都是破败的草房,心里暗暗失望,看来小别墅是没有了。七弯八绕后他眼前出现了一个用青砖垒起的大院落,院门很宽大紧紧关闭着,青砖建筑在这一片土房中格外引人注目。孙旭东眼看着一只猎狗飞快地跑向院门高声大叫,心里暗叫一声侥幸,看来至不济也是个财主了。
院子里面的人大约是听到猎狗的叫声,“吱”地一声打开了院门,当先的一只猎狗呼地一声就蹿了进去,羊群咩咩叫着紧跟其后。孙旭东站在最后远远地打量着开门的中年汉子,就见他跟自己一样也是头发散在后面,面目狰狞,身上穿着黑色的粗布大袄,正站在门边看着羊群进院,嘴巴不停在动,好像是在数羊的只数。嗯,这个管家还不错,挺认真。孙旭东心里想。
孙旭东跟着最后一只猎狗进了院子,院子很大,正前是五间青砖瓦房,两边各有一排低矮的草房,院子角上用木栏子围出了动物们的天堂。
门边汉子点清了羊数阴着脸问道:“怎么少了一只羊羔子了?”
汉子说话的态度让孙旭东有些不安,这可不是管家对主人说话的样子啊。哪有见了领导还恶声恶气的?想想平时馆长见了蒋局长的样子,这汉子的神态实在是有些不对头。那汉子见他不说话眉毛一扬,恶声道:“你哑巴了,老子在问你呢。”
鬼才知道怎么会少了一只羊,又没有办交接手续,孙旭东看他那副凶神恶煞的样子甚是不爽,刚想回他两句,那汉子顺手抄起一根鞭子打了过来,动作异常迅捷。嘴里骂道:“好你个臭奴隶,弄丢了羊还敢拿眼瞟我,反了你了。”
毫无防备的孙旭东结结实实地挨了一鞭子,顿时懵了,倒不是挨了一鞭子,有破羊皮袄挡着,不算太痛。让他发懵的是他怎么会是‘臭奴隶’呢?
尽管从汉子对他的态度上他大略知道自己可能不是这个家的主人,但也不至于一下子就从财主变成了奴隶吧?再说这奴隶也太遥远了吧,这难道不是在三国时期?奴隶社会可是在二千多年前才有,本来就够远的了,这汉子一鞭子又把他抽远了几百年。
那汉子手中的鞭子没头没脑地落了下来,前面屋里的人听到动静也跑了出来。孙旭东沉浸在强烈的落差中,一时竟毫无反应,任由那汉子的鞭子雨点般地落在身上。
出来的几个人都在围观,没有人上前劝阻。那汉子抽了一阵子,大约是手酸了,鞭子往地上一扔,对身后一个年纪很轻的后生说道:“阿福,这臭奴越来越贱了,丢了羊还敢拿眼睛横我,今晚饿饭。”叫阿福的后生一脸阴笑,躬身说道:“是,大管家,饿他几天,看他是不是得多懂点规矩。”
大管家瞪了孙旭东一眼后气哼哼地进了前面的屋子,阿福一招手,跟他一同出来的几个人一起上来围着孙旭东。阿福看到孙旭东背上的弓箭,皮笑肉不笑地说道:“哟,君武,这张弓不错啊,不会是偷来的吧?”说罢转到他身后,想动手取下孙旭东背上的弓。
君武?孙旭东明白了,自己附身的那个羊倌名叫君武,看来君武不仅是奴隶,而且在这个家中也是经常被欺凌的对象,这个比自己矮了半头正在眼前晃来晃去的阿福,肯定是其中的一个。看他想动手摘自己的弓,本想出手教训教训他,但此时还没弄清情况,只好忍住。
阿福手握着弓背,嘴里啧啧作声:“哎哟,这可是一张军弓啊,不对不对,看来不是偷的。”说完,慢慢拿起弓,眼见孙旭东身前的弓弦到了他下巴位置时,猛向后拉,用弓弦勒住了孙旭东的脖子,大声喊道:“我看你是用那只羊羔子跟哪个逃兵换来的吧。你们都别愣着,给我揍这贱奴。”
孙旭东脖子被勒,顿时喘不过气来,急忙双手撑住弓弦,身子向后倒去,这是一个保护性的动作,以免颈脖被弓弦勒伤。边上几个人听了阿福的命令,一拥而上,拳打脚踢。倒地的孙旭东忙双手抱头护住脸,意识中两个部位是最重要的,一个是刚刚才得来的新脸,另一个则是要弓起身子才能保护住的重要工具。
“你们给我住手。”随着一声娇斥,从前屋过来两个人,“阿福,你又在欺负人,你当你是谁啊?”孙旭东松了抱头的手,只见说话的是一位十七、八岁的姑娘,红着脸圆睁两眼怒盯着阿福。
“大小姐,这可是大管家让我干的,你别管。”
“呸,我爹让你饿他饭,让你打他了吗?”
“那是因为大管家不知道这贱奴拿羊羔跟人换了弓箭,要不还不得让我扒了他的皮。”
“那也得等我爹说话,你们滚开些。”大小姐说完,又对身边一起出来的老汉说道:“黄伯,你扶他到屋里去吧。”
叫黄伯的老人扶起孙旭东,向左边的草房走去,孙旭东从大小姐身边走过时,看了她一眼,正好碰到大小姐满是关切和怜惜的目光,不由得由中一动。眼睛的余光扫过阿福时,只见他满眼恶毒地瞟着自己。
阿福看着大小姐对孙旭东充满关切的神态,心里酸溜溜的,暗暗咬牙切齿:总有一天老子要弄死这个贱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