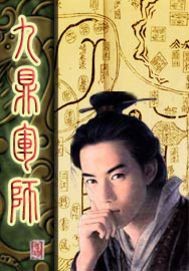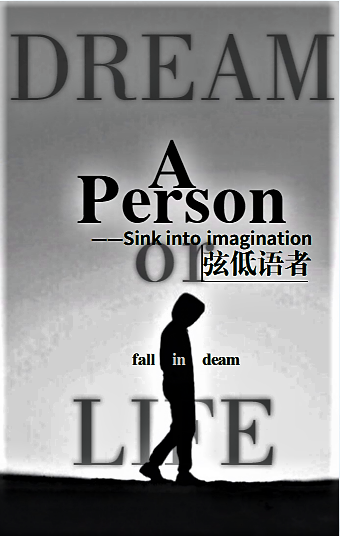孙旭东大吃一惊,南宫说的那帮子人肯定就是自己手下的斗士,他们是一群勇夫,现在眼中大概只有自己,可能是见自己入营后良久未归,放心不下,便要来闯营。急忙拦住转身要去的南宫,对景监一拱手道:“大将军,可能是和我一同来的兄弟,待我与护卫大人一起去看看。”
两人急步赶到大营辕门,孙旭东人还未到,就听辕门外乱哄哄一团,成鼎破锣一样的大吼声,大约正在教训拦住他们的护卫兵丁:“我们君武大人是来投景将军的,为何将他扣住?谁要敢动了他一根寒毛,老子就和他拼了。”
孙旭东心中感动,这是一帮最单纯、最真挚的生死兄弟,在来的那个几近尔虞我诈的世界里,自己的朋友中几乎是找不到一个的。他跨过辕门,见来了大约一半的斗士,便脸上佯装怒容,高声说道:“成鼎不可造次,这可是景大将军护边大营的辕门。”
乱哄哄的斗士们见到孙旭东,立即欢呼一声,渐渐静了下来,成鼎急步迎上来说道:“我们见大人久入不归,怕有什么不测。再见不到大人,咱们就要踹了这个...那什么。”成鼎看到孙旭东身后的南宫,硬生生地忍住了鸟大营三个字。
孙旭东瞪了他一眼,板着脸说道:“景大将军怎会害我,成鼎行事鲁莽了。怎么孙先生也没拦你们。”
成鼎嘻嘻笑道:“孙先生倒是拦了,可是没拦住。大人,你可是咱兄弟们的主心骨,一刻也离不了的。”
孙旭东听罢一怔,明明自己走时吩咐过,他不在时一切听从孙先生号令,看来这帮人是一点组织纪律观念都没有了,这种势头可绝不能听任任之。但此时是不便理会的,转头对南宫苦笑,南宫哈哈大笑:“我南宫要有这么一帮兄弟,高兴还来不及呢,君武兄弟不要责怪他们了。”
“这就是你从那边带出来的人吗?”景将军不知何时已站在身后,孙旭东忙躬身答是,转过身对着斗士们说道:“这位就君武景二哥的大哥,景大将军,大伙参拜。”说罢自己先跪了下来,身后的斗士们立即齐刷刷地跪下。成鼎偷眼望着景监,就见他两眼炯炯有神,配着削瘦的脸型,不怒自威,虽是一身常服,却透出一股手操生杀大权的将军气势,内心不由有些惴惴。
“好、好,都是些勇猛之士啊。”景监这一次并没有伸手扶他们,而是来到跪倒在地的斗士们中间,这中间有不少人曾经和景皓一齐同甘共苦,现在看着他们对景监的心灵也是一种籍慰。
“孙先生没来吧?”景监问道,孙旭东见成鼎在**,用手捅了一下他,成鼎忙答道:“孙先生没来,还拦着不让我们来。”
“哦,孙先生内慧之人,自不会同你们一般胡乱行事。”景监口中有责怪之言,脸上却是嘉许之色。“大伙儿都是曲乡义民,既愿到我护边大营来投军,我景监都收了。南宫,你这就带着义民们到花儿坡陈校尉那里,告诉他先把义民们安顿下来,三日后本将军自有后命。”
景将军的话有些奇怪,孙旭东没听懂,但知道景监既象这样说自然有他的道理,便大声说道:“多谢大将军收留。”南宫得令即让兵士拿些火把出来分与斗士,准备出发。
景将军走到孙旭东面前,挑了一下眉说道:“君武兄弟,你先带着人跟南宫去,另请转告孙先生,本将军不日一定前往拜访,失礼之处还望先生莫怪景监。”
目送着南宫领着孙旭东他们去了,景监回了大营,刚进辕门,就见将参王平带几个人急急赶来。王平见到景监一怔,忙行了参礼说道:“有人报我说是有刁民竟敢闯营,莫非还惊动了大将军?”
“哦?是谁报你呀?”景将军面无表情地说道:“不过是曲乡一众义民想要来投军罢了,我已经把他们收了,安置在花儿坡营了。”说罢不再理会怔在一边的王平,径直回了大帐。
孙旭东他们先到几里之外的一片洼地,汇合了扎营在这里的余下斗士。替孙先生和旷引见了南宫之后,即在南宫的带领下,天刚亮时到了花儿坡。孙旭东记得当初景皓就是在这儿筑营时,中了白军的埋伏被俘到邺城的,此时只见花儿坡的军营依山傍水而筑,营前埋着鹿角竹签等防袭设施,四周都用高大木栅栏围住,很明显,在这儿筑营就是为了能以居高临下之势,封锁住营前一条通往鑫国纵深的大道。看来这些工作都是景皓被俘后,鑫军继续完成的。
花儿坡的守将陈伟是景监的心腹校尉,得了景监的将令,立即令军士在军营西边腾出了十顶大牛皮帐篷,安顿了孙旭东的人马。南宫一路上已经和孙旭东混得稔熟,此时见诸事已安置妥贴,便告辞回大营回复将令。
一同送走南宫,陈校尉过来客套了一番自去操练兵士。孙旭东等三人围坐在帐篷里,孙先生听完孙旭东述说昨晚的情形后,闭目沉思了片刻,说道:“不用说了,景大将军身边定有掣肘之人哪。”旷点点头:“我想也是这样的,不想让别人知道咱们的来历。”孙旭东眼光闪烁,摇摇头道:“我想还不仅于此,这其中的隐情现在实在难以看破。”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孙先生朗声一笑,“咱们不用瞎捉摸,景氏兄弟是旷古罕有之国士,有这一条就足够了。走,咱们去看看鑫国兵士的斗志如何?”
三人来到大营东边的操场,场里两千多兵士正在进行操练,对于这种大规模的排兵布阵,孙旭东虽然得到过景皓的一些指点,但那是纸上谈兵,还是不很熟悉。此刻得孙先生和旷在边上一一点评讲解,自觉大有收益。
看了足有小半个时辰,三人回到帐篷,立即展开讨论,孙先生是大行家,历数鑫兵操练中种种不足,以及将后实战中会因此带来的种种恶果。旷则在一边补露拾遗,孙旭东只有点头默记,偶尔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时,立即被孙先生批驳得体无完肤,让孙旭东闹个大脸红,这孙先生在用兵上确实太过厉害。三人海阔天空,慢慢又扯到了兵器的优劣上来,这下孙旭东大占上风,将孙先生和旷说得两口大张,惊诧莫明。其实孙旭东在这个上面已经用了很大的心思,自己是另外一个世界过来的人,那里现在用的兵器在这儿只要有一样就足以称王称霸了,只是得不到而已。
“铁制兵器取代铜制兵器是必然的。”孙旭东下了一个结论,准备结束这次讨论去弄点饭吃吃,然后补上一小觉。
“铁器粗糙不说,又脆而易折断,还不好打制,君武大人这个说法未免太过武断了吧?”孙先生求知欲甚强,兴头正高,不依不饶。
这个问题孙旭东想到了一些,这里还是一个青铜时代,铁器还只是用在什么铁链、铁栅栏或是某些粗糙农具上了,说明人们还没有真正掌握好冶铁的技术,自己虽然知道铁制的兵器比铜制好得多,但可惜在那个世界里也没干过铁匠这一行,对于冶铁这门技术也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但他相信,只要得一人相助,自己就一定能冶炼出适合打造兵器的精铁来。此人暂时还没找到,此时便故作神秘地笑道:“先生到时自知。今天休整一天,自明日始,您们二位就要开始训练斗士们了,不能总让他们歇着。大家既是来投军,就要守军规、军纪,先生要好好替他们讲讲,触犯军纪是要杀头的。我看这些天很多人都散漫了。好了,咱们该去祭祭五脏庙了。”
“君武大哥,你的衣服脱下来我帮你洗吧,我学会了呢。”孙旭东刚出帐篷,就听云公主一声脆生生的声音,她正和祠福媳妇一道在收斗士们要换洗的衣裳。云公主自失忆后,性情大变,所作所为让这些知道她底细的人经常瞠目结舌,不敢相信。她身后低着头站着的祠福媳妇,不时红着脸瞟孙旭东一眼。
随着公主的转变,孙旭东对她的看法也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毕竟是自己一巴掌把她打得像个白痴,以前的事都忘了个干净,虽然或许对她来说不一定是坏事,但对于有着现代心理常识的孙旭东来讲,还是知道失忆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常常会为了一个我是谁的问题想破脑袋。
“哦,不用啦。这儿有水吗?”孙旭东知道这个地方水属于紧缺资源。鑫国穷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于天干少雨。
“不要很多水的,我们都是一点点刷的。”云公主的笑脸极为灿烂。我靠,这一巴掌打的?孙旭东看着云公主心下歉疚,“不用替他们洗,他们自己也长着手呢,别累着了你们。”
“累不着,君武哥,那我们去了。”
孙旭东答应一声,回过头和旷、孙二人面面相觑,满脸的匪夷所思。
“君武大人请留意,军营里是不能有女人的。”孙先生望着她们的背影,提醒道。
“先生说的是,昨晚路上我已请南宫护卫回到田齐后,找户合适的人家,让公主住进去。再租间房让祠福把家安了,他们一家也是为我们而不能在田国立足了。”
孙先生欲言又止,过了一会儿说道:“君武大人心地善良,如此安排甚妥。”
第三日上午,孙先生手挥令旗正在军营西边空地上指挥着斗士们排阵,本来想过来看看笑话的陈校尉在旁边看了多时,嘴巴张得极大,眼看着场中这些身穿着乱七八糟服色的百姓动作虽不熟练,但随着令旗挥动演练出来的阵型真是千变万化,神秘莫测,不禁对那坐在二人抬的瘸子佩服得五体投地,这貌似一帮乌合之众的难民,竟被他**得有板有样。
一阵马蹄声响,前卫营放出的斥候骑马赶来,跳下马躬身禀报:“校尉大人,前营大道上一彪人马正冲大营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