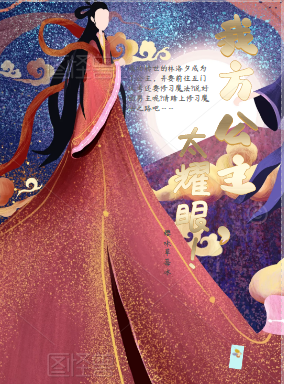一阵轻微的脚步声传来,打断了孙旭东的遐想,黑暗中一条黑影慢慢走近,从身形上看,好像是吊往这边走来。孙旭东连忙闭上眼睛假寐。
黑影到了跟前,踢了孙旭东一脚,轻声说:“起来,跟我走。”
确实是吊,孙旭东爬起身,全身酸痛。跟着吊往西走去,回头确定一下自己的草棚的位置,营中草棚众多,都是一样的式样,不要回来时弄错了。
到了奴隶营的尽头,围着的木栅栏上挂着灯笼,有兵士手持长矛在游弋。吊进了一个小些的草棚,孙旭东跟了进去。
这是一个有门的单身草棚,只有吊这样的工头级别才能享受得到的。最为难得的是里面竟有一盏菜油灯,地上铺着的是新草,很厚。比之自己睡的草棚,可算得上是星级宾馆了。
吊让孙旭东坐下,坐草铺下拿出一块破老布后撕成条状,帮他把铁镣和脚能接触的地方用老布缠上。孙旭东看着五大三粗的吊笨手笨脚地弓身给自己缠铁镣,脑子里映出了小时候父亲给自己系鞋带的情形。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上,除了大小姐和小山,每个人象是都对自己怀有敌意,眼下的吊竟如长兄慈父一般关照着自己,再也忍不住,顿时豆大的泪珠滚落下来。
吊为他缠好了铁镣,坐在草铺上,见孙旭东偷偷抹泪,嘿嘿笑了:“怎么像个娘们?是不是脚很痛?”
孙旭东眼望着满脸沧桑的吊,觉得他眉目间依稀有点像田青。心里估算着吊的年纪应该在三十岁左右。对于君武也就是眼前自己的确切年龄并不知道,但从景将军说的小小年纪来推测应该也就是十八、九岁吧,称吊一声大叔应不为过。
“吊大叔,我...”孙旭东想说些感激的话,一时却说不出来。
吊大手一挥,“知道我为什么要特别关照你吗?”
这正是孙旭东想知道的,他摇摇头。
“我也是鑫国人,原本住在都城咸城,是平民。”吊眼望着闪烁不定的灯火缓缓说道:“祖传的技艺,技兼冶桃(冶古代中打制箭镞、戈等兵器,桃专指铸剑),家里几代都在咸城的兵器作坊为国工。”
一听吊在说自己的身世,孙旭东暗暗高兴,因为可能会说到自己急于想知道的情况,连忙聚精会神地细听。
“自我祖父开始,我家便掌握了铸造加长铜剑的秘诀。一直以来就只为鑫国的王公贵族们铸造长剑,这原本可以让将士们在疆场大展神威的长剑,却只能成为王公贵族炫耀身份的腰间饰品。除了他们,如非王命,其他任何人都不许拥有加长的铜剑。”
吊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祖父渐渐厌倦了为他们铸造这没用的兵器,便封炉不再铸剑。可那些王公贵族们却不依不饶,逼着他开炉铸剑。祖父情急之下,推脱说以前能铸长剑是因为有剑仙附体,现在附体的剑仙走了,再也铸不出了。如此一说,那帮人也只好悻悻而回。那一年我十岁,我弟弟还不到两个月。”
“三年后,一位名满天下的剑士,从田国赶到咸城,求我祖父为其铸长剑。起初祖父一口谢绝,没成想剑士在我家门前跪求三日,不饮一滴水,不食一粒米,终昏绝在地。”
“祖父将剑士救起,赠金劝其回田。剑士又出门跪在门前,不饮不食,直到二次昏绝。祖父无奈,问他要长剑何用,剑士道他不满白王的暴政和一心兼吞天下的野心,要孤身犯险,求祖父为其铸长剑后去刺杀白王。”
“祖父思忖了一夜,只道剑士得剑后如果真能刺死白王,确实是为天下人除一大害,从此天下少了不少的纷争,各国无须再去穷兵黩武,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不正是铸剑桃工的最高王道吗?剑士要刺的人是白王,不也正是我鑫国多年的宿敌吗?”
“第二天,祖父开启了封闭了三年的铸剑炉,用了十几天的功夫铸出了一把加长铜剑。铜剑临出炉时,祖父喝令我父亲用木锤猛击其胸,吐前一大口鲜血喷于长剑之上为长剑发红。当时不懂事的我和弟弟在一边吓得大哭,因为以前的长剑发红都是用鸡血来做的。”
“剑士带着长剑离开了咸城,三个月之后,从白国都城邺城传来了有人行刺白王失手,当场自戕的消息。祖父暗暗叹息了一回,浑没想到此事给我家带来的祸患。”
“又过了两个月,白国十万大军压境,当年已入致政之年的老鑫王一向懦弱,原以为白王又是来索城要地,没想到白国十万大军只是要鑫国交出为刺客铸剑之人。”
“祖父所铸之剑天下无双,白国人一见便知。为一人而息干戈鑫王自是愿意从命,更何况还有几年前让祖父铸剑而未得的王公贵族们在一边煽风点火。当晚即派甲士围了我家,除了我娘带我外出得以幸免,其他一家老小近二十口子全部被抓,次日全部交与白国。”
“白国国君将我全家押到都城邺城,并未加害。只要我祖父开炉为他们铸剑,为剌客铸剑之事即可既往不咎。我祖父佯装答应,开炉时率我家男丁十三人纵身跃入烈火雄雄的铸剑炉。这其中就有我不到四岁的弟弟呀。”
灯光中,两行清泪从吊的眼中流出。如此惨剧,以前只在小说或是电视中看到过,眼下即活生生地在眼前,孙旭东也不由暗暗跟着他难过,看来人不可貌像,吊绝不是像他的外表一样的粗鲁汉子,他应该是一个身怀绝技、经历坎坷而内秀其中的人。
吊沉默了多时,张开大手抹去脸上的眼泪,继续说道:
“白王得知自是大怒,将我家女丁一律打成贱奴,永世不得脱奴籍,我娘得知后投井而死。自此后,原本三代同堂的我只得改名换姓,一个人四处飘零,不敢以家传技业谋生。直到二十岁才在济城落下脚,开炉为人打制农具度日。三年前白国侵占了济城,我被打为奴隶,在肩头烙下了印记,发到这儿修城墙。”你说完沉默了一会,用温和的目光望着孙旭东道:
“你嘴角的一颗痣很像我弟弟,他死的时候太小了,眉目我已淡忘了,只记得这颗痣,不过要论年岁你们应该差不多大。”
孙旭东恍然大悟,原本是君武嘴角的一颗痣让吊如此关照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只知道自己的脸变了,却还没有机会找到镜子一睹自己的尊容。看来嘴角有颗给他带来幸运的痣,让他想起了那颗著名的“幸福痣”。吊的叙述中带来了不少的信息,但他还想知道得更多。
“那我叫你大哥吧。”吊看起来很高兴地点点头,“那我认了你这个弟弟。你在家是干啥的?”
“我是放羊的呀,你不是叫我羊牯吗?”
“哦”吊呵呵地笑了:“这儿管捕来做苦工的奴隶都叫羊牯。”
“原来如此。”孙旭东也笑起来。“你是军奴,那是你父亲还是祖父被白国俘过?”吊又问道。
“...这个,我不知道。”吊诧异的看着他,“你家是在哪里?”
“嗯...”一无所知的孙旭东不如何回答,愣了半晌。吊见他吞吞吐吐,原本很热忱地望着他的眼光,慢慢变得冷淡:“哦,你不想说就算了吧。”
“大哥,我得了失忆症!”孙旭东脸上做出一片痛苦的表情,临时想出来一个搪塞之计。
“失忆?失忆是什么意思?”
“两天前我在山上放羊,被山石绊了一跤,跌倒时头在山石上碰了一下,醒来后以前的事都记不起来了。”
吊听着有些吃惊,问道:“事都装在心里,你的头碰一下怎么会忘了?”
古人以为记忆是存放在心里的,所以有心想事成等成语。这是个医学问题,孙旭东一时半会儿跟吊解释不清,只好答道:“我也不知道,只是醒来后心中一片空白,什么都不记得了。”吸取教训,这次他说心中而不说脑中。说完满脸诚恳地望着吊。
“哦”吊像是看着出土文物一般看了他一会儿,伸手摸了一下他的头,宽厚地笑了:“你总不会不知道自己叫什么了吧?”
“他们都叫我君武。”孙旭东见吊相信了,暗暗高兴,这下发挥的余地可就大了,无所顾忌,什么都可以问。
“大哥,现在是什么朝代?”这个问题很重要。
“看来你真是全忘了,倒是头一次听说摔一跤不掉东西掉心思的。呵呵”吊还是有些匪夷所思,“现在是什么朝代?现在是一个天下大乱、黑白颠倒、无廉无耻的朝代。”
这也太笼统了吧?一头雾水的孙旭东真想直接问现在是中国历史上的哪朝哪代?想想不能,对吊说道:“大哥,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你给我从头说说吧。”
“嗯,”吊答应一声,低头沉思了一会说道:“我们本应该都是大忌王朝的子民。四百年前,大忌王一统天下,那时天下太平,老百姓们安居乐业。大忌王为表彰有功的臣子,分封了一百零八个大小不等的诸侯。”
“被分封的诸侯,初时尚能相安无事,后来就经常有些纠纷摩擦。开始还有些顾忌大忌王,诸侯们只是小打小闹,两百年过后,大忌王日逐衰落,非但无力再干涉诸侯间的倾轧,连自身也朝不保夕,要看大诸侯们的眼色行事。自此诸侯们大鱼吃小鱼,每日里东征西伐,攻城掠地,用治下子民的鲜血和生命扩大自己的领地。百年一过,一百零八家诸侯中有的丢了领地成了人家的奴隶,有的被外姓分裂篡了侯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