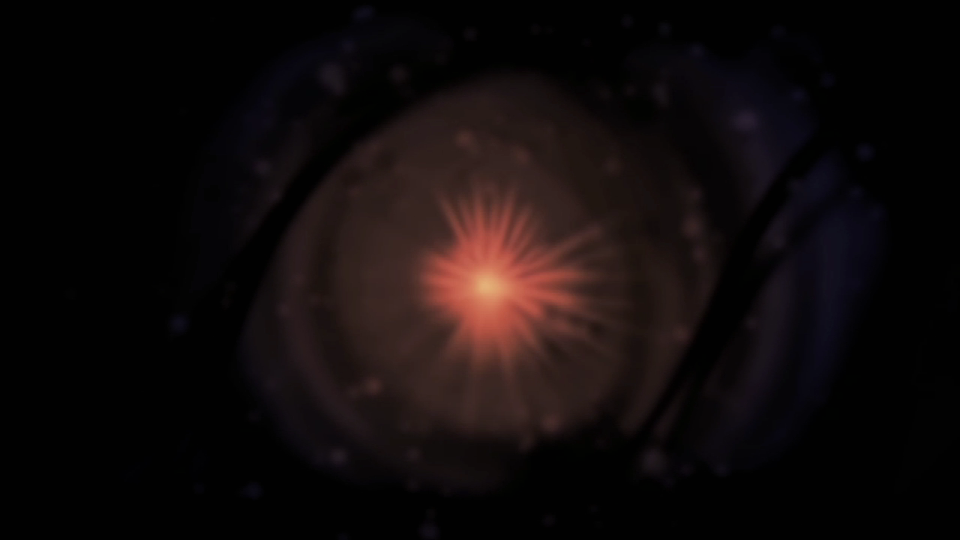送信的胡兵见震住了守营的兵士,两腿一磕放马冲进大营,四下张望就见一座大帐篷前树着一面半月形的旗子,门口还站着四名手按弯刀的卫兵,连忙一拨马头,来到帐篷前跳下马背说道:“有急信送月明公主。”
“好,把信拿来。”帐篷门前当值的是月明公主的卫队长,点点头大刺刺地说道。胡兵一怔:“带的是口信,我要面见月明公主。”
“口信?你哪个部的?有没有通行腰牌?” 公主并不是随便就能见的,队长皱着眉问道。
“老子这可是急信儿,误了事当心公主剥了你的皮。”那胡兵忽然变脸大声叫道,卫队长被他吓了一跳,不由勃然大怒:“去你妈的,敢跑到老子这儿充大,给我拿了。”
那胡兵见大话吓不了人,猛地抽出了腰刀,就听帐篷门口一声惊叫:“让他进来。”
卫队长眼睁睁地瞧着胡兵收刀进了帐篷,临从身边过时还对他哼了一声,紧接着在里面当值的卫兵都被公主退出了帐篷,心下不由大奇:这鸟兵从哪里冒出来的,还真他妈的横。
“毛怀,你们大将军没事吧?”帐篷里月明公主又是紧张又是害怕,连她自己都能感觉到说话的声音变了腔调。
毛怀此行冒着的极大风险,不光是怕被胡人识破,万一胡安丝托是虚情假意,毛怀就是自寻死路。此时见月明公主头一句话就是问大将军,毛怀一颗怦怦乱跳的心才放了下来,忙对胡安丝托行了礼才说道:“公主放心,大将军没事。”
胡安丝托长舒了一口气后双手合什,压在心中的大石被突然搬开,立时轻松得想哭,忍了半晌后两眼还是涌出了泪水,再跟毛怀说话时已是掩住的笑意:“你可真大胆儿,怎么会找得到这里?”
毛怀呆呆看着胡安丝托善变的脸,心中只觉奇怪,见问嘿嘿笑着答道:“毛怀是跟着狗找来的。”
*********************************************************************************************************************************
“大王,天大的喜讯啊”太叔公举着伯齐报捷的奏报,小跑着进了老鑫王歇息的偏殿,尖细的嗓音让正在闭目养神的老鑫王慢慢地睁开了双眼,眼见喘着粗气的太叔公孩子一般地兴奋,老鑫王微笑着问道:“太叔,什么事儿让你高兴得这样啊?”
“大王。”太叔双腿跪在卧榻前,高举着一封黄绢说道:“太子爷一战便灭了胡子万人,大王请看。”
“哦?”老鑫王接过黄绢,展开后眯着眼看了几个字又递着太叔公道:“哎,寡人眼睛越来越不中用了,你念给寡人听吧。”
“是。”太叔公答应一声,接过黄绢站起身,清清喉咙后将伯齐一篇花团锦簇般的奏报念得是抑扬顿挫,梁绕余音。
“嗯!”静静听到太叔公拖着长长的尾音读完,老鑫王惬意地缓缓靠在后背上,两只老眼盯着偏殿顶上的大梁问道:“伯齐的奏报是直接送给你的么?”
“一共是两份,还有一份送给了甘臣相。”
“哦,”老鑫王慢慢地闭上眼,像是自言自语道:“怎么不见甘臣相来啊?”
太叔公躬着身刚要答派人去请,就听殿门外甘虹的声音:“大王,杜城大捷。”老鑫王抬头看了太叔公一眼,表情怪异地嗯了一声。
甘虹一脚跨进偏殿门,见太叔公站在榻边手拿黄绢,心里暗恨一声:“果然这老阉狗手里也有一份。”表面却只是装作不知,跪下后面带欣喜道:“大王,太子爷神勇,杜城又传捷报。”
“嗯,寡人已经知道了。甘臣相请起。”老鑫王呵呵笑道。甘虹故意先作出一个惊异的表情,然后又作了一个恍然大悟之状说道:“一有天大喜讯,老臣都每每落在太叔公身后呵。”
老鑫王呵呵一笑道:“不能怪臣相,太叔跟寡人住得近些嘛。嗯,此次杜城大捷,伯齐自己虽有小功,所赖者还是部下将士一心,争相用命才能立此大功。臣相,就照这个意思拟诏,伯齐就算了,其他将士按例加倍叙功。”
“这。。。”太叔公惊倒在地,他深知伯齐为人,从不和属下争功。从奏报来看无论如何这一仗太子都是首功,绝不会是伯齐自吹。老鑫王如此办理岂不冷了太子爷的心?难道还有其他用意?
“太叔是不是为伯齐抱不平啊?”老鑫王见太叔公要说话,拦在头里说道,接着又冷哼了一声:“身为鑫国太子亲自提兵,劳师糜饷达上年之久才有此次大捷,寡人不怪罪他也就罢了,还能叙功?”
太叔公只觉老鑫王简直老糊涂了,自头前三月后,杜城捷报频传,虽然都不如此次功劳大,但起码不能说伯齐是在劳师糜饷吧。低头沉吟片刻还是跪下说道:“大王,自三月后,太子爷屡立战功,这都是有奏报可查的。。。。”
“查?你翻出来查查,寡人虽老,却还没老糊涂,先前哪一战不是景监派去杜城的那支。。。军打的头阵,还有,即如伯齐此封奏报,又何尝不是景监的那支军起了大用?”
一直在边上呆看的甘虹,此时笑吟吟地看着气极败坏的太叔公,心里却像是吃了蜜糖一般乐开了花。
跪在地上的太叔瞟了幸灾乐祸的甘虹一眼,将心一横,磕了个响头后挺直身子说道:“回大王,景监派去杜城的叫破虏军。破虏军有功,朝堂自当按例封赏,却不可因此抹杀太子爷之功啊。”
“放屁!寡人是他老子,怎么会抹了他的功?这大鑫国是谁的?自己保住自己的东西还有什么功?他要保不住这大鑫国将来说不定是谁的了,寡人的儿子又不止他一个,太叔,你明白吗?”老鑫王勃然大怒,起身喘着气大发雷霆之威,最后一问几乎是咬牙切齿。
“大王。” 尖细的声音里满是绝望,太叔公将头重重磕在头上高声叫道,抬起头只见老鑫王望着自己两眼似是要喷出火一般,心中不禁一阵战栗,双泪齐下。
“不要再哆嗦了!侍卫,将他叉出去!”老鑫王已气得手摇心颤,怒声呼过侍卫,将满脸是泪的太叔公扶下偏殿。
甘虹一时呆住,眼前的一切来得太过突然,除了处理谋逆之事,没见老鑫王发过这么大的火。眼见太叔公顿手锉脚,眼泪长流绝非假意,一阵巨大的惊喜让他一时无所适从,稍顷过后才急急跪下后又向前挪了几步:“太叔无状,大王切不可生雷霆之怒,气大伤身哪,大王。”说罢低头作戚戚状。
“唔!”老鑫王长出了一口气,慢慢靠在靠背上,缓缓说道:“臣相,太叔比寡人小十二岁,却已经老糊涂了,你比寡人小十岁,还没有老糊涂吧?”
“大王,太叔也是一时糊涂,还请大王恕罪。杜城大捷,老臣觉大王所处甚当。太子爷乃是人中龙凤,自当能领会大王激励之意,挥威武之王师,早灭胡虏以永靖我大鑫边患。”
“嗯。”老鑫王应了一声:“看来,你这个大两岁的反而没有老糊涂啊。这就下去拟招吧。”
****************************************************************************************************************************************
坐着双辕轺车上,甘虹皱着眉将偏殿里的事细细又过了一遍,再无可疑,一时只觉神清气爽,跟方才去王宫时满腹烦心事,真是恍如隔世。甘虹高兴不光是跟自己在朝堂斗了几十年的太叔公今日触了大霉头,更为高兴的是老鑫王对伯齐的态度。回到相府,下了轺车不见门前守值的奴仆也不以为意,来不及等身后的跟随,竟亲手推开了虚掩的大门,唬得刚出完恭回来的守值奴仆腊黄着脸跪在台阶下发抖,甘虹冷笑着哼了一声,对身后的跟随说一句:“要有人在朝房等,让他们午时后再来。”说罢迈步走向后院,心情一好性情大高,老甘虹此时只想去狐姬那儿抢个风暴。
跪在地上的奴仆一见,额头上立时见了豆大的汗珠,腊黄的脸霎时便惨白如雪,哆嗦着嘴唇只是说不出声。甘虹身后的跟随见了不免奇怪:“你奶奶的,相爷还没把你怎么的呢,怎么那副熊样,哎,哎,我入你奶奶的,怎么倒了?”
进了后院老甘虹真想闹上一嗓子二黄:几月处心积虑的图谋总算是没有白废,伯齐太子之位岌岌可危矣。此时回想起老鑫王那句‘寡人的儿子又不是他一个’,老鑫王已暗存废伯齐之心真是表露无遗。真要能将公子伯牙扶上王位,若干年后,说不定真让老鑫王今天说着了,大鑫国指不定是谁的呢。
伺候狐姬的一个小女奴听到动静,轻轻伸出头,一见甘虹脸吓得雪白,急急缩回头时却被今日眼清目明的老甘虹看了个正着,说了声“住了”,小女奴一惊想跑却终是不敢,迟疑着呆呆站住,等甘虹走到近前时两身望地,身子竟不停发抖。甘虹瞧了她一眼,心中疑惑:这小女奴长得极为标致水灵,老甘虹烦闷时也不时吃吃她的豆腐,摸个手捏个乳什么的,虽无床第之欢,但对她从来都是好脸色,不至于如此害怕。甘虹望了一眼后房,心中陡起警觉,瞪了那女奴一眼,蹑手蹑脚摸到了几十步外的后房。
刚到窗棂下,一阵娇喘便从窗缝中钻了出来,甘虹一阵惊诧后顿时气极,再侧耳就听狐姬气喘着娇哼:“爷,用劲,爷用劲啊。。。。”甘虹只觉双耳嗡嗡作响,全身的血液直冲头顶,一阵阵昏眩让两腿打颤,软得只想一屁股坐倒在地上,忙伸手扶住墙竭力站住才未跌倒,正在此时,房里一男子喘着粗气道:“来,狐媚儿,张嘴吃住,让爷舒坦舒坦。。。”,甘虹听罢,犹闻天上一声惊雷一般,慢慢瘫倒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