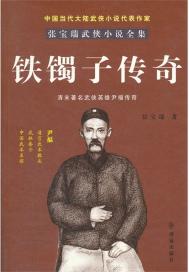秦书玉醒起来,忍住继续臭骂宥文的冲动,转头笑脸对着花泣:“宥文玩了个女人没给钱!”
花泣知道秦书玉在编瞎话,不想和他追根究底,她内心的痛楚散不去,没有心情去管宥文是干了什么,当然不会是玩了个女子不给钱这么简单。
宥文现在不缺银子,他是个商贾天才,精于算计,去一趟东平国不知给他顺带捞去了多少旁门左道的好处,哪能在乎那点青楼女子的皮肉钱!
“秦书玉!别净糟践我!”宥文怒了,虽然闯了祸事理亏,也不能被这么污蔑人格,兄弟开开玩笑可以,当着花泣的面可不行,这形象是要一落千丈的。
“你们继续吧,我回去了,哥,什么时候离开川口县,遣人捎个信给我!”花泣面无表情的说了一句,就起身出门,也不等秦书玉回话。
花泣独自一人穿梭在街上,偶尔被人擦撞一下也无甚知觉,一路上也不知被刮蹭了多少次,才回到川口县衙。
子俞还在前堂,低头处理着公务,听见脚步声,才抬起头见是花泣。
“吟儿,玩好了?”子俞微微含笑。
“嗯。”花泣低头应了声,就直接从一旁走侧门进后衙。
子俞觉得花泣似乎有些不开心,便放下手中的纸笔,起身跟在花泣后面。
花泣想着事情,没感觉后面有人,直直的回房,随后转身关门,把子俞夹在了门上。
花泣吓了一跳:“子俞?你什么时候跟在我后面的?夹痛了?”
子俞苦笑,进屋揽着花泣的肩膀,他高过花泣一个半头,把她裹着走,坐在榻前:“吟儿有事不开心?”
“没有,子俞你去忙你的吧,我很乏力,想躺一会儿。”花泣只想自己一个人静一静。
“想睡你睡就是了,子俞就在这看着你,要子俞抱着你睡也行,来吧!”子俞说着就要往榻上躺。
“我......头痛!”花泣是“有病”的,这“病”随时随地会“旧疾复发”,只要子俞赖在花泣的房里,必定是这里不好,那里不舒服。
“又头痛了?我去煎药。”子俞都躺在榻上了,一听花泣又犯病,立刻坐直起身,也不问花泣同不同意,出了房门就往后头去自己煎药,已经习以为常。
花泣不到不得已,不会轻易使出“旧疾复发”这招,不然每“复发”一次,子俞就煎药,那滋味......花泣其实喝的想吐!
花泣躺下,闭上眼睛就看见叶青林的样子,也不知秦书玉他们能不能照顾好他,按道理郎中会随时候命,但她就是心疼,疼的她连气都透不过来的感觉。
想当初她离开,是把叶青林往绝路上逼,迫使他写下休书,他是那么冷傲的一个人,都能强行改变了他自己的性子,低下头来哄她,她却依旧离开了他,还是用子俞打击的他,这种打击,可能一辈子也无法痊愈。
如今,他就躺在驿馆的病榻上,而她,只能在自己的房里思念他。
想了很多,想了很远,有前事有将来,却无法真正的面对眼前,她拼了命忍耐着,煎熬着,强迫着,让自己不要再去找叶青林。
子俞端着药碗进来,还冒着热气,药煎好了,这药,每次都要煎半个时辰以上,才能把药性熬出来,子俞熟能生巧,已经不是开始那个连炭炉都生不着火的二公子了。
花泣在榻上就睁着眼想叶青林,就已经想了半个多时辰。
子俞把药碗放在桌上,拿了扇子给药汤扇风,想凉的快些,一手用汤羹搅动,一手扇着风,这大冷天的,药很快就凉。
“吟儿,可以喝了,来!”子俞自己先试了试药汤的温度,觉得合适了,才端给花泣喝。
花泣皱着眉,她没病!不想喝药,但不得不喝!端着碗,磨蹭着。
“可是要我来喂你喝?”子俞见花泣端着不喝,以为是怕苦,看来是想给她灌下去。
“不用!”花泣一捏鼻子,咕咚咕咚几大口就吞了下去,估计连舌头都没沾湿,就已经进肚子了。
“来,吃吧!”子俞掏出了一颗炒糖块。
每次看花泣喝药那么痛苦,子俞思来想去,觉得肯定是吟儿怕苦,就问了县丞,有什么能使喝药的人嘴里不苦,县丞道那就加些蜜和糖,但可能会使药效变差,若真是怕苦,喝完再吃上一颗糖便行,子俞在集市逛了许久,才在卖糖人的那里,让他做了一些小糖块。
“这个?子俞真仔细,谢谢!”炒糖还是指头般大小一块的,从未见那里有卖过,花泣有些感激。
子俞当真是很仔细的一个人,他自小被府里宠着长大,生活都不需要自理,事事有人打点,来了川口县,当了官,独立了,也是真正成熟了,心思细腻,很体贴照顾人,花泣都要觉得自己上辈子是积了大德了,老天爷才会给她送个子俞在身边,可她却只能把子俞往外推。
冤孽啊!
“好吃么?”子俞笑笑看着花泣吃,感觉比他自己吃糖还要甜蜜。
“嗯,炒糖很香,我只见过炒糖做的糖人,各种糖样,人,牲畜,神兽,花草,没见过做成糖块的,这得多浪费啊!”花泣原本闷痛着,这下被子俞弄的又没这么伤怀了,开始肯叨几句。
“吟儿喜欢就好,那些小事就莫要去操心了,但是糖块也不能吃多,牙口会不好!”子俞的声音还是那么柔和。
花泣觉得,子俞就是那种你骂他,他也纹丝不动对你笑的人,你打他也打不下去的人,他总是这么温暖,对着他,让人很难会生出气来。
“子俞,看我,差点就忘了,想和你商量的,什么时候送牛下去各乡各亭,这一折腾,到现在才想起来。”花泣听见子俞说牙口的事,竟然能联想到牛吃草的牙口上去,想起原本就是去前堂找子俞商量这事的,结果秦书玉来了。
“我看呐,明日就送下去吧,正好,村民都在山上垦荒,可以把自家的牛赶到有草有树的地方,边垦边放。”子俞和花泣想到了一块。
“嗯,还有一个多月便是大年了,如今各乡各亭也不知开垦的怎么样,要先把秧田弄好,年后就要发种粮下去,不然秧苗到三月长不出来。”花泣就是个劳碌命,越想越远。
“吟儿放心吧,你刚才和书玉去逛集市那会儿,下面已经有好几乡都来人汇报了,村里大户些的人家,多的已经垦出了三四亩地,一两亩的也有许多,小户人家三五分田也基本都有,年前再垦上一个月,年后再垦一些,二月前,小户人家两亩以上,大户七八亩地是不成问题的。”子俞早就掌握了,就知道花泣随时会问。
“种粮呢?犁耙呢?买回来了么?”花泣要一样样问清楚,心里有数才踏实。
种粮是必须要有的,而且要足,要精粮,这个若是省了,来年不用指望有多少收成。
犁耙是耕田农具,这是犁和耙两样东西。
犁是在一根粗木头横梁端部安上厚重的钝弯刃,横梁的一头是另一条粗木把手,这边的前头捆着绳子,绳子两端再绑在一根短弯木上,弯木套在牛的肩膀,人只要在后面把犁刃插.进土里,掌握着把手,拿根竹条,轻轻鞭打在牛屁.股上,赶着前面的牛走,一手再拉着系在牛鼻环上的绳子,掌握着牛的方向,牛就拖动着犁往前走,这是用来破碎较大的土块,耕出槽沟的农具。
耙,在设计上和犁有些相似,只是在犁刃的地方改为粗铁齿耙,铁齿有十来条,有男人的拇指粗,比吃饭的筷子长些,先是用犁把土翻开,再把田里灌适量的水,用耙将土和水混合搅均,翻平整,让水田里的土变的细腻,同样需要牛来拉,才能减少农夫消耗体力和大大加快翻土的速度。
“犁耙已经到了,这东西好找,铁匠铺也有存一些,就是种粮要慢些时候,我们买的数量太大,只能找官家粮仓去买,需要层层上报,算起来,最快年底可以运来。”这么大手笔,子俞也有些压力。
“好吧,希望一切顺利,可别再出什么事了,子俞,你有没有怨我?”花泣有些不忍了。
“怨你什么?”子俞压根就不明白花泣是什么意思。
“怨我给你弄了这么大的摊子,让你忙前忙后,还担着风险!”花泣无奈的看着子俞,开始心疼他。
“吟儿你脑袋里总是装着些什么?竟有这种想法,我怎么会怨你?傻吟儿,是我害你劳累才是,人人都是夫在外,妻守家,而我却让你总是跟着东奔西跑,正打算以后就让你在家歇着呢,外面的事,我会做,你是女子,不能让你跟着我吃苦受累。”子俞伸手刮着花泣的鼻子。
在子俞的心里,他是夫,花泣是妻。
花泣也听见了,她不敢出口反对,随他吧,他喜欢怎么叫都可以,欠他的太多,花泣很希望子俞能够任性一些。
“不不不,子俞,我这个人,自小在乡野长大,轻骨头,就喜欢找事情做,不然就会闲的发慌,你让我跟着你去山上,我才感觉舒服,头痛也不会发了。”花泣就担心子俞会宠她到什么都不让她做,又拿旧疾说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