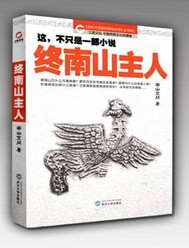子俞看了下被摁住的妖艳婆子,似乎有些眼熟,想了许久才想起来,这不是一直求着要来当厨娘的那个么?
就算不要人家当厨娘,也不用把人摁住吧?
子俞疑惑问道:“是这人偷东西让吟儿抓住了?”
花泣笑笑摇头:“子俞,你把她带去前堂,打上几板子,就明白了!”
子俞毕竟是堂堂朝廷命官,不能无缘无故把人抓起来先打一顿,但还是把妖艳婆子给弄去了前堂。
衙役把妖艳婆子往堂上一扔,不用打,婆子就自己招了。
傍晚时分,妖艳婆子不再妖艳,蓬头垢面,一身邋遢,爬着从县衙出来。
她是招完之后被打了五十大板的,子俞念她一把年纪没几年活头,才手下留情,能受下来五十大板已经是命大。
天擦黑的时候,同样蓬头垢面一身破烂的唐氏和她的婢子也被扔出了县衙。
花泣猜测的没错,是唐氏,动机明确,阴暗狠毒,只是可惜唐氏做的太没有技术含量,这么轻易就让她给揪出来,没劲。
明泫来县衙找子俞商讨两川口用地契书那日,子俞在前堂旁若无人的和花泣谈论两人的终身大事,撒了一地狗粮,让刚好从后面侧门经过的一个婢子给听了去。
这个婢子便是唐氏的婢子,唐氏那日刚好受了安氏掌嘴的气,满心怨恨,一听花泣和子俞在前堂谈婚论嫁,便失了理智,让婢子去外面买毒药,婢子害怕,去药铺门口晃荡半日也不敢进去买,怕被当场抓住报官,在街上晃荡来晃荡去,恰巧让妖艳婆子撞见。
这妖艳婆子平日专门走歪门邪路赚银子,见那婢子心事重重,很是好心问可是有什么难事,婢子觉着和这婆子互相不认识,也就不需要防范,把要买毒药的事给婆子一说,婆子呵呵笑的不停,就这样的胆子还学人家下毒害人,未免也太没用了。
婆子当即问婢子,肯给多少银子,她去买,婢子拿出唐氏给的一两银子,婆子两眼放光,告诉婢子晚些时候回来这个地方取货。
婢子按约定时辰回到那里的时候,婆子果真等在那里,用宽袖挡着,神神秘秘的给了婢子一个瓶子,里面便是婆子口中的毒药。
这毒药并不是婆子去药铺里买来的,第一她奢钱如命不想花钱,第二她也不敢,药铺卖出如砒霜那种东西,一丁点都要把祖宗八辈给问的清清楚楚才肯卖,要是婆子去了,指不定也给报官抓了。
但是能吃死人的这种东西,到处都是,城外那大路边水沟旁,偶尔会有几颗野山茄,婆子活了这把年纪,自然了解,这东西比砒霜管用,保管能毒死,毒不死也能毒疯。
交代了婢子,若想对方死的快些,就放半瓶,一口毙命,若是要人神不知鬼不觉的毒死,就滴出一小滴,拿一碗水匀开,再从碗里舀两勺子到饭菜里,这样就不会即刻毒发。
婢子把毒药带回来之后,唐氏便让她开始行动,时常去厨房,趁厨娘忙碌的时候,连着下了半个多月的毒,愣是没人发现,直到花泣头晕自己感觉出来。
花泣自己吃下毒药,加速毒发,整个后宅从上到下都被关了起来,子俞只好让衙役去街上贴告示招厨娘。
妖艳婆子也看见了,她的邻居进了县衙当了厨娘,夜里忙完回家时常会碰见,跟妖艳婆子说她的工钱有一两银子,妖艳婆子不信,那邻居只好说出县衙发生的事,才能让她有这么好运气,若不是县衙急于请厨娘,也不可能有这么高的工钱。
妖艳婆子明白了,她的毒药卖给了县衙后宅的人。
反复求着邻居带她进县衙,找县令大人说她也要去当厨娘,邻居被烦的无奈,只好从后门领她进去过几次,子俞去后厨给花泣端饭菜时,听说那妖艳婆子也想当厨娘,眉头紧皱,觉得她不合适给回绝了。
妖艳婆子时常从后门偷偷溜进来找她那邻居。
她不是真心想来当厨娘,而是想找买她毒药的婢子,想敲她一笔。
只要威胁那婢子若不给她银子,她就去向官爷告发,定能让人乖乖拿钱消灾。
只是来了多次,因为后宅的人都被关押着,她没见到人,就趁没人偷偷在后院一个个的屋子找,原本以为买她毒药的主子必定住正屋,才来到花泣纸窗外,徘徊了一阵又走了,她隐约觉得屋里有人,不敢随意莽撞进去看,万一里面的人不是买她毒药那个婢子的主子,她就难脱身,幸好后宅如今没什么人,她犹豫了一阵就赶紧走了。
回去想想不行,这么好的机会,不敲那婢子一笔,过了这村没这店,晌午过后,妖艳婆子又从后门溜进厨房找她的邻居,想问问,哪个屋子住的都是哪个主子,不想一进厨房门,就被花泣给逮住。
婆子本是为财,被衙役往堂上一丢,唯恐自己没了老命,没等子俞开口,自己就把什么都招了。
本想把这婆子按律发配,念她一把年纪,发去哪里必定死在哪里,干脆就让她领了五十大板,若她能坚持下来,就算她命大,婆子被打完还真就没死,自己爬走了。
婆子指认出来的婢子,就是唐氏的婢子,开始还给唐氏担着,只道是她一人所为,与唐氏无关。
子俞心里有数,定是唐氏给了婢子银子送回老家安置,才能让她出来顶包,主簿拿来律例,大声念道,若在婢子的老家搜出来路不明的银子,全家送官,婢子才哆嗦着承认了是唐氏指使。
唐氏自知子俞不会姑息她,自始至终也不愿意开口。
主仆二人被打了八十大板,丢出了县衙,让她自生自灭,同时扔出来的还有休书一封。
算是手下留情了,也幸好花泣没事,不然唐氏便是谋杀,得偿命。
唐氏在宁阳城的娘家,子俞也派了人去告知,从此她是生是死,与他再无瓜葛。
后宅的人都被放了出来,各归各位,谁也不敢提起这事,谁也不想再招惹是非。
果然如花泣想的那样,后宅果然就安宁了。
安氏很感激花泣没有落井下石,若是花泣强行将这罪名摁在她身上,大约她也就只有含冤承受,这才放出来,就立马来到花泣榻前侍奉。
有人的时候,花泣总要装装样子,让人觉得她的病并没有完全好,只是快了,好歹有个过程,安氏伺候的更是尽心尽力,生怕花泣不悦,哪日自己就大祸临头。
她从一开始的怨恨花泣,到如今只剩下惧怕,是生与死的考验,不由得她不服。
只要花泣能容下她,在这后宅,不当主母也当真没什么,什么主母,夫君承认的才是真主母,哪怕花泣和子俞果真圆房,她如今也不敢多做他想。
......
天日渐冷起来,十一月初五,冬至,宥文回来了。
这趟派他带着十个人去了东平国买牛,足足走了一个月余,赶回了一千五百头牛,据说东平国的牛贩子还帮忙一直送到两川口,如今都在城郊让一众衙役看管着。
宥文痩了许多,花泣见到满脸风霜的宥文时,直道再也不让他去了,赶明儿派别人去,宥文却呵呵傻笑,道还是派他去好些,他走了一回,熟路了。
花泣获子俞准许,去了城郊看那一千多头牛。
子俞扶着花泣从马车上下来,花泣望过去那一片有黑有黄低头吃草的牛,心里一激动,蹦跳着跑了过去。
子俞连忙把她抓了回来。
“吟儿,你忘了自己还在生病了么?”子俞故作生气状。
“啊?对啊,我在生病。”花泣刚才确实是忘了,幸好子俞知道她的性子,没心没肺的,也不放在心上。
只好改为病态的步伐,小心的接近一头黄牛,不敢太深入牛群里,怕牛万一受惊起来,一冲一撞,会把她给踩扁。
这么冷的天,绿草还是比较少,只有在近河边的湿地,还有一些顽强的绿着,边上没水的地方,早就枯黄,但牛不挑食,就是干草,也能吃下去,还让衙役去乡下收车干稻草来,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可以给这些牛吃。
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说的不是它们,这些只是寻常耕地的黄牛,有些毛色深些,深到黑色,它也叫黄牛。
这些牛便宜,在东平国,一两银子可以买两头健壮的母牛,公牛更便宜,三百五十个百铜子一头,不知东平国那些牛贩子从北国贩来之时得有多廉价。
县丞很会选地,这块地方,有条小河穿过,水草丰美,对岸上面是山坡,牛也能上去,只要把周围用栅栏围起来,牛在里面就不会走丢,衙役轮班看守,想也没有贼人敢来偷牛。
宥文精啊,不愧是从桃源村出来的,知道买牛不能买太多公牛,日后发下去给各乡各亭,每个村子的公牛只能有一头,其余的全发母牛。
为什么?一个村子有两头公牛,碰见了就会互顶打斗,然后打输的那头就会从哪个山上被顶下去,摔断骨头,最后只能在山里活活的宰了吃肉,没办法,断了骨头的牛,是不可能再好回去继续耕地了。
母牛也不是完全保险,冷不防一个怀了牛崽子,就被娘娘一样供着,不能下地了,所以公牛少,控制起母牛来也心里有数,排队轮着来。
花泣美美的看着这群牛,决定过几日就先给一些村子发下去,让农户自己去山上边垦荒边放牛,减轻县衙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