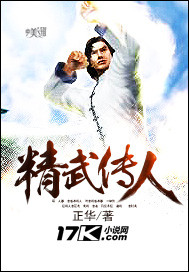新年终归是热闹的,单是那烟花爆竹声就已经足足影响了满路两晚的睡眠。什么叫有人欢喜有人愁,这就是啊。
熬到大年初二,她困到记忆力也衰退,连回娘家这么要紧的事也忘得一干二净。还是陆园林叫她起床,她一时想不起,迷迷糊糊还问:“你起这么早干什么?”
陆园林吃了一惊:“忘了吗,今天要回家啊。”
“哦。”打算埋头再睡。
“啊!”顿时清醒从床上跳起来,“几点了?”
“你还有二十分钟。”陆园林在一旁看热闹。
她这才争分夺秒开始行动。
才上车又犯困,嘴上嘟嘟哝哝:“这儿的人过年实在太热情了,”认输说,“我真有点吃不消啊。”
陆园林帮她系上安全带,戏说:“现在知道了吧,我能活下来也不容易。”
噗嗤,满路忽的一笑。这人总是有意无意戳中她的笑穴。
低头看见她顶着两只硕大的熊猫眼,眼皮都快撑不起来,一时有些疼疚:“再睡会儿,从这儿回去至少也要三个小时呢。”说完便驾轻就熟地从身后抽出一张毛毯盖在她膝上。
满路整个人瘫软在副座上,微微侧着头,含了情看向他。
他总是把一切都安排周全,叫人无可挑剔。满路总觉得这是她几生几世修来的福报。她素来不是妄自菲薄的人,可他终究是太好,太好太好,好到她常常疑惑,他这样出类拔萃的人,为何偏偏停在了她这里?
“懒虫又怎么啦。”他漫不经意问。
满路瘪嘴不答,抬手拂过他的脸,无由的娇嗔满面:“幸好有你。”而陆园林只是含笑摸摸她的头,什么也没有说。
到家的时候已经快早上十点,满路中途醒了再也没能睡着,一路找了许多话跟园林聊,她每说一句,他就淡淡地笑,常是慢半拍地应着。渐渐才忘了疲累的。
“哎你分我一点儿。”下车了她突然说。
“没事儿,不重。”陆园林动了动眉梢,从容吐出。
“那不行!”满路说,“待会儿我妈又得教育我,说我成天就知道欺负你,我可惹不起。”
她每一次给家里打电话,方兰都千叮咛万嘱咐,说,陆园林这样子温和的脾性,定不是讲不得道理的人,若是真吵架准也是他先败下阵来,所以啊这样举世无双的好男人,她不能恃宠而骄,得好好对人家。
园林也知道她没少被说教,笑把一瓶酒递给她:“好吧,这个给你。”
她如愿以偿接过,前脚刚踏入电梯就提醒园林:“待会儿我哥肯定会跟你要红包,他这人啊三十岁了还跟个小孩似的,贪玩爱闹,只有叶姐治得了他。”
陆园林则淡定笑了笑:“放心,我都准备好了。”
“啊!你还真的当真啊。”
“这是他应得的。”他情深意长望向她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她泄气,罢了罢了,他和舜禹的革命友谊深厚得很,又岂是她能够体会得了。于是摆摆手出了电梯按门铃。
是舜禹开门。
“新年快乐啊林妹妹!”她学他:“新年快乐啊林哥哥!”
“舜禹,新年快乐!”陆园林从不唤他哥,他和舜禹本就沆瀣一气,说起来舜禹也就比他大了那么一点儿,两个人又都不拘小节,无所谓尊敬不尊敬。可舜禹这回却嘲谑:“新年快乐啊妹夫!”
人就堵在门口,所谓百炼成钢,满路一眼识破他的把戏,回眸笑看了眼陆园林,神气十足说:“我厉害吧!”
陆园林抿唇轻笑,掏出一个鲜色的大红包,上面烫着喜庆的一个“贺”,递过去说:“请笑纳。”
林舜禹这才称心如意放行。
林培良和方兰正在里间厨房做饭,只听见流水哗啦啦的声音,对外头的事一概不知。
“爸,妈,新年快乐!”满路和园林这下倒真的心有灵犀。
两人回过头一看,林培良先反应过来:“哟!”
“来啦!”方兰擦了擦手,解下了围裙。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林培良和方兰也步调一致。
陆园林又摸了摸口袋,掏出与方才一模一样的两个红包,毕恭毕敬地呈到二老手上,一脸诚笃地笑:“爸,妈,这是满路和我的一点心意,祝愿您们身体安康,福寿绵长。”
“哎哟,这!”芳兰为难地看向林培良。
林培良说:“既然是孩子一片心意,我们就别推了,收下吧。”
满路没料到陆园林把林培良和方兰的份儿也算上,还把自己的功劳也随了进去,事事做得周到却从不曾告诉过她,只是默默地,默默地自觉。
他给她的,从来都是温暖而踏实的安全感,是伸手就触碰得到的真实。在她浴火却不得重生的时候,谁也没有料到,赤焰和坚冰竟会不期而遇。他炽盛且热烈,却偏偏遇上一颗虚弱而荒凉的心。却没有逃。
那时候她已是千疮百孔,绝望使她放弃了挣扎,她就那样奄奄一息地沉静无比地等待着上天最后的宣判。她以为心底的窟窿会越长越大,直到溃烂,直至再也摸不着心脏在哪里。而他缓慢沉着,像个强大的光源体,不管她驻足在哪一个街头,总能感受到他小心释放着的光亮和温热。
他是光。
“舜禹,去烧菜!快快快!”方兰说,“我和你爸要跟你妹妹还有园林聊聊天儿!”
“妈,我是不是你跟爸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舜禹丧气地说,“怎么就这么差别对待啊。”
“去去去!话真多!”林培良也催他。
“你怎么不让我也聊聊天儿啊。”边走边嘟囔。
“净知道贫嘴!”方兰目光追着他的背影,下一秒又变回慈祥的母亲,“园林,来,吃水果。”
“谢谢妈。”陆园林颇感同情地低笑。
林培良精细地将满路端看一番,问:“这才多久不见,怎么越来越瘦了?”
陆园林听了后指控她:“吃的比猫崽子还少,说破嘴皮也不听。拿她没办法。”
满路正低头喝茶,半晌才醒悟在说自己,于是也自上而下打量片刻,朝林培良说:“哪儿有,明明胖了。”
“爸,你眼花啦。”满路笑他。
“哪里胖了!跟竹竿子似的,风一吹就倒了!”方兰插话说,“老是游思妄想,就不让人省心!”
“妈,大过年的你还骂我。”她嘀咕。
“大过年也得骂!该骂!年后你把工作给辞了,老老实实给我回家呆着!我问过几个中药医师了,给的方子都差不多,你回来,把身体养好再说!”
“妈,你又来了。”她简直要哭,“这跟我工作没关系。你别自己吓唬自己,弄得草木皆兵的。”
“再说了,我这不是随你嘛,天生。”
陆园林好笑又好气地瞥着她。
“我说不过你。”方兰赌气说,“反正工作要比你身体重要,比爸妈的感受重要。”
她听了心里一凉。
“哎哎哎,行了行了,别说了。”林培良在一旁规劝。
使力揉揉眉心,满路哑口无言。这下真是负薪救火,自取灭亡。
“妈,您把方子告诉我,我来熬,一样的。”陆园林忙补救。
“这怎么行!你工作这么忙,哪还有时间给她熬药!”方兰说,“这药啊都要慢慢慢慢地熬,用温火熬,这样出来的效果才最好!你忙起来没日没夜的,请阿姨熬我也不放心,我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你就别操心了!”
“我不忙。”陆园林说,“年前我已经跟公司申请减负了,公司同意了。”
满路吃惊地看他一眼,这人真聪明,他这么一说方兰肯定没意见。
“这下你放心了?”林培良语气无奈,“孩子难得回家一趟被你唬得大气都不敢出,你看看,你自己看看。”说完顺手指了指满路。
满路暗松了一口气,抬眼朝方兰无辜地笑:“我去看看哥做得怎么样了!”溜的时候倒是健步如飞。
方兰指了指厨房的方向:“看看,都是你给惯的!”
林培良不做声,只低头闷笑,想了想推脱责任:“都是园林给惯的!”
陆园林闻言好笑,仍然一副宠辱不惊的面容,心上却陶醉难以自拔。都说女儿是父亲上辈子的情人,满路和他说,在他们家一直都是方兰唱红脸林培良唱白脸,以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其实他也很想要一个女儿,五官最好是像她。之前他不经意跟她提过,她抗议说:“我不要生女儿。”
他问:“为什么?”
“我傻啊,好端端的干嘛生个女人出来和我争宠。”
他霎时无语,被气得喑哑。她见状大发慈悲说:“生儿子我可以考虑一下。”
“我反对。”轮到他有意见。
“那怎么办?”
“不生了。”他说。
“附议!”她转瞬化作一脸促狭的笑,又有些得意,他幡然醒悟,上当了。
可心髓始终甜洽。他招认,他贪恋这样患得患失的她,有欲有求的她。才像个俗人。他希望她做个俗人。
“开饭啦!”舜禹探出脑袋播报。
满路在一侧嫌恶说:“中年大叔惯有行为之一,说话偏爱歇斯底里。”
“林满路,问你一个问题。”他居然没有暴跳如雷,反笑得和气,“你见过打女人的男人吗?”
她苦心思量,刚想说没有,顷刻觉悟过来拔腿就跑。
舜禹的厨艺比之陆园林不分仲伯,她以前总觉得舜禹不去当厨师真是可惜。
于是趁机讨好,谄笑说:“哥,你烧的菜越来越好吃了。”
“你少来。中年大叔可没这么容易讨好。”舜禹鄙视她。
林培良半啼半笑着摇头,司空见惯。陆园林也窃笑,把凉瓜夹到她碗里,顺便教育她:“你再兴风作浪我们就要成为众矢之的了。”
“瞧瞧,这才是明白人。”舜禹嘚瑟说。
“是啊是啊。”她说,“我不是明白人。我这就打电话叫叶姐别过来了,省得有的人啊嫌我多管闲事。”
舜禹啊地弹起来,诧愕若呆子,将信将疑:“真的?你真把她叫来了?”
“千真万确。”
“我求了老半天也没见她答应,你怎么说动她的?”
“那你得好好反省反省了。”她正经八百道,“我跟她说我回来了,她自告奋勇说要来的。”
“唉。”他深受打击,颓丧说,“凄凄惨惨戚戚,怎一个愁字了得。”
方兰笑:“叶子是好久没过来坐了。”
满路怜悯地拍拍他肩膀,指着满盘佳肴:“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