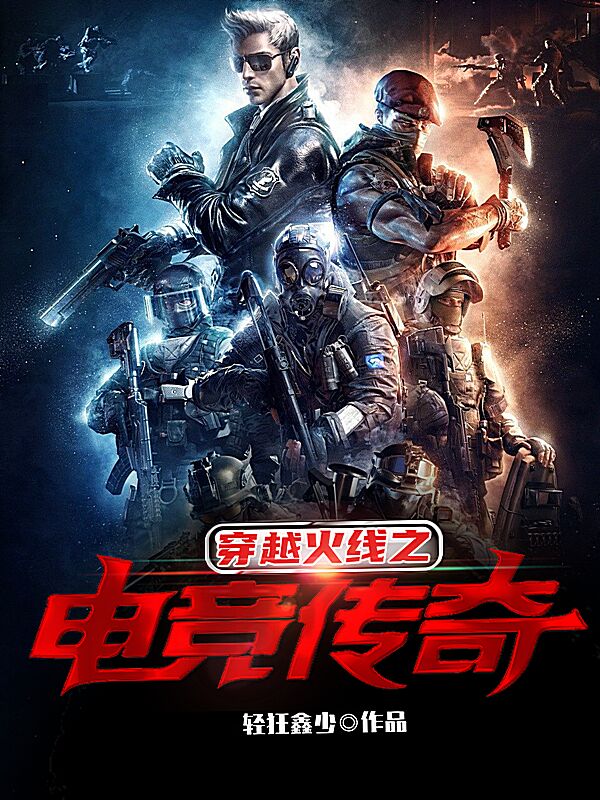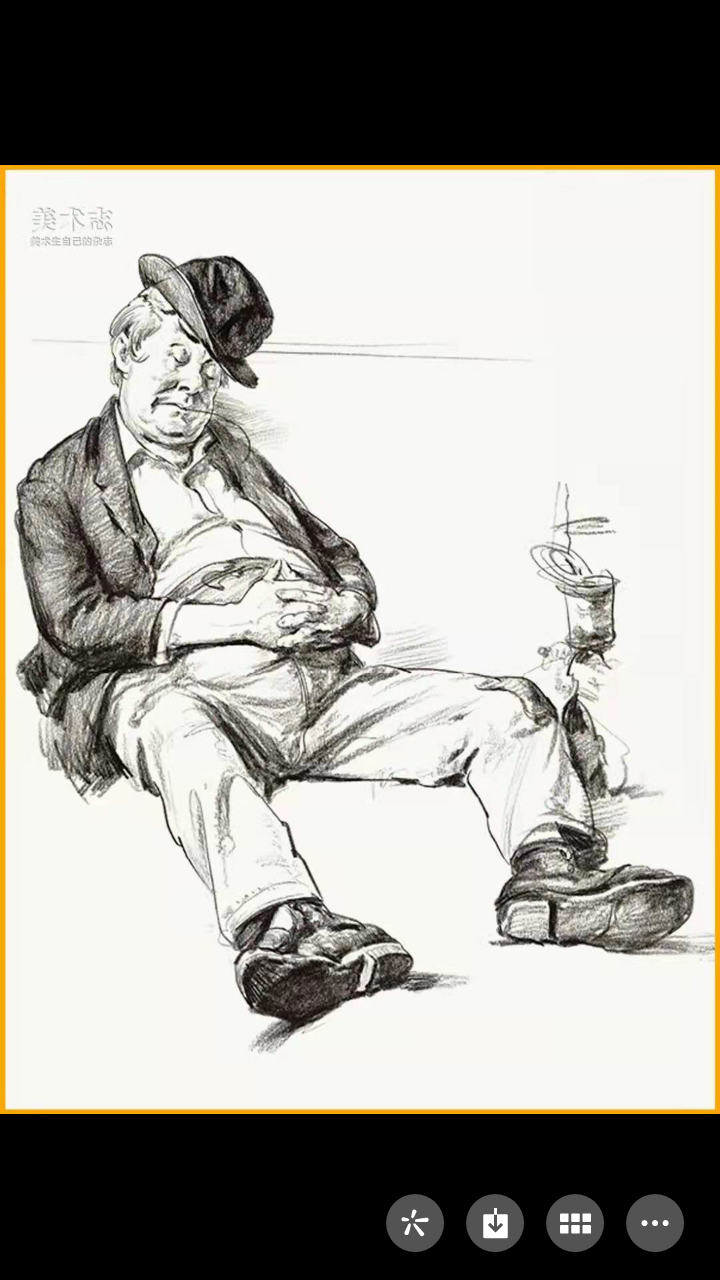却说梁太祖朱温整日在宫中无所事事,闻听中书令张全义在府内修造避暑花园一座,名曰“会节园”。朱温便下令召张全义入宫来见。朱温一见张全义问道:“张大人你好雅兴啊!”
张全义伏地言道:“臣年老愚昧难解陛下圣意,请万岁明示。”
朱温道:“前方将士浴血拼杀,爱卿却斥资修造会节园,挥霍无度,是真的吗?
张全义一听此言吓得魂不附体,但又脸色一变笑道:“陛下所言不假,为臣所建会节园乃为圣上开心解趣所造,圣上不往御用,为臣岂敢玩乐其中。”
“哦?”朱温一听此言又问道:“果真是为朕所造?”
张全义言道:“臣确是为陛下所建,只是尚未寻得美姬,故未敢邀陛下圣览。”
朱温大笑道:“爱卿真乃朕竑股之臣,传旨起驾,朕要亲往会节园一游。”朱温遂起驾出宫,张全义却是吓得冷汗倒流。
朱温来至会节园,观其园景别致非凡,亭台楼阁、枕山引水、泉石轩榭、花木禽鱼点缀的幽雅神韵,青林斜影,绿水浮纹。正是:
亭台溪流映古松,
青石小径意幽浓。
碧草点落黄鹂鸟,
群花绽放满园红。
翠园艳色春尚早,
惟见异境独不同。
忘却三军枕戈月,
只愿醉卧冥冥中。
全义家世濮州,曾从黄巢为盗,充任伪齐吏部尚书。巢败死,全义与同党李罕之,分据河阳。罕之贪暴,尝向全义需索,全义积不能平,潜袭罕之。罕之奔晋,乞得晋师,围攻全义。全义大困,忙向汴梁求救。朱温遣将往援,击退罕之,晋军亦引去【这是前事。如今全义、罕之皆归朱温】。全义得受封河南尹,感温厚恩,始终尽力,且素性勤俭,教民耕稼,自己亦得积资巨万。特在私第中筑造会节园,枕山引水,备极雅致,却是一个家内小桃源。朱温篡位,授职如故,全义曲意媚温,乞请改名,温赐名宗奭,屡给优赏。及温到他家避暑,自然格外巴结,殷勤侍奉。
温一住数日,食欲大开,色欲复炽。默想全义家眷,多半姿色可人,乐得仗着皇帝威风,召她几个进来,陪伴寂寥。第一次召入全义爱妾两人,迫她同寝,第二次复改召全义女儿,第三次是轮到全义子妇,妇女们惮他淫威,不敢抗命,只好横陈玉体,由他玷污。
一日朱温召见全义,信口言道:“朕的御驾来府,爱卿为何不唤正室来见?”
张全义心中一惊,心想这皇帝要见自己的夫人可如何是好?赶忙言道:“启禀万岁,臣之糟糠已有五旬,人老珠黄恐惊圣驾。”
“放肆!汝敢抗旨不遵?!”朱温怒道。
“臣万万不敢!”张全义道:“臣谨尊圣命,请万岁稍候片刻。”
张全义走出会节园是满脸愁闷,心中暗想如何是好?也罢,大丈夫能屈能伸,忍字心头一把刀,忍了吧。张全义胡思乱想之际已到夫人储氏的卧房。夫人储氏见张全义满面愁容便问道:“老爷何事忧愁?”
“夫人呐,全义对不住你呀!”说着张全义屈膝跪倒,储氏赶忙问道:“老爷这是何故?”
张全义言道:“当今万岁驾幸会节园,要夫人往内阁侍寝。”
“啊!”储氏骂道:“你这老不死的,非要建什么会节园,如今要让我失掉这一世的清白……”
张全义哀叹道:“夫人,你就顾全大局吧。夫人若是不去,我这一世功名革去不说,只是这抗旨不遵也可株连满门呀。”储氏哭泣片刻才点头应允,只得浓妆艳抹,强作笑脸去会节园侍寝。小阁之内,男欢女乐,水**融,张全义无力地坐在青石之上唉声叹气。正是:
枉费金银失妻妾,
会节园内难保节。
逞得富贵多无益,
才知今日自作孽。
张全义正呆滞之时,忽见其子张继祚冲冲提刀而来,张全义问道:“我儿提刀来此做甚?”
张继祚怒道:“方才闻侍人言朱温逼母亲侍寝,天子既无人伦之理,何不杀此暴君以谢天下!”
全义硬行扯回,且密语道:“我前在河阳,为李罕之所围,啖木屑为食,身旁只有一马,拟宰割饲军,正是命在须臾,朝不保夕,亏得梁军到来,救我全家性命,此恩此德,如何忘怀!汝休得妄动,否则我先杀汝!”【救命之恩用妻女相报,也是奇闻。】继祚乃止。
越宿,已有人传报朱温。温召集从臣,传见全义,全义恐继祚事发,吓得乱抖。妻储氏从旁笑道:“如此胆怯,做甚么男儿汉?我随同入见,包管无事!”遂与全义同入,见温面带怒容,也竖起柳眉,厉声问道:“宗奭一种田叟,守河南三十年,开荒掘土,敛财聚赋,助陛下创业,今年齿衰朽,尚能何为?闻陛下信人谗言,疑及宗奭,究为何意?”朱温被她一驳,说不出甚么道理,又恐储氏变脸,将日前暧昧情事,和盘托出,反致越传越丑,没奈何假作笑容,劝慰储氏道:“我无恶意,幸勿多言!” 储氏夫妇,乃谢恩趋出;朱温也未免心虚,即令侍从扈跸还都。
一日朱温泛舟九曲池,池不甚深,舟又甚大,本来没甚危险,不料荡入池心,陡遇一阵怪风,竟将御舟吹覆。梁主温堕入池中,幸亏侍从竭力捞救,方免溺死。别乘小舟抵岸,累得拖泥带水,惊悸不堪。
时方初夏,天气温和,急忙换了尤袍,还入大内,嗣是心疾愈甚,夜间屡不能眠,常令嫔妃宫女,通宵陪着,尚觉惊魂不定,寤寐徬徨。梁主病不能兴,召语近臣道:“我经营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余孽,猖獗至此,我观他志不在小,必为我患,天又欲夺我余年,我若一死,诸儿均不足与敌,我且死无葬地了!”
语至此,哽咽数声,竟至晕去。近臣急忙呼救,才得复苏。朱温只怕晋王,谁知祸不在晋,反在萧墙之内。嗣是奄卧床褥,常不视朝,内政且病不能理,外事更无暇过问了。
朱温连年抱病,时发时止,年龄已逾花甲,可一片好色心肠,到老不衰,自从张妃谢世,篡唐登基,始终不立皇后,昭仪陈氏,昭容李氏,起初统以美色得幸,渐渐的色衰爱弛,废置冷宫。陈氏愿度为尼,出居宋州佛寺,李氏抑郁而终。此外后宫妃嫔,随时选入,并不是没有丽容,怎奈梁主喜新厌旧,今日爱这个,明日爱那个,多多益善,博采兼收。甚至儿媳有色,亦征令入侍,与她苟合,居然做了个扒灰老。
一日朱温装作重病不起,博王友文、福王友璋、均王友贞、贺王友雍、建王友徽、康王友孜纷纷前来探视,朱温对诸子言道:“朕身染重病,左右伺候不周,朕令汝等遣王妃伺候龙驾,以尽孝道。”几位王爷一听,知道朱温心术不正,但又无人敢言,只得遵命。两个时辰之后,六位王爷领来七位王妃,其中一位乃是郢王朱友珪之妻张氏。朱温遍观众儿媳,见朱友文之妃王氏,朱友珪之妻张氏容貌俊美,淫心大发,乃令张氏、王氏二妃留宫中侍寝,其余儿媳各回王府。朱温当夜令二位王妃与其共寝德寿宫,此后由两位王妃轮流陪驾,其她王妃容貌一般,朱温也不要求她们尽孝了。
朱温在宫中与两个儿媳*,柏乡大战却惨败而终。监军朱友珪与都督张归厚带着败报惶惶回城,二人自知此番大败必遭朱温重罚,所以提心吊胆地往宫中请罪。刚进内宫,小太监拦住二人去路问道:“郢王殿下何往?”
朱友珪答道:“小公公速禀报父皇,朱友珪有十万火急军情要奏。”
小太监言道:“殿下有所不知,张王妃正在服侍皇上,不可惊驾。”
“啊!”朱友珪得知妻子在宫中陪驾朱温,顿时两腿发麻,瘫坐在地。小太监与张归厚赶忙搀扶朱友珪。朱友珪惨淡言道:“前番兵败柏乡,而今父子争妻,友珪必死无疑了。”
张归厚问道:“殿下平日与王妃夫妻情义如何?”
朱友珪答道:“情义尚好。”
张归厚言道:“殿下无忧矣,若张氏在圣上面前为你求情,则不会怪罪战败之事。” 朱友珪闻听此言才心中一块石头落地。此时有人来报皇帝与郢王妃回驾德寿宫,朱友珪才哆哆嗦嗦前去见驾。
朱友珪与张归厚跪在德寿宫中待罪,朱温身着内衣从屏障之后走出,问道:“柏乡战事如何?”
朱友珪答道:“孩儿死罪,大军折损三万余众,损失战马五千匹。”
“啪!”朱晃拍案大怒道:“若不斩汝二人,焉能对得住阵亡将士?来人将朱友珪、张归厚推出午门斩首!”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听屏障之后有一女子言道:“父皇且慢!”接着屏风之后缓缓走出一位美貌女子,身着衬裙,肩背裸露,此人正是朱友珪之妻郢王妃张氏。张氏玉婉扣住朱温右臂,脸颊抚慰朱温脸庞,柔声劝道:“父皇看媳妇之面饶过友珪,再战之时令其将功补过不迟。”
朱温顿时转怒为乐:“朕之儿媳真乃贤德之女,看你面上饶他一回。友珪还不谢过王妃。”
朱友珪差点儿没把嘴唇咬破,心中暗想这让我如何拜谢?妻子与我父皇交欢,我不能喊夫人,却又是我的正房妻子,更不能喊母后。情急之下只得按太监们的叫法喊道:“朱友珪谢过王妃娘娘!”
朱温言道:“今日天色不早,就令张妃回王府与友珪团聚,传博王妃今夜侍寝。” 朱友珪这才明白原来带绿帽子的人并不是他一人,还有他兄弟媳妇。
朱友珪与张氏回到郢王府,夫妻二人将房门一关,朱友珪一把将张氏长发揪住,满脸凶煞地骂道:“贱人!老子阵前卖命,你却与父皇通奸,今天我非把你打个皮开肉绽!”
张氏一把挣开朱友珪,毫不惊慌地说:“朱友珪你有本事打死我,到时老头子非杀你不可。” 朱友珪一听这话又软了下来,,怒气冲冲地坐在一边言道:“此等*之事若是传出去,岂不被天下人笑话。”
张氏却说道:“亏你还是帝胄之后,皇族血脉。岂不知有失必有得,有弊就有利。”
朱友珪惊讶问道:“此话怎讲?”
张氏言道:“昨夜我在父皇枕边百般夸奖你,父皇已向我许诺,决定将皇位传与郢王。”
“蹭!”的一下,朱友珪从椅子上蹦起来问道:“夫人此言当真?”
张氏附耳言道:“女人枕边风威力无比。” 朱友珪顿时奸笑起来。
朱晃送走张氏,又迎来王氏。王氏哄弄朱晃颇有功夫,令朱温如醉如死,一阵云雨之后。朱温困倦欲睡,王氏依偎朱晃怀中问道:“自太子朱友裕归天之后,陛下尚无皇储,不知陛下可选继位太子?”
朱温言道:“朕已决定立郢王朱友珪为太子。”
王氏赶忙言道:“父皇好生偏心,那博王友文虽是养子,但自幼追随父皇如同亲生,父皇岂能偏心。”
“郢王友珪乃是嫡长子,当立皇储。”朱晃言道。
王氏冷笑道:“嫡长子?分明是父皇与营州妓女所生。”
“爱妃不可胡言,你听何人所讲?”朱温言道。
王氏言道:“开封城内人人皆知,朱友珪乃妓女詹鹊所生,身世卑贱,难道*养的野种也能当太子,岂不是让天下笑话。而友文风雅好学,精通诗书可担大任。”
朱温经不住王氏伶牙俐齿,言道:“朕亦有同感,爱妃放心,选个吉日朕拟旨立博王友文为太子。”王氏听罢此言一把搂住朱温,二人又是一阵亲热。
朱晃卧病在床,却常做梦思念张氏,于是又派人诏张氏入宫侍寝。虽然张氏百般献媚,朱温已无力房事。张氏见他病入膏肓,便轻声问道:“父皇立嗣之事可曾定下?”
朱温微弱答道:“朕已拟旨传位友文。”
张氏焦急问道:“那日父皇许诺传位于友珪,因何要变?”
朱晃言道:“友珪乃妓女所生,出身卑贱焉能继承皇位?”张氏闻听此言明白其中原委,未等天亮便早早回到郢王府。
朱友珪不知张氏因何提早回府,张氏言道:“昨夜侍寝父皇,其言郢王妓女所生出身卑微,不可继承皇位,皇位将传与博王友文,如之奈何?”
“老匹夫占我妻房,却不传皇位,欺人太甚!” 朱友珪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与妻子张氏商议道,与其传位博王朱友文,不如自己杀父自立。正是:
纳媳何念父子情,
一朝反目见血腥。
若非扒灰悖天理,
岂能骨肉动刀兵?
不知朱友珪如何夺位,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