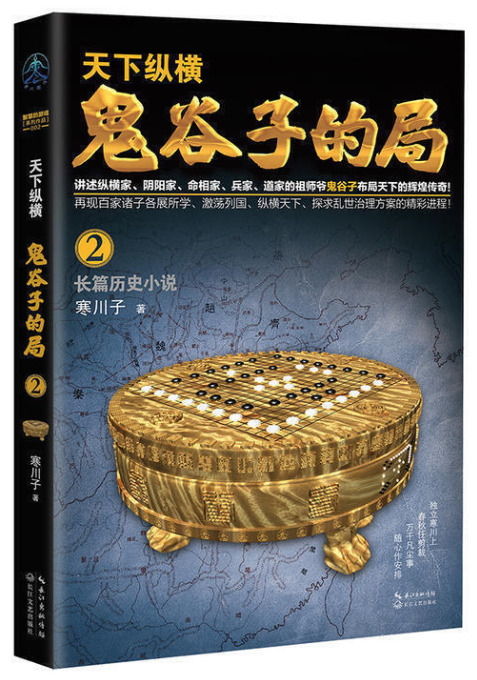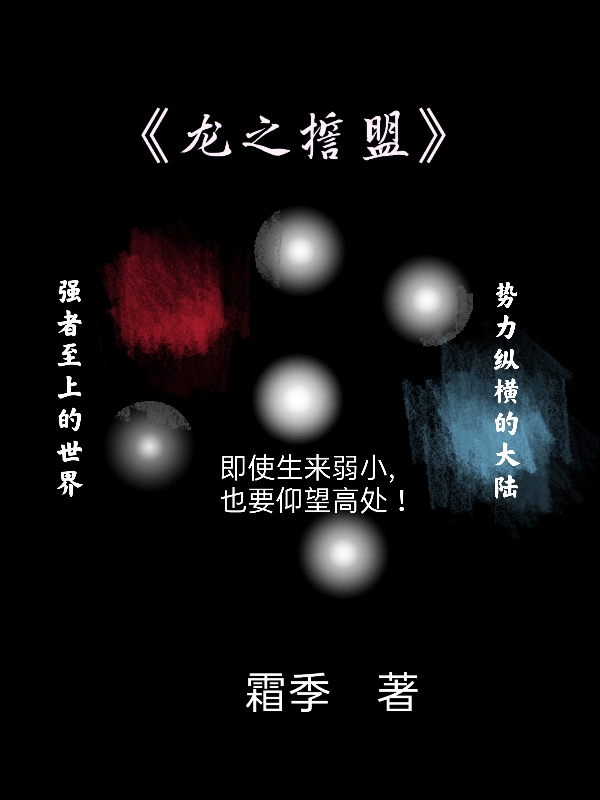朱怀镜觉得莫名其妙,说:“这并不怎么好笑呀!你怕是神经有问题了吧?你不要疯了才好哩!你要是疯了,孤身一人,没有照料,不要害死我?”
李明溪却真如疯了一般,说:“你还别说疯子哩。我想疯子都是些智力超常聪明绝顶的人。你说为什么总见狗发疯,而不是其他动物发疯?因为狗是动物中最聪明的。当狗的智力超过了极限,同人一样聪明时,就成了疯狗。又因为狗对人最了解,所以狗一疯了就咬人。”
朱怀镜不明白这人怎么一下子脑子里钻出这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便说:“我不同你讲疯话了。你只说中午有空出来一下吗?我有事同你讲。”
李明溪不太情愿出来,说什么事这么神秘,电话里说说不就得了?朱怀镜说你这是讲废话,好说我不说了?于是两人约好,中午十二点在市**对面东方大厦一楼咖啡屋见。
说好之后,朱怀镜再来细想这事。管他个鬼哩!反正话也说出去了,只好将计就计,假戏真做了。再说刘仲夏对画坛也一无所知,能哄就哄吧。这时突然停电了。市**也常停电,事先也不打招呼。他原先在下面工作,县**的电是不敢随便停的。偶尔停了一回,**办一个电话过去,电力公司的头儿会吓得忙做解释。也不知现在下面的情况怎么样了。从这里的迹象看,似乎市**的威信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本来就冷,停了电,室内阴沉沉的,更觉寒气森森。窗外的树木在寒风中摇曳。冬越来越深了。
朱怀镜中午下了班,径直去了东方大厦。李明溪不会那么准时的,他便找了个位子坐下来。小姐过来问他要点什么,他看了一下单子,发现咖啡要十块钱一杯了。两个月前他来过一次,是六块的价。却不好说什么,就要了一杯咖啡。这地方静得好,间或来坐坐,也蛮有情致的。等了半天,李明溪才偏了进来。他穿了件宽大的羽绒中褛,人便有些滑稽。
咖啡屋备有快餐,有些不伦不类,却也是这里的创举。生意倒还好些。他俩各要了一份快餐,再是一些饮料。一边吃着,朱怀镜说:“也没什么事,只是想请你替我作幅画。”
李明溪觉得奇怪,眼睛睁得老大望着朱怀镜,说:“你不也神经了?你平时不是总说我的画臭,送给你作揩屎纸都嫌有墨吗?今天出鬼了!”
朱怀镜不好意思起来,说:“你就别小心眼了。我那么说你,是见你太狂了,有意压压你的锋芒。你就当回事了?说实在的,你的画并不差,只是你没出名。你该知道毕加索的笑话。这位大师后期画风越来越怪诞,几乎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据他晚年私下透露,他自己都不明白怎么画出这么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只是他的名气太大了,不论怎么画,都得到世人的喝彩。人们越是欣赏他的怪,他就越画越怪。这其实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媚俗。也不知当时人们争相购画和收藏毕加索画作的时候,那些自命高明的美术评论家为他的作品大吹大擂的时候,毕加索老头儿躲在一边是怎么想的,说不定暗自发笑吧。”
李明溪听了只是笑,并没有知音之感。他反正一直在笑。过了一会儿,他说道:“你反正不懂画。”
朱怀镜说:“那么你是只给懂画的人作画了?这样的话,你们当画家的只有饿死一条路。不过真正要饿死的也只是你这些不成名的。那些大家,落笔千金!国画不是讲究留白吗?人家画面上留出一大块白宣纸,也是好几万块钱一平尺!”
李明溪这下收住了笑容,只把饭菜嚼得嘎吱响。朱怀镜说:“你别同我这样了。我这也是有苦衷哩!”他便把缘由说了,只是没有说到日本前首相收藏李明溪画作的事。
李明溪这就抬了眼睛,目光怪怪地望着朱怀镜,像望着一个陌生人。又是笑。好半天才说:“你要去拍马,拿我的画作当拍子?开始我还想给你画,现在你就是打死我也不画了。”
朱怀镜急了,说:“我拍他的马屁干什么?他只是处长,我也是副处长。我要拍马屁也会去拍秘书长,拍市长。只是我们一道共事,人家提出来,我怎么好驳人家的面子?”
李明溪是个糊涂人,没有去想刘仲夏怎么会知道这世上还有个李明溪。朱怀镜当然也没说起上午即兴说谎的事。他只是说他单位的人事关系,当然也说得遮掩。他说官场这正副之间,有时是天壤之别。就说市长,不仅带着秘书,还有警卫,出门就是警车开道。到了这个位置,说不定哪天往北京一调,就是国家领导人了。至少也是部长什么的。级别虽然不变,却是京官。但副市长们,弄不好一辈子就只是这个样儿了。正职要是一手遮天,你就没有希望出头。
刘仲夏就是这种人,他不让任何下属有接触上级领导的机会,好像怕谁同他争宠似的。碰上这么一位正职,你纵有满腹经纶,也只是沤在肚子里发酵。他没有权力提拔你,甚至也并不给你穿小鞋,但就是不在领导面前给你一个字的评价,哪怕坏的评价也没有。那么你就只有在他刘处长的正确领导下好好干了。干出的所有成绩,都是因为他领导有方。你还不能生气。你没有理由生气,别人并没有对你怎么样呀,你要是沉不住气,跑到上级领导那里去诉苦,就是自找麻烦了。领导反而会认为你这人品行有问题。人家刘仲夏同志可是从来没有说你半个不字,你倒跑来告人家状了。所以你只好忍耐和等待。
朱怀镜就这么要死不活地熬了三年了,市长换了两位,他同市长话都没有搭过一句。市长他倒是常看见,但这同老百姓天天在电视里看见没有什么两样。在电视里还可以看见市长的头部特写,连市长伸出来的鼻毛都看得清清楚楚。而他通常是在办公楼的走廊里碰上市长。现任市长姓向,一位瘦高的老头儿。向市长从走廊里走过,背后总是跟着三两个蹑手蹑脚的人。这些人都是办公厅的同事,都是熟人。可他们只要一跟在向市长背后,就一个个陌生着脸,眼睛一律望着向市长的后脑勺。似乎向市长的后脑勺上安着荧光屏,上面正演着令人兴奋的色情片。前面的人就忙让着路,就像在医院急救室的走道上遇上了手术车。朱怀镜碰上这种情形,总会情不自禁地叫声“向市长好”。向市长多半像是没听见,面无表情地只管往前走。有时也会笑容可掬地应声“好”。但即使这样每天碰上十次市长,市长也不会知道你是谁。可市长偶尔回应的笑容,却令朱怀镜印象深刻。他有时在外面同别人吃饭,人家把他当市长身边的人看,总会怀着好奇心问起向市长。这时他就会想起向市长的笑容,感慨说:“向市长很平易近人。”他心里清楚,这与其说是在摆向市长的好,倒不如说是在为自己护面子。如今这世道,不怕你吹牛说自己同领导关系如何的好,甚至不怕暴露你如何在领导面前拍马,就怕让人知道你没后台。朱怀镜缺的就是后台!
朱怀镜一时也不说话了,只机械地嚼着饭,不知什么味道。这本是一个清静的所在,但他俩的清静有些叫人发闷。吃完饭,两人又各要了一杯咖啡。
“明溪,”朱怀镜语气有些沉重,“你是槛外人,自然可以潇潇洒洒,无所顾忌。但官场况味,你是无法体会的。不亲临其境,谁也想象不出那种味道。一切都是说不出的微妙。比你创作的苦闷更甚百倍千倍。你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不管春夏与秋冬。我就太难做到了。”
朱怀镜说了许多,无限感慨。他从来没有这么同人推心置腹讲过自己的境遇。他知道现在这世道,你同人家诉苦,除了遭人看不起,连一点廉价的同情都捞不着。所以现在人们不管弄得怎么焦头烂额,却总是打肿了脸充胖子,牛皮喧天。有些人屁本事没有,居然就凭吹牛,转眼间大富大贵了。你今天还在笑话这人瞎吹,明天你就不敢笑话别人了。人家早已真的人模人样了。
朱怀镜说话的时候,李明溪一直埋着头。他脸上的笑容越来越怪异。等朱怀镜说完,长叹一声,他才似笑非笑地说:“如此说来你还真的很痛苦?我原来只以为你有些无聊哩!好吧,我画吧。你说,他有何兴趣?我没有激情,只好搞命题作文了。”
朱怀镜想了想,说:“那也一时说不上。不过人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只会说几句官话,他还是经济学博士哩。”
李明溪听了马上笑了起来,说:“经济博士?据我所知,如今官场上有些人的文凭来得可并不经济哩。”
“人家可是出过几本书的哩。”朱怀镜说,“他那几本书将是他在政界过关斩将的重要资本。”朱怀镜说是这么说,他怎么不知道李明溪说的是事实,花钱买硕士、博士文凭的领导干部太多了。
“有了。”李明溪突然眼睛亮了一下,随之掩嘴而笑。
朱怀镜原以为他得到灵感了,可是见他的样子像是恶作剧,就说:“画什么东西就随你,只要不像纪晓岚羞辱和珅,搞他什么‘竹苞松茂’之类的东西去骂人家就行了。他也是文化人,你的那些小聪明,人家懂!”
说好了,时间也就差不多,付了账走人。朱怀镜径直去了办公室。本想去刘仲夏那里说说索画的事,估计他这会儿可能还没有来上班,就先翻翻报纸。看到一则笑话,说是第比利斯一幢高层建筑停电停水一个多星期了,有人却贴出一张通知:请冬后幸存者于星期一上午在大楼前集合,拍照留念。朱怀镜立即想象着俄罗斯的冬天,寒冷而漫长。他不禁打了个寒战。俄罗斯人真是幽默,快要冻死了还有心思开玩笑。记得西方有个说法,说人在最无奈的时候就只有笑了。朱怀镜心想,暖气要是还不修好,这里只怕也要拍冬后幸存者纪念照了。只是没有人敢开这种玩笑罢了。
想给刘仲夏打个电话,又觉得不太好,就跑过去看了看。仍不见他来上班。已是三点半了,要来也该来了。只怕是开会去了,去开会也该打个招呼。正副职之间工作不通气,论公是不合组织原则,论私是不尊重人。朱怀镜便有些不快了。又一想,何必想这么多呢?自寻烦恼。也有可能人家有紧急事情出去了,来不及打招呼。
他一个下午没事,只在装模作样地看资料。冷又冷得要命,久坐一会儿就透心凉,只好起身到各间办公室走走。手下同志们是两人一间办公室。同事们见他去了,忙招呼朱处长好,手便下意识地抚弄摊开的文件,好像要告诉他,他们正在认真阅读资料。一见这样子,朱怀镜就知道他们是在海阔天空地聊天了,却故意装糊涂,说:“都在看吗?时间越来越紧了,要好好看一看资料。不光是看,还要琢磨一下观点。”同事们点头称是。他当然明白手下人最烦的就是成天傻坐着看资料,却仍是故作正经,强调吃透材料的重要性。他讲得好像很认真,手下人听得也好像很认真。真是有意思,官场上的很多事情,大家都知道很无聊,但都心照不宣,仍是认认真真的样子。似乎上下级之间就靠这种心照不宣,维护着一种太平气象。
好不容易挨到了下班,朱怀镜步态从容地回到家里。一进门,就嗬嗬地搓手。真冷得有些受不了啦。他估计这会儿刘仲夏即使开会去了也该回来了,就准备挂个电话过去。他刚拿起电话,又放下了。还是明天上班时没事似的告诉他吧,不然显得太巴结了。香妹在厨房里忙,说道:“你这么冷,不知道开电暖器?”朱怀镜开了电暖器,身上慢慢暖和些了。琪琪小孩子不怕冷,坐在一边看电视。电视里正演着卡通片。
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香妹的表弟四毛来了。四毛提了个尼龙编织袋,站在门口半天不晓得进来。朱怀镜说你快进屋呀!四毛擦着鞋问要脱鞋吗?朱怀镜说着不要脱哩,却又取了双拖鞋给他。
“快叫舅舅,琪琪。”朱怀镜说。
琪琪喊了舅舅,却头也没抬,望着电视不回眼。香妹听见了,摊着双手出来招呼:“四毛来了?快坐快坐。我在做饭,你姐夫陪你说话吧。”
“今天从乌县来的?”朱怀镜问。
“是。清早上的车。”四毛答道。
“姨夫姨姨身体好吗?”朱怀镜又问。
四毛回道:“我爸爸身体还行,做得事。妈妈身体不行,一年有半年在床上。”
“家里收入怎么样?”朱怀镜问。
“一年到头找不到几个钱。”四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