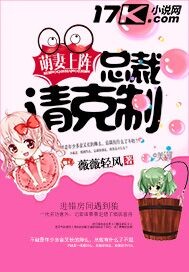卫奴儿冲李毓之淡淡一笑,就这一笑,这带有丝丝挑衅意味的一笑彻底激怒了李毓之,让她陷入盛怒的情绪之中。
没错,奴儿在赌。
李毓之出自名门,一生顺风顺水,一直都是高高在上的掌权者。她从来没有输过,所以她自信于自己智谋与自己的权力,可她并不知因为她从未输过,所以她把自负当成了自信。她相信她安插在小柳庵的碧兰,相信她不会背叛自己,相信自己的安排是天衣无缝。所以她一定会坚定地认为她拿到是真的木兰花簪,而木盒之中的,却是奴儿为了逃避罪责而假造的一模一样的赝品。
果然,李毓之几步上前,凑在陆挚身边瞧了瞧他手中的簪子。这样乍眼一看,这两支簪子当真是一模一样。
“倒真是奇了!怎会有两支一模一样的簪子。”李毓之叹道。
“是呢,怎么会是一模一样的呢?”奴儿也如此反问,她故作懵懂继续说道,“娘亲的簪子我一直珍藏,也不知为何会有一支一模一样的簪子落在了后院井底,偏还这样巧,正好是秋心落水的地方。”
李毓之与奴儿两人说话之间暗自交锋,也难辨谁真谁假。此时江氏上前,对着奴儿问道,“四小姐,这支簪子除了花纹样式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自是有。”奴儿抬头看了看陆挚,“只怕父亲不愿意听。”
陆挚一挥大手,“说。”
奴儿犹疑了一下,像是下了决心这才开口,“父亲当年将这支簪子赠予娘亲,娘亲爱若珍宝,自己用小刀在木兰花瓣后刻下了父亲的挚字和娘亲的柳字,刻字虽小,但依稀之中仍能辨析。”说罢对着陆挚深深地磕了一个头,“请父亲亲自验证!”
是么?
她竟把他们的名字刻在一起……柳儿,你是念着我的,对吗?陆挚连忙将手中的簪子反过来,他的大手在银簪上摩挲几下,是真真正正的刻字,而且看上去已有些年头,决不能可能造假。这是她刻的吗?她刻下,便说明她有情,那她又为何要背叛他?
他长叹一声,双手无力地垂下。他低头看看仍旧跪在地上的奴儿,心中有了一丝不忍,他起身亲自扶起奴儿,道了一句“委屈了”。奴儿心中一震,这一句委屈了她等了多久,多少年。娘死了,卫颐也死了,一句委屈就能带过这些仇恨吗?爹啊,作为你的女儿,不管你怎么对我,冷落我也好,折磨我也罢,我都可以不恨你,我都可以原谅你。
但人死不能复生。在你把冷剑刺进卫颐的身体里的时候,在你任由李毓之毒害母亲的时候,在母亲躺在病床上变成一具冰冷的尸身的时候,你就不是我父亲了,血缘之情,血缘之亲,早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彻底断了。
如果当初李毓之栽赃母亲红杏出墙之时,如果当初从母亲枕下搜出那块玉佩时,你能给她一个解释的机会,给她一个说话的机会,是不是一切都会不一样。可是你没有,你甚至都没有彻查,仅凭一块玉佩就判了她死罪,从此将她打入冷宫,恨她怨她。
陆月白见状,顿时按捺不住,她忿忿不平地开口,“父亲难道连另一支簪子都没看就认定卫奴儿是无辜的吗?”
“放肆!”陆挚怒斥,“越发没有规矩了!竟敢出言顶撞自己的父亲!”
李毓之见状暗道不妙,她立刻上前一巴掌狠狠地扇在陆月白脸上,“果真是放肆!母亲平日里是怎么教你的,都统统忘了吗?你也是,你才多大,儿时也不过是见过卫姨娘几面,就将这簪子给错认了。差一点竟冤枉了你自己的亲妹妹,你可知错?”
陆月白白皙的脸庞上瞬间出现一个巴掌印,她捂着脸,泪水止不住的落下。她虽没有陆银华精明,但却不傻,她知道此计已然失败。一切的事情都只能是她的一个失误,与栽赃绝无干系。而她也要撇清自己,于是她跪下哭着道,“父亲,是月白错了。月白年纪小,本也是想替无辜惨死的人找回公道,却不想弄巧成拙。只凭着印象便将簪子错认了,请父亲责罚!”
陆挚一向雷厉风行,李毓之生怕他动怒责罚陆月白这才抢先扇了她一个巴掌,现在见陆挚的心绪已被卫奴儿搅乱,心中恼怒又不得发作。只能在一旁求情,“还请将军念在月白年纪小不懂事的份儿上,饶了她这一次。而且琼光宴在即,若是传了出去,月白的名声又往哪里放啊!”
“是啊,将军。”江氏走上前轻轻拉了拉陆挚的衣袖,劝道,“琼光宴在即,女孩子家的名声最重要,将军大可饶恕她这一次。莫说她一个小孩子,方才就连妾身都看走了眼呢。”
“江姐姐,话虽是这样说不假。只不过,这簪子无论是从材质、样式,除去刻字都一模一样。若非有心而为,哪里会有这么巧的事情?而且跟谁的簪子不一样,偏偏跟卫姨娘的簪子一样。”说话之人是府里最为泼辣的妾室王氏,她出身青楼,形形色色的人什么没见过,性子泼辣又耿直。当初随是在青楼但却是个淸倌儿。她崇拜陆挚的英武之气,当初为了嫁给他更是当街拦马示爱,这才入得府中。
“我们这些后入府的,都未曾见过卫姨娘,更何况是要仿造她的簪子。为何会有一模一样的簪子出现在一具尸体旁,而涟漪苑的人又为何溺死在井中,这些将军都不想知道吗?”王氏反问。
奴儿心知,李毓之在府里根基深厚,又有强大的娘家作为后盾。此次之事并不能扳倒她,不过她也从未想过要凭此事来扳倒她。她不过是想要借此撕开李毓之伪善的面孔,让陆挚知道他的正室夫人是一位为了扳倒敌人不息栽赃别人的人,就算那人是个孩子,一个失去母亲的孩子,他陆挚的孩子。
其实奴儿心中不是没有抱过为母亲洗清冤屈的念想,不过之所以想要为母亲洗清冤屈,她是想要他的父亲明白真相之后带着悔恨而死。要他后悔,要他自责,明白自己曾经究竟做了多大的错事。
奴儿跪下说道,“父亲,奴儿已经证得清白之身,已然足矣。其余的,但凭父亲做主!只愿父亲日后,肯多信奴儿一点,记得奴儿也是您的女儿。便罢。”
陆挚看着这个女儿,他似乎很久很久没有这样仔细的瞧过她了。还记得当年这个女儿刚刚出生之时,他一手抱着柳儿,一手抱着女儿,还记得那时候他的柳儿笑着对他说“陆郎,这是我们的女儿,你日后可不能因为她是女儿便薄待了她,否则我可是会责怪你的”。她娇嗔的样子到现在他都还记得很清楚,柳儿,你在天上看着可怪我薄待了咱们女儿?
他微微闭眼,稳了稳心绪,理智告诉他,他对此事应该就此不追究。事实上,他也的确这样做了。
他的选择几乎是在奴儿意料之中的,她丝毫不感到意外,这就是权贵。任何事情,在利益面前都是不可深究的。陆挚明白,她也明白。
殿里的人三三两两的退下,奴儿走时,秋兰还跪在殿中的一个角落里。她无声地抽泣着,她只是一个丫鬟,哪怕找到了自己的妹妹,哪怕看着她死了,她也没有办法去改变什么,甚至连追究凶手都做不到。
奴儿走上前扶她,却被秋兰一把推开,她双眼通红,眼中充满悲伤和愤恨。
奴儿上前在她耳边低声说道,“秋兰,你难道不明白吗?秋心是怎么死的,为何而死,根本不重要。秋心的死,仅仅是有人想要借此给我按上罪名,让我万劫不复而已。这只是一场上位者之间的斗争,弱肉强食,你,看开些。”
“是谁?”秋兰喃喃问。
“是谁,就要你自己去深究了。”说罢,奴儿转身退了出去。白双在外面候了许久,一见奴儿出来立刻迎上来,大松一口气,“小姐你可算是出来了,奴婢的心可都要跳出来了。”
“这便心都要跳出来了。那再过些时日岂不是要吓死了。”奴儿淡淡地说。
白双一脸迷惑,“小姐可是有主意了?”
“琼光宴要到了,好戏,还在后头呢。”奴儿轻笑。
“若非小姐聪慧,一早叮嘱要牢牢看紧碧兰,否则也不能略施小计,就偷天换日。不然,眼下恐怕已经被安上了罪名。”
碧兰是李毓之安插进小柳庵来监视自己的,这一点,奴儿一早便知。所以她才要白双盯紧碧兰,她故意任由碧兰偷走那支簪子,又变卖了当初母亲从宫里带出的一幅珍贵字画,重金请外面的匠人打造了一支一模一样的簪子,再用假簪子把真簪子换了回来。如此,一出偷梁换柱就唱成了。
白双眨眨眼睛,“那碧兰应该如何处置?”
“碧兰办事不利,以李毓之的性格必然会惩处她一番。想来碧兰也会将小柳庵盯得更紧。而且经过此次事件,想必李毓之定然不会再轻举妄动。”奴儿顿了顿继续说道,“去打听一下碧兰可有什么把柄在李毓之手上,若是有咱们便要帮她一把,若是没有那就更好了。”
“小姐想要策反她?”
“不可以么?”奴儿笑眼盈盈地看着白双,“等着吧,琼光宴可会比今日精彩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