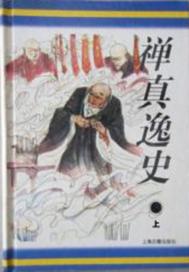她像丢了魂似的,呢喃着对不起,然后绕过男人沿着走廊继续往前走。
“哎哎,想走就走啊?”那男人伸出手拦住了她。
昏黄的灯光下,那男人流里流气的,勾起唇角露出一丝猥琐的笑容。
她没想过会遇到什么危险,只是目光没有焦点的看着他,半晌,缓缓开口。
“那你想干什么?”
“陪哥玩玩,你想要多少钱,哥给。”那男人满嘴胡话,伸手就要去抱她。
叶琳已经好多天没有精心的打理自己,身上穿着款式简单的棉布裙子,几天没有熨烫,看上去很廉价。
那男人以为她是缺钱,“五十万买你一夜,怎么样?”
金碧辉煌是会员制的,来这里的人不是富家子弟,就是企业大亨,总之没有贫穷之辈。
“滚开。”叶琳看也不看他一眼。
“脾气还挺大,我就喜欢你这样的,过来让哥好好疼疼你。”
说着,那男人伸出手将她一把拖进旁边的空屋子里,一把将她按在沙发上,不由分说就撕开了她的连衣裙。
“放开我!”直到这时,叶琳才从酒意中有些清醒过来。
她虽然瘦的像皮包骨似的,但她的力气也不算太小,使出浑身的力气去抵抗几乎压在她身上的男人。
那男人看她竟然还有几分力气,想来也是不愿意硬上,从兜里掏出些什么东西,直接塞进了她的嘴里,手放在她的喉咙处一动,那药就被她咽了下去。
叶琳开始剧烈的咳嗽,有些被呛到了。
男人又开始将手伸进她的裙子里,狞笑间,身后突然响起一个清冽的男声。
“住手!”
只见张敬文穿着一袭休闲装,皱眉看向那男人,随后一个拳头就挥了出去,狠狠的打在那男人的脸上。
男人吃痛向后倒了一下险些站不稳,他揉着发疼的嘴角,往地上吐了一口血。
“妈的……敢坏老子的好事儿,你谁啊你?!”
“给你点时间,你快滚。”张敬文冷着脸看着他。
平时柔和的脸上不再是那种柔和的线条,取而代之的是冷厉的带着恨意的色彩。
叶琳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张敬文,一时间有些呆住了。
可是不知怎的,头却越发的沉重起来,本来初秋的天气已经很冷了,她穿着薄薄的连衣裙,身上却感觉一阵阵火热。
那男人自知打不过张敬文,往地上又狠狠地呸了一下,夺门而出。
“快起来,你怎么样了?”张敬文赶紧上前去扶住有些迷糊的叶琳,眼里满是疼惜。
周身突然散发出一种难以忍受的热感,那些身上难以启齿的地方开始痒了起来,叶琳心里一惊,突然想到刚才喝进去的那东西,眉头一皱。
她推开张敬文的手,想自己一个人仓皇而逃,据说这种东西,发作以后找个没人的地方用凉水泡一泡挺过去就好了。
她有些心慌,时间不等人,再晚一会她就走不了了。
跌跌撞撞走到门旁边,却再也没有力气出去,一下跌坐在地上。
张敬文狐疑地看着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赶忙伸手过来扶住她。
这一扶,那双迷离的眼睛就死死盯住了张敬文秀气好看的脸庞,“师兄……”
叶琳的毒已经发作了,她控制不住自己,嘴里不断呢喃着,“太热了,你救救我。”
伴随着她嘴里不断发出的让男人难以忍受的叫声,张敬文才突然反应过来她发生了什么。
她一边说,一边将自己已经被人撕裂了的连衣裙脱下来。
张敬文睁大了眼睛,喉咙上下翻滚了几下,身体已经做出了诚实的反应。
他扭过头看向别处,赶忙伸出手按住她就要掀开裙子的手,将自己的黑色薄款风衣脱了下来披在她的肩头。
“叶琳!你清醒一点,我这就送你回……”
不行!这种情况下不能送她回家,张敬文蓦然停住了话。
若是发作的话,她自己很难挺过去,即便是挺过去了,也是难受的像是死过一次一样。
他英俊的脸上写满了愤恨,皱着眉,良久,那双温柔的小手已经急切地摸上了他的胸膛。
“师兄……救救我……”她柔声细语,脸上尽是媚态。
他不敢想,若是自己今天没有跟朋友一起来这聚会,没有在走廊路过的时候发现她,后果会有多么的可怕!
手已经放在了兜里的手机上,却还没有下定决心要不要拨通。
那娇媚的声音在他耳边一次次地响起,他有些克制不住,心一横,拿出电话拨了过去。
“喂。”那边是低沉没有感情的男声。
“顾彦深,叶琳现在在金碧辉煌,如果你不要她的话就直接放了她,这样对她,你还是男人吗?”
那边沉默了一下,沉声问道,“发生什么了?”
张敬文没回答,只是报了个房间号,接着说,“你若是再不来,她可能会有危险。“
那边没说话,直接挂断了电话。
不出十分钟,顾彦深带着周末匆匆闯进了房间,一进屋便看到这样一幕。
那小女人的裙子像块破布一样,外面披着一个男式的黑色风衣,脸上是连他都没见过的妖娆妩媚。
而给他打电话的张敬文,此时此刻正在抱着那小女人,表面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可作为同性,顾彦深看得出来,他在强忍着。
顾彦深这等身份,自是一眼就看穿了发生了什么。
他凌厉的眸子扫射了一眼屋子,最后停留在了那小女人绯红的脸上,蹲下,将她从张敬文的怀里抱过来。
“怎么回事?”
张敬文在一边喘着粗气,终于放松下来,面无表情看着顾彦深。
“她遇到小流氓,差点出事。”
那怀中的小女人还在无比娇柔地喊着,嘟着小嘴,伸出手就攀上了顾彦深的脖子。
那柔软的身子突然在他怀里扭动了起来,顾彦深一颤,身体微微有些发热。
“你可以走了。”顾彦深冷着脸,将叶琳身上的风衣拿下来扔给张敬文,自己的外套脱了下来披了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