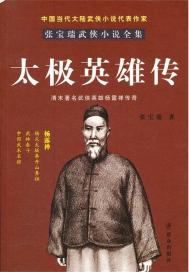南国的秋天,就像一个短腿的谎言。匆促之间,仿佛所有的钟声在同一时刻敲响。生命的呼吸在雷阵雨的噩梦里,又在方醒的凌乱中续接它的波涛。轻轻走向阳台,我的窗前正对着红灯初熄的舞厅和斜压过来的高楼,那充满欲望与冲动的姿影,挡住了我远眺的翅膀。阳台下有一棵老树,透黄的枝叶正像楚天的编钟声声敲击,斑驳的间隙有刺眼的晨光穿透我心。这光、这影、这声音,此时是那么迷离,斜倚倾听,似乎交汇成旋律和话语,覆盖了一切寂静。偶尔有一两片树叶被晨风刮落,飘向楼下那条古旧小巷的青石板上。它的尽头是一片贫舍,那里挤住着世代的广州人。当我听着嘻笑尘嚣之声绕梁于小巷,看着大清早就忙于生计的人流,蜗居在古旧与新潮的夹缝里酷似逃遁地守着内心的真实,总有一种随时升腾又随时坠落的伤感。冥冥中,生命的长廊似乎有一座城门。城外是一方锁锈的天堂。
任岁月流淌,在灵魂的阶梯上,我是一个出逃的囚徒,忘了姓名、家门,飘泊的每一个驿站。
一度喑哑着沉寂,恰似长鸣的钟,昭示总有一条路得走。有所舍弃自然要有所获取。想起福克纳的一句话:“一个人应该比舍弃做得更多,应该有更加积极的行动,而不能仅仅躲开。”眼前这棵生命树上每一根叶脉,在晨光中多像从天堂里剪下的小小火焰,它照亮我的身影,以一截又一截刻骨铭心的记忆塑造着自己。在语言的根茎上生长欲望的稻草时,晨风摇动的秋叶成了生命创力的标识。尽管伤痛、污泥包围着她,但她伸展的枝叶,毫不犹豫地指向被锁住的方向。于是,我开始以当下的方式——奔忙、忧虑、焦灼、梦幻、潇洒、慌乱、热闹、寡合——传达逝去的日日夜夜,让一个本真的自我、寻求幻美的自我,修复得更理智、更合乎人性也更具恩情寓意一些。我在南方最热闹的角落里就这样孤独地写诗。有时寂寞得像一只躲在屋檐下的驼鸟。诗歌成了我心灵最宽的天空。
我无法选择个人的命运,却别无选择地追赴缪斯一次又一次的约会。我浸入诗歌的是整个的人——血肉之躯,呼吸的、感觉的、思想的律动。我渴念保持清凌凌的心头词源,执掌心灯熨平惆怅的灰烬。我希冀在心驰寥寥的一角维持都市与乡村的平衡。力求拄着世俗的拐杖探寻天堂的矿脉,祈求亲近心灵就像亲近星空。
我知道,在通往灵魂的山坳上,我永远都是一个逃遁的囚犯,永远都在心灯长眠处,倾听“窗含西岭千秋雪”,倾听精神磨难和生命过程的斑驳印痕。
十年化血为墨,我终于砌搭了这一座心的“叶子城”。我深知,苍天在上,任何精神的建筑都不过是些粗糙的毛坯,何况这些但求精致难免粗流的诗行。艺术品的完美永远只是一种仰望的姿势。
一九九八年八月二十五日晨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