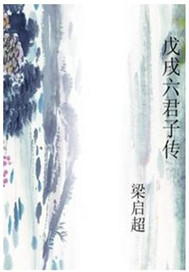温良摆摆手:“不用,娘没胃口。”
墨文担忧道:“娘,再没胃口多少也吃点,您这一天了都未进食,身子哪里受得住。”
“对啊娘,儿媳妇和墨文特意煮吗您最爱的莲子粥,现在还是热的,娘你多多少少吃点。”瓶儿柔声劝解道。
“嘿嘿嘿,嘿嘿嘿,天仙儿,天仙儿别跑。”屏风后,也可以说是笼子里,墨渊零散着一头黑发,目光空洞盯着地上,傻笑。
温良看着心里一阵刺痛,方才有想些喝一点粥的心情瞬间没了。她一手扶住额头,道:“你看看你弟弟现在这个样子,娘我哪里吃的下饭啊。”
“说起这,娘,弟弟这到底是怎么了,昨天晚上吃晚膳时还是好好的,怎么突然便是疯了?”
温良摇摇头,整个人颓废异常,本便是半头银发,如今一夜之间倒真是像老了十岁,磨平了眉眼间几分锋利。
“你先走吧文儿,娘想和瓶儿说几句话。”
墨文有些犹豫,不知为何好端端温良要撇开自己。
瓶儿握紧了墨文略有些冰凉手指,笑着摇头:“娘定是要跟我说些女子间琐事,相公你不方便听得,总归是一些鸡毛蒜皮小事,相公你便先回房休息一会儿,若是不想休息,睡不着便去铺子里看看,最近上吗好多新货。”
“也罢,我便离开了。”
“相公做事小心一点。”瓶儿目送墨文身影消失至极什么都看不到,这才依依不舍收回目光。
温良见此,道:“你和从前倒真是变化大。从前我家文二无论待你多好你都看不在眼里,现在知道文二待你好了,后悔了。”
“娘你可真会说笑。”瓶儿不置可否:“的确,从前是我眼瞎,现在弥补还不算晚。”
温良道:“弥补?你如何弥补,你已经死了,画嫣辞。”
瓶儿愣了愣,倒是许久未听得别人唤自己这个名字,时间久她差点有些忘记自己究竟是谁了。
“娘,我也没打算瞒你。”
温良痛心道:“墨渊这事是你做的吧?”
画嫣辞点头,算是承认了。
“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可是文儿二弟,你伤害他也算是在迫害文儿啊。”转头便是能看到现在疯疯癫癫得墨渊,她只要一想到昨夜墨渊还抱着她的胳膊撒娇说是要再娶两个小妾,今儿便是成了疯子,让她心里如何平静,如何面对摸墨渊。
画嫣辞眸子很静,眼底似乎还有两分嘲弄:“娘,我的好娘啊,墨渊对阿文如何你会不知?阿文不知如何面对墨渊那个畜生,娘你可曾想过墨渊做了这么多又如何面不改色,没有丝毫愧疚之心面对阿文。说句实话,我能到现在不杀了墨渊已是我的极限。”
杀了他,杀了他。这三个字仿佛一把利剑,击的温良仅有意识溃不成军。她手指颤颤巍巍指着画嫣辞,斥责道:“画嫣辞你别给我太过分,你信不信我将你是画嫣辞的身份公众与众,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的身份,皆时我看文儿还会和你在一块儿吗。”
画嫣辞又是一笑,道:“娘亲真打算这样做,可我不介意鱼死网破。我不杀你那是念在生前你待阿文不薄,对我也算说的过去,我念你的好,您老也别在挑战我的底线,若不然弄死你和墨渊真的比杀只蝼蚁还要容易饿多。所以,我劝娘你还是不要有太大动静哟。”
“你……你……”
“好了,话已至此,娘也是聪明人,怎么做儿媳这便不用多说了。”
画嫣辞盈俯身:“这几天儿媳约摸要有事要忙了,府里还请娘多多费心,别把所有事情都交给阿文来做,我怕他累到了。”
临走之际,她也看了眼笼子里的墨渊,嘲讽十足:“想来这样活着,对他来说才是种折磨,不比一刀杀了他让我痛快。”
方出了门墨文便推着轮椅过来了,他急急忙忙推了两下:“瓶儿。”
瓶儿笑笑,揽在墨文伸手推动轮椅:“怎么不回去?”
“不放心你。”
“担忧娘亲欺负我?”瓶儿半开玩笑道:“我可是对他儿子照顾的无微不至,娘亲也是个通礼的,自然不会为难我。”
墨文一手握住瓶儿手背拍了拍,笑道:“就不晓得谦虚点。”
只瓶儿噘起小嘴,道:“本来就是嘛。”
墨文又是一声轻笑,未说话。
过了会儿,瓶儿低了眉眼看墨文,咬着唇道:“阿文,我们俩要个孩子行吗?”
墨文一愣,随后苦笑道:“我也想,可是我这身体……”
“身体不用担心,阿文若是想,自有办法完成。”
墨文低低头看了眼自己盖在厚厚软毯之上的双腿,能重新站起来吗,他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这么长时间过去他也是习惯了不能走路是什么滋味。
“不用了瓶儿,现在你和我好好的,日子过得舒心,其他的我什么也不奢求了。”
墨文浅笑,虽是低着头却是一脸满足。
从前便是奢望太多,得到一点老是想着让其他都是他的,以至于后来什么都没了。现在他懂了,这个世上再没有什么比看到自己珍爱之人平平安安,在世上活着更好的事了。
“阿文……”瓶儿停了两步,也不推了,只望着回墨文,一句话说不出。
“怎么了瓶儿?”
画嫣辞没有说话,偷偷抹去泪水,仰头笑道:“没,没什么,就是感觉阿文待我太好了,我怕这一切都是个梦,梦醒了什么都没有了,阿文也不要我了,想想我都害怕。”
墨文笑道:“傻姑娘,胡说什么,你是我的妻子我怎么会不要你。以后咱俩过自己的日子,其他的都别问了。”
画嫣辞泪光微闪,点了点头。
晚上时刻,墨家灯火微暗,画嫣辞睁开眼,侧身看了眼墨文,确认墨文已经睡着后,起身随意穿好衣服出了门。
北城夜里起了风,叫个人都没有更是显得极为萧索。画嫣辞来到一处荒僻树林间,那里已有一红衣女子在侯着。
画嫣辞咬了咬牙过去,道:“何时给我解药?”
白倾瓷双手负后浅浅笑道:“要我给你解药,我交代你做的事情做好了没有?”
画嫣辞摇摇头,眼里闪过一丝挣扎:“清山殿的道仙都来了,我不能搞出太大动静,若不然定要被抓走不可。”
“那是你的事,与我没有任何关系。”
“你……这般无情。”画嫣辞一愣,倒是没有想到白倾瓷拒绝的如此利落。
“我无情,这话不觉得可笑吗?”白倾瓷仿佛听到了什么大笑话,掩唇笑了,微微上扬的眉眼都是笑意:“你我不过只是一场交易,各取所需而已,其他的,我给你你想要的,你帮我办事,物竞天择。现在你办不成事,我又凭什么给你解药?”
“可我已经尽力,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能做到。”画嫣辞去软了语气,略带几分恳求道:“三天。”
白倾瓷没有说话,画嫣辞连忙改口:“明天,明天,求求你了明天,现在先给我一点行不行,我的肉体已经开始腐烂了,撑后不了多久。”
“人啊,可怕。”白倾瓷犹豫了下,从怀里掏出一个白瓷瓶子:“一枚救命药,一枚毒药,如何用,你自己好生掂量。”
待白倾瓷身影消失在片树林里,画嫣辞失了所有力气瘫坐在地上,不停吸着凉气。
她已经死了,半年前与墨渊私奔,这人骗她让自己喝下毒药后,他却反咬她一口,说是自己勾引她,这一切都是她做的,不遵守妇道,红杏出墙。她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时候北城的人都是如何说她的。不得好死,浸猪笼,以及鞭尸,光是唾沫星子早已可以将她淹死。
她没想到这种时候相信她,替她辩解,为自己烧纸的人竟会是一直被自己嫌弃的墨文也便是他丈夫。他一个人站在北城所有责备中坚信自己,无论如何,依旧是那句“我信她。”
信她,信她,为何信她。
画嫣辞不明白。
再后来墨渊接着墨文调查她死因,偷偷在回来路上马车动了手脚,墨文跌落草丛,双腿残废。
她在一旁无力呐喊,拼命阻止,得来的只有无可奈何,眼睁睁看着墨文被墨渊所害,自己被冤枉,痛不欲生。
因为怨气太重无法脱胎,她便冷眼将这些变故全都看在眼里,心里除了悔恨便是滔天不甘心。某天夜里她如常来到墨府,却被一团黑气带走,认识了白倾词,这个阴鬼一族人女子,在她帮助下,自己重新有了一副身子,因是稻草做的时常腐烂,她不得不过段时间便吸取人的阳气来维持容貌。
当然天下没有什么好事,白倾瓷肯帮助自己,自己也是需要付出代价。她需要折磨一个人,名叫长安,说的时候北城是未有这么个人存在,便说是三天后。
画嫣辞胡乱摸了两把泪水,踉跄着回去了。
因有了阴鬼一族人帮助,她即便出现在这种道仙面前也是不会轻易被人发现。
长安躺在床上睡得香甜,睡梦里也不知做了什么美梦,嘴角还带了一抹笑意,轻轻浅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