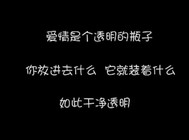第七章 风雨情更浓
由于小警官的帮助和他在大街上的支持,也是由于珍珍的容颜出众和非凡的打扮,她的叫卖生意明显好于公公和枣花的收入。晚上婆婆接过珍珍的钱,她一边数着,一边考虑,除去本钱,她挣得纯利可不少啊!心里很满意;但心里有时也不由得闪过一丝阴影:
“没了儿子,这样的媳妇恐怕难留住人家啊!女人长得艳了,难说哪天会不会招来灾祸。可她还是不断的安慰自己:
“什么时候了,儿子没了,过一天算一天吧,随她去吧。反正各人有各人的路,自己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吧。我自己可别再那么封建了……”
陈氏往挎包里装钱,心中不由得一阵阵酸甜苦辣。
公公也不傻,他看着珍珍的货在街上转了几圈就没了,也看到她招揽生意的娇媚,心中不由得也对她产生了非意和偏见,也为她不住的叹气;还会用另外的“眼睛”不住的窥窃这个儿媳妇的一言一行。
的确,人的七情六欲,随时都在绽放,何况珍珍又这么年轻呢?
年轻美丽的珍珍,当然会做她那些年轻的美梦:她时常回忆起与岳阳在一起生活的美好的片段,或回忆与岳阳在床上的欢乐……想得多了,想得美了,她不想让美梦醒来;但好景不长,梦就是梦,她总会醒。面对现实,珍珍会哭泣一阵,或是偷偷地抽泣几声,白天还得把那偷哭湿透了的枕头偷偷地放在僻静处晾干。
珍珍自从给那个小警官伍士元送货,特别是第一次伍士元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握了她的手,这阴阳相吸的纹波就在珍珍的意识中不断地荡起了涟漪。伍士元的身影,他的热心肠的帮助,他每天在大街上远远瞅着她,好像是在维护和“保卫”她,他的所作所为,她和他每天下午的会面,都变成了一张张无形的网,网有那么多纹丝,网丝又是那样的柔软和黏糊,横七竖八的紊乱的网丝缠住了她;她意识到自己已是网中被粘住了的可怜虫儿,无法脱身了。她等待着,默默的等待着,不知哪天,也不知什么时候,那个大网中,将会突然出现一只大蜘蛛把她慢慢地吃掉。
一天夜里,珍珍奇怪地梦见了伍士元。
那是一个大雾弥漫的天气,她挎着货篮没边没际地在大街上奔走。引河镇街上一个有名的恶赖叫“野狸子”的家伙,他像个幽灵一样,突然出现在珍珍的前边,双手张开拦住她,耍起了无赖,死不要脸地缠住了珍珍,要抱她,又去拽她的衣服。她拼命挣扎,拼命和那个无赖厮打。
突然,伍士元像一个天神从空而降,他对着那个流氓“啪啪”就是两个耳光,接着又是猛力地一脚,“野狸子”立时倒在地上哀嚎。珍珍被救了,她看着他笑。伍士元没说话,只是用手把珍珍的衣服理了理,微笑着离去了。
淡淡的太阳从雾中隐来隐去,始终不想放出亮光。雾还在弥漫着,珍珍仍在大街上荡游着,她今天的运气不佳,炒货无人购买,烟也没售出一包。她没精打彩地来到警局门口,警局的门敞开着。突然从局子里走出很多警察,把篮子里的瓜子、花生果一抢而空,几十包的杂牌烟也被一人一包地拆着抽了,刹时烟雾和雾气交织在一起。她害怕了,这些警察怎么会这样?她怕他们不付钱。一会儿一个小警官到每个人身上掏了钱,一分不少的交给了珍珍,珍珍又转忧为喜。她想该给伍士元送货了,他却站在了小值班房门前等着她,他说他已叫手下把该要的货给拿走了。珍珍一时迷茫,一时高兴,她要进屋说声“谢谢!”伍士元说不用。她不知怎么的,自己却不知不觉的坐到了他的怀里。他揽着她,她看着他。珍珍又不知怎么了,一下倒在了伍士元的身上,伍士元一咕噜翻身压住了她,她好舒服啊,但她忽然觉得自己喘不开气,她的梦醒了,是一床被子压在她的身上。她抱着被子,甜蜜的思念着:每一天的时间呀,上午要赶快过去,下午最美的时刻——那个小值班室换班的时间要赶快到来。
这大概是麦收过后的时间了,进城赶集的老百姓的斗篷上沾着不少麦芒子,还有的人把打下的新麦背到城里的市场上去卖。天气是越来越热了,一早晨起来,人们喘气就不痛快。早饭后,珍珍就换上了夏天穿的最薄的连衣裙,那清雅淡蓝的色调,使她更加绚烂多彩。这件连衣裙是洪岳阳前几年在苏州粮食交易大会过后,到有名的女士衣行里,费了好大的功夫给挑拣的。岳阳回来的那个晚上,她穿着丈夫刚买的这件裙子高兴地跳起来,翩翩起舞,然后抱着岳阳亲了好几次。这会,她看见自己的这身打扮,又构起了对亲人的无限思念,她饱含着酸楚的泪水,真想挎着货篮到道北去大哭一场,可今天挎的货太多了些,她慢慢地安慰自己,打消了伤心的杂念,她逐渐地养成了把痛苦暗暗埋在心底的习惯。
珍珍忧心忡忡地又来到了南北大街最繁华的地段,在一棵大树的阴凉下,放下了盛满香烟和炒货的货篮子。不一会儿,就围上了不少喜艳的男人争抢挑拣篮中的货物。他们嘴里嗑着瓜子,手里剥着花生,有的叼着烟卷,那贼溜溜地双眼就不停地瞅着珍珍那鼓溜溜的上怀,有的还趁珍珍低头给顾客拿货的当口,使劲歪头瞅着那领口下似露似藏的胸部,有的还有意无意地去碰她那丰满的屁股。珍珍一边数着卖到手的钱币,一边心里暗暗地骂着:使劲地看你的姑奶奶吧,早晚让雀儿啄去你们的双眼珠子;你们的娘和女儿,也让千万人去瞅、去看,也让你们自己去靠去摸……珍珍气急了,有时还骂出声,可那些恬不知耻的衣冠楚楚的油头滑贵,竟把钱攥在手里,故意挑逗珍珍去接,然后再趁机去碰碰珍珍的手,或故意把她的手捏一下。珍珍气愤地一把拽过钱,呸出一口唾沫,没好气地闪到一边又骂:这些钱真臭真脏。
珍珍顺着南北大街,又拐弯走向东西大街,她来到大戏院的门前,剧院里已好长时间没开演了,门前冷潇潇的。天更闷热了,似乎像个大蒸笼,罩在人们的头上,“轰隆隆……”似乎是炮响,又像是雷声。珍珍向天空望了望,西南天边处黑乎乎的,乌云正向太阳逼近。又是一连几声沉甸甸的闷雷,西南方真地起雨了。珍珍赶忙走到几家店铺,那些店铺的老板和伙计可都是熟悉的面孔,她含着微笑把香烟和瓜子、熟花生又硬派给他们
那些店老板和伙计也似乎板着面孔半真半假地说:
“硬派是吧,我们可没钱给你。”
珍珍说:
“没钱啊,好说,拿去白吃。”
可是,那些老板和伙计还是一五一十的把钱给了珍珍。
珍珍再次微笑着感谢他们。
天色暗了下来,货篮子轻快多了,炒货和香烟快要卖得差不多了。珍珍想到剩下的香烟和炒货是留给伍士元他们的,可离换班的时间还差许多。
雷声越来越紧,天色越来越暗,她必须提前给伍士元送货,他不在,就放在别人那儿,反正她常进出警局,那儿的人她差不多都认识了,她也不怕警察欠她的账了。
珍珍一阵急促的行走,已来到警局大门,她向站岗的打了个招呼,就大摇大摆的进去了。
珍珍还没到转弯处,突然一阵狂风袭来,把她刮了一个趔趄。这时天上的乌云像野马,直向东北方奔跑;忽然,头顶上一连几声炸雷,好似天崩地裂。珍珍似乎有些紧张,又有些害怕。她巴不得一步走到伍士元的小值班室,即使雨来了,她也能避避风雨。
天更暗了,似乎夜晚就要提前降临。又是一个特大的风头,直刮得垃圾和碎草碎纸屑没头没脑的打在珍珍身上、脸上。她的眼似睁似合地只顾往前走,当她快要一步迈进值班室时,大雨瓢泼似地从天上倒下来。
伍士元听到是珍珍的声音,他放开门高兴地欢迎她。
珍珍像个落汤鸡,不知是害怕还是高兴,她没头没脑的一下闯了进去,恰巧闯到伍士元的怀里。
一个紫条闪,紧接着就是一个炸雷,差点把珍珍和伍士元两人震晕。小屋顶被雷震得哗哗落土,伍士元把珍珍抱得很紧,生怕被雷公雷母抢了去。他拽下晾衣绳上的毛巾,轻轻地给珍珍擦着脸上和身上的雨水。他欣赏着她那被雨水湿透的身上的线条,也为珍珍今天的打扮而陶醉了。珍珍似梦非梦的柔软地趴在伍士元的怀里,任他欣赏。
真真问他:
“您怎么提前来了?我若是找不到你,今天可悲大雨淋惨了!”
“我看天不好,就提前来到了,这也可能是要和你提前相遇的缘分吧!?”伍士元自豪的说。
珍珍也面红耳赤的不知说什么是好:
“难得遇上你,老天安排的。”
伍士元亟不可待的把珍珍抱上他的小床,一下子倒在她的身上。
他醉了,他晕了。珍珍不知是害怕,还是幸福?她懵懂地睁开眼,也仔细地瞧着伍士元魁梧的身躯,宽阔的胸怀,她意识到她那夜的梦今天真的变成了现实。
雷声更紧,雨声更急。小窗户外,只能听到哗哗的雨声,呼呼的风声,风伴着雨,雨伴着风,闪伴着雷,雷震撼着大地。
伍士元趟在这个美得像朵玫瑰花似的珍珍身旁,珍奇地抚摸着她,亲他,吻她。珍珍在伍士元的身边,像个乖乖的小绵羊,哼哼地让伍士元欣赏个够。这一对男女,实在难以忍受这暴风骤雨的激情。那熊熊燃烧的烈火,把他俩烧得醉生梦死,魂飞梦绕……
雷电交加,似乎在给她俩掩饰着这人间偷情的爱的狂浪,爱的纵欲;风雨相伴,呼啸拍打,也似乎在为这人间的爱的绽放作优美旋律的伴奏……
时间这东西,你想叫它快,它偏过得慢;你想叫它慢,它却偷偷地就溜走了。小值班室的挂钟无情地敲响了十七下,小值班室安排换班的时间已到,别人马上就来换班了,伍士元要下班了。这会儿时间真宝贵,你为什么不停留一下呢,你就不同情这对情人吗?他们俩似捆在一起,似胶黏在一起,怎么也不想分开。伍士元又狠狠地亲了珍珍几口,珍珍也狠狠地抱了抱伍士元。两人恋恋不舍地分开了。他和她甜蜜地微笑着,相互调整着自己的神态。
门外的风小了,雨也小了,狂风暴雨过去了。珍珍整理自己的货篮,把该留给伍士元的几包香烟和瓜子拿到他的办公桌上,双眼再次妩媚地瞅了瞅他。伍士元像往常一样,点清了钱交给珍珍,然后又使劲地握了握她的手。
珍珍自己放开门,啊,好清新的空气,她深深地吸了几口,又不由地打了一个寒颤,便轻飘飘地离开了小值班室。到了拐弯处,她又不由自主地转脸望了望伍士元最后一眼,就冒着丝丝的小雨走出警局。伍士元望着雨中的珍珍,心中不由的一阵怜悯,一阵内疚,他真想永远留住今天下午这风雨中的美好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