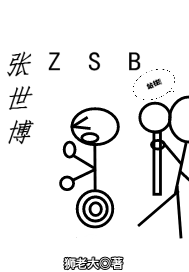五两银子是庄户人家一年所用之资,一个老太太哪里有这么多银子,但五两换五十两,老太太哪能错过这么美的事儿,东拼西凑弄了五两银子,又把自己老伴儿以前穿过的衣服拿了两套给萧容湛换上。
马是买不起了,最便宜也得四五十两,不过搭车坐就便宜的多了,一贯钱就能走好远。老太太把他引上官道,正巧得有辆骡子拉的两轮板车停在路旁,一老一小正往上搭草料。老太太讨巧,帮着谈了谈,两贯钱拉到同州。同州再往西南方向四百里,就能进入越西境内了。
车上的干草料有点扎得慌,老太太支了招,把衣服垫在屁股下面坐着。车子很颠,还有一股新鲜的骡粪味儿。
日头毒,不一会儿车上三个男人就晒得一身臭汗,萧容湛索性躺下了,虱子多了不怕咬,反正已经很倒霉了,还讲究什么?啃了赶车老汉给的半个硬面饽饽,噎得嗓子疼。
从前太不食人间烟火了,有这样的经历也未尝不是好事,至少可以知道,真正的老百姓是如何度日的。想到这里,容湛心里也就畅快多了,把被迷晕和抢劫的事儿抛到脑后。要是元熙看到自己这副样子还不知道会是什么反应呢。或许会开心一点儿吧?因为她平时最喜欢捉弄自己了。
出来已经三天了,照这个速度,十天肯定回不来。还不知道京城里发生了什么,容润能不能应付。想起自己这个六弟,容湛也有点心疼,要不是他仗义,怎么会扛这样的事儿?还不知父皇会罚他跪到什么时候去。年少时自己被罚跪,六弟还偷偷给自己送点心,那时容润才八岁啊。
“要睡觉,把杂草盖在身上就不冷了。”老汉儿说着,用干草把容湛和他那个儿子埋的严严实实,只露了个脑袋:“夜里风寒,睡觉别翻身,当心冻着!”
迷迷糊糊的睡过去,再一睁眼,已经是次日正午。
路边有个茶棚,又老两口用大铜壶烧了清冽的甘草茶。老汉停下车:“李二哥,来六个炊饼,三碗茶。”
李二哥应了一声:“哟,铁根,这是谁啊?”
“顺路拉的客人。”
容湛跳下车,抻抻筋骨,这光板睡了一宿,身上僵的不行。茶棚的炊饼蒸的挺软,容湛连吃了两个,噎得不行,忙喝茶往下顺,这茶也甜,挺解渴的。
老汉和他儿子笑的不行,还怕他不够吃,问他要不要再多吃一个。
这茶棚以南就是同州地界儿了,也就是说,该是告辞的时候了。萧容湛从包裹里拿了一块银子,约莫有二两。老汉儿推脱不收:“说好是两贯钱,怎么给这么多?”
容湛不由他不收,塞进了他儿子的口袋。转身往西南方向去了。
越往西南走,东西就越贵,一个炊饼从一文钱涨到了十文钱。雇车要五贯钱,只负责跨过同州,再往西南走还得加钱。银子再少也得坐车,毕竟比两条腿走得快。就这样,还没到越西边境,他就被扔在路边了。
包裹里空空如也,连吃饭的钱都没了,加上这个地方穷,没人愿意省出粮食帮助别人,索性把老太太给的另一件衣服换了一碗苞谷面汤喝了。
这下没了饭辙,他只能靠两条腿,幸亏只有几十里路,走走也就到了。容湛低头瞧瞧,没把靴子也给老太太换银子真是明智,要不是这双鞋结实,说不定会脚板磨穿,那就真成了踏破铁鞋无觅处了。
走走停停,饿了也没有办法,只能一条路走到黑,到了安康镇的时候,天刚刚擦黑,乌云滚滚好像是要下雨。
卫家的名号很响,在街上随便一问就能问到。
“诶诶诶,你就别往里进了,要吃的坐在门口等。”
容湛还没跨进店门,就被六子推了出来,容湛抬头望望,上面的牌子写着李记两个字。问路时,那人说的就是李记。
“这不是卫家的店吗?我找卫家小姐。”
六子瞪大了眼睛,伸手探探他的额头,倒还真是有点发烧:“我说,您这是烧的,你个要饭的找我们东家?干嘛?谈生意啊?”
刘天宝从店里出来:“六子,你干嘛呢?”
六子回过头:“宝哥,这来了个要饭的,要找咱家小姐,你说好笑不好笑?”
刘天宝随意一瞥,从佩囊里掏出一串铜钱想把他打发了。但就这一瞥,他一怔,不对,他回过头,又自己看了看,差点咬了舌头:“端……公子?”
“六子,快把公子扶进来,”刘天宝说着就去扶容湛,嘴里还欢喜的嚷嚷:“东家,你看谁来了?!”
令儿闻声出来,也是吓得不轻,眼前这个布衣短褐灰头土脸的人,不是萧容湛又是谁?!她揉揉眼睛,确信自己没有认错。
“公子,这是怎么了?快把公子请进去。”令儿说着倒了一碗热茶:“公子,我去给你烧热水沐浴。”
“令儿……元熙呢?”容湛四周望了望,没看到元熙的身影。
“她跟胡掌柜看货去了,估计快回来了,”令儿招手叫刘天宝:“把你的新衣裳给公子拿一套穿。”
刘天宝点点头,就要进门拿衣裳。一转头,看见元熙和胡掌柜已经站在门口了。
胡掌柜有点纳闷:“唉,怎么把要饭的带进来了?”
“谁让他进来的?”元熙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令儿嘘了一声,示意众人都离开,刘天宝把胡掌柜拖走了。
“元熙,你听我解释。”
“谁让你进来的,出去。”元熙头也不回的往里走,萧容湛忙上前拦住:“求你了,听我解释,我就说一句。”
“半句也不听。”元熙扯住他的衣裳把他往店外推:“你从哪儿来回哪去,我又不认识你,谁让你进来的!”
“元熙,我不是故意毁约,是我母后以死相逼,我也是无奈,我……哎!”
一句话没说完,他人已经被元熙推出店外,呯的一声,元熙将门关住,把门栓牢了,任他怎么敲也敲不开。元熙不想听他敲,到后院去了。
雨点儿冰凉凉的落在脸上,令儿搓搓手臂,天怎么突然就冷了?上午还是艳阳高照,下午就阴风阵阵的,想必今晚的雨小不了。
晚饭早就吃完了,六子把自己裹进被窝儿看他十文钱买来的话本子,胡掌柜回了自己家。只有刘天宝和令儿两个在院子里来回踱步,元熙的脾气他们拧不过,又怕真的给萧容湛冻病了。想偷偷出给他送点吃的,可元熙就这么死死盯着,他们哪儿也去不了。
令儿急的跳脚,廊下雨滴跟不要钱一样倾盆而下,打在手上还挺疼。
“小姐,你这是干嘛啊?下这么大的雨,殿下要是给淋出毛病,你怎么担待?”
“担待什么?是他自己想淋雨。”元熙望着天边的浓云,心里也有点后悔,但这嘴硬的毛病一时间又改不了。
刘天宝找了把油伞:“这样,我去赶他走。”
“天宝你!”令儿忙上前拦住他。
刘天宝低声道:“我去给殿下安排个住的地方啊。”
“谁也不许走!”元熙赌气道。
“小姐,好歹您让殿下进来,听他解释一句啊!”令儿拉住元熙的衣袖,温声道:“我知道,他在外面受苦,你心疼着呢,你也不看看时候。人家千里迢迢找到这儿来,又没带侍卫,弄得跟乞丐似的,狼狈成这样,这一路肯定吃了不少苦。说明殿下真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啊,你听他说说也好啊。”
“是啊,小姐,在京城的时候,殿下对你就上心。如今为了见你又吃了这么多哭,我们外人看了都感动,你的心难道是铁打的?”刘天宝有点气愤。
元熙确实后悔了,后悔不该把他直接推出去。
“那,那我去开门。”元熙自知理亏,有点不好意思。
打开门,门外却空空如也,令儿一愣:“人呢?”
元熙一惊,忙跨出门去。萧容湛倚坐在墙根下,浑身湿漉漉的,好像睡着了。元熙慌了神,伸手去探鼻息。他额头滚烫滚烫的,身子也烫。元熙这才注意到他的脸色有多差,简直就是变了一个人!
“容湛,萧容湛!你别吓我,你快醒醒!”元熙轻轻拍拍他的脸,但他却似沉睡一般,一点儿反应也没有。
“快把他抬进去,轻着点。”元熙几带了哭腔。真没出息,本来是要怪他的,可看他这样就怎么也生气不起来,心里疼的刀割似的。
刘天宝把萧容湛背到元熙房里,拿了自己的干净衣裳来给他换好,令儿烧了热水,元熙浸湿了帕子替他擦拭。他烧的挺厉害,唇色都发白了。
“小姐,我去抓点儿药回来吧?”
“你去叫六子,到库房里,抓点柴胡回来熬水,告诉厨房热水不能停。把胡掌柜买的烈酒拿来一壶。”
萧容湛眉心一直没有舒展开过,想必是很难受。元熙紧紧抓着他的手,心里已经把自己数落过一千次一万次了,干嘛要跟他较这个真呢?
“阿湛,你千万不能有事,只要你好起来,我什么都不怪你了。”元熙悄悄抹了抹泪。
萧容湛似能感觉到似的,把元熙的手攥得紧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