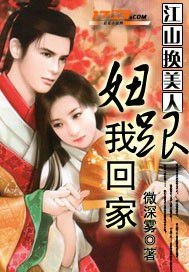容湛的车驾碌碌出了宫门,迎面而来的是宝亲王府的马车。对面的车驾缓缓停住,却不肯把路让开。
容润从马车上下来,跪到容湛的车驾前,朗声道:“臣弟叩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容湛一掀轿帘,望见容润,冲他勾勾手道。容润欣然站到他窗前道:“今儿是什么日子,皇上怎么想起出宫了?”
容湛反问道:“今儿是什么日子,宝亲王怎么想起进宫了?”
容润含笑道:“也没什么,就是来给母后跟皇兄请安。”
“请安?没递牌子就进宫请安,大楚有这条规矩吗?”容湛上下打量了容润一眼,他只穿了一身便服,根本不是进宫见驾的服色,便知道他的目的不单纯,绝对不是进宫请安这么简单。
容润一听这话,嘿嘿一笑,道:“皇上真是明察秋毫啊,臣弟这么一丁点小小的破绽,都被皇上识破了。臣弟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啊。”
容湛,微微一皱眉:“马屁拍的有些过火。”
“过火吗?臣弟不觉得啊?臣弟说的是事实嘛!”
容湛淡淡一笑道:“别那么多废话了,到底来干什么的,直说吧。”
容润颔首道:“皇上,臣弟要是说了,您可千万别不耐烦啊。”
容湛凝了他一阵,轻轻地嗯了一声。
容润往身后看了一眼,摸摸脑袋,道:“其实臣弟是特意在这里等皇上的,臣弟听说卫府的公子最近在府中苦读,一副誓要名列三甲的架势。”
容湛凝了他一阵,又嗯了一声。
“臣弟正是来说此事的。”容润看了看容湛的车驾道:“皇兄,卫家的事,卫大人也跟臣弟说过了,卫成庸是个倔脾气,您就算跟他讲,也是讲不明白的。还不如,顺其自然,合乎天道。”
“怎么个顺应自然,合乎天道?”容湛将车驾帘子掀起,道:“上来说。”
容润谢了恩,起身上了容湛的车驾。
“宝亲王妃如何了?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吗?”容湛问道。
容润略一滞,点点头,笑道:“谢皇兄关心,元月的伤口已经好多了,只是什么都记不起来,其实记不起来也好,忘了过去的事,人就不会痛苦。像现在这样,一张白纸,从头再来,心里没了那么多负担,反而落得轻松自在。”
“负担?”容湛有些诧异,但很快就对这个话题失去了兴趣,转而问道:“你刚才说什么顺应自然,合乎天道?”
容润愣了一下,皇上的话题转的有点快,快到他还没反应过来。
“臣弟的意思是,感情上的事,强求不得,强扭的瓜不甜。当初咱们大家一力促成成庸和宬香的婚事,可偏偏那个时候成庸的心里没有宬香,就算皇兄动用权利,把宬香硬塞给他,他也不会爱宬香的。而没有感情的婚姻只会给两个人带来痛苦,这一点,皇兄的心里应该一清二楚。”
容湛凝了他一阵,脑海里浮现出赵可贞的影子,当初的赵可贞不就是想尽办法,希望能得到自己的宠爱吗?可她越是想方设法,容湛就越是不给面子。赵可贞虽然作恶多端,但她的痛苦是真真切切的。她落得那样的下场,容湛少不得也是要富有一些责任的。
“你是说……”
“相反的,彼此牵肠挂肚的两个人,就算是千山万水,千难万险,也是阻碍不了的。就像当初皇兄对皇嫂那样,虽然有母后和赵可贞的阻止,虽然有现实中的种种阻碍,但皇兄对皇嫂的感情始终如一。但是皇兄,你不觉得那段日子过得的确有些艰难吗?”
容湛凝着他,微微垂下眼睑,不由得笑了笑:“六弟,你从前可不是一个能把道理讲的这么透彻的人呐。”
容润的笑意渐渐从脸上凝固下来,变得有些惆怅:“皇兄,这些都是臣弟亲身经历过后,才明白的道理,皇兄是身在福中,不知道世事的艰难。皇兄跟皇嫂是一见钟情,虽然有些许的阻碍,但老天保佑,命运却一直是顺畅的。不像臣弟,不像赵可贞,更不像宬香。”
容润的声音渐趋有些低落,好像一个没命运愚弄得丧失了斗志的人。
容湛望着他,笑笑:“才刚多大年纪的人呐,说出的话像老头儿一样。”
容润抬起头,恳切道:“皇兄,臣弟求你了,就给卫成庸一个改过的机会吧。宬香也不小了,难得遇上一个如此心仪的人,你若是断了卫成庸的前程,就等于把宬香的婚姻也毁了。皇兄,宬香是咱们唯一的妹妹,你我已经经历了太多的波折,她一个女孩子,千万不要再把他推到不堪回首的路上去了。”
“六弟……”容湛有些失语,他这次见到容润,觉得容润有些变了。从前的他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邪王,容湛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从容润的嘴里听到如此沧桑伤感之语。
容润才多大的年纪?鬓发间有已经有几根白发了。
“皇兄,感情可以很弱小,也可以很强大,在皇权面前,它微乎其微,但却能像蔓草一样,坚韧不拔,哪怕将它折成千万断碎片,它已然不会有所改变,而且,它会用它强大的生命力,生长的漫山遍野都是。皇兄,情这种东西,禁是禁不住的,您还不如想办法,顺应自然,也算是圆了宬香的一个梦。”
容润说着,笑的有些苦涩:“皇兄不知道,每次看宬香跟臣弟提及成庸,那种发自内心的喜爱和失落,臣弟看在眼里,连臣弟这个做哥哥的都觉得心疼,更何况是她自己?她坚持了这么久,好不容易看到希望了,好不容易看到成庸对她有情。皇兄要是为了颜面而阻止了她们,宬香的心里会有多痛苦?我想皇兄也是会心疼的。”
“宬香是朕的妹妹,朕何尝不心疼?”容湛望向容润,还是有些迟疑:“只是这样做,太便宜这个卫成庸了。他想要就要,不想要就甩开,当朕的妹妹是什么?现在他想要,朕还不想给了呢。”
容润含笑道:“皇兄既然也是心疼宬香,我看不如刁难刁难卫成庸也就罢了,既让他知道天高地厚,又让他明白这份感情来之不易,要学会珍惜。”
容湛挑挑眉,道:“六弟今天特意来这儿等着朕,想必已经把一切都想好了,那朕倒是想听听,六弟说的刁难,是怎么个刁难法儿。”
容润勾勾唇角,道:“臣弟看,卫成庸既然要参加大楚今年的恩科,那不如就看看他的真才实学。若是他能一具名列三甲,就许他娶宬香,他若是考不中,就要他下次科举继续考,考中为止。”
容湛凝着眉,上下打量了容润一番,他这主意听起来不甚高明,而且还有点故意偏袒的意思。
“六弟,卫成庸学识渊博,杂学旁收,朕扪心自问,论做文章,朕都未必能跟他比上一比,朕怎么看,六弟都像是在帮衬他。还有,他若是考不中,就不许娶宬香,难道他一直考不中,宬香就要一直等下去吗?”
容润噗嗤一声笑了出来:“皇兄,臣弟就说您是明察秋毫,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的眼睛。”
容湛皱了皱眉,假意推了容润一下,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怎么突然向着卫成庸说话了?”
容润敛去了笑意,款款道来:“昨日卫大人曾经找到臣弟,说他这个儿子读书简直读得发疯,每日只睡不到两个时辰,茶饭不思的。整个人都魔障了,请臣弟去劝劝他。”
容湛点点头:“所以你就善心大发了?”
容润应了一声:“皇兄,成庸这一次是真的回心转意了,他曾对臣弟言道,他先前的心都在兰玉身上,却忽略了身边真正对他好的人,兰玉固然好,那不过是一个幻想罢了。就像书中自有颜如玉,难道谁还真的在书里见到过美人不成?读书人自己幻想出来的,不过是个执念罢了。再加上强权一逼,他也就顾不得自己的真心了。知道那一日宬香陪他在雨中罚跪,他才忽然想明白,其实他根本就不曾了解过兰玉,而宬香,每日都像影子一般围着他,久而久之,他也就习惯了。”
容湛长长叹了一声,其实现在回想起来,他也有许多对不起赵可贞的地方。当初若不赌气娶她进门,若不是无意之举给她燃起了希望,赵可贞未必就会变成后来的那个样子。
容湛有些沉重,虽然他没有爱过赵可贞,但却不由得想真心实意对她说一声抱歉。
“成庸真这样说?”
容润点点头:“皇兄,人能认清自己的心,这是多难得的一件事啊。成庸到底还是个正人君子,把宬香嫁给他,他不会亏待宬香的。”容润说着笑了笑:“至于那些所谓的舆论,堂堂皇室何必怕它们呢?所谓舆论,不过就是人为扭捏而成,可以说成黑,也可以说成白。反正,多数老百姓是没有思考能力的。那些不怀好意的人可以制造舆论,难道皇兄就不能扭转舆论吗?”
容湛凝着他许久,朗声笑了:“六弟,你可真是长大了。”
容润笑道:“皇兄,既然这个疙瘩已经解开了,不如你我兄弟去痛痛快快的喝上一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