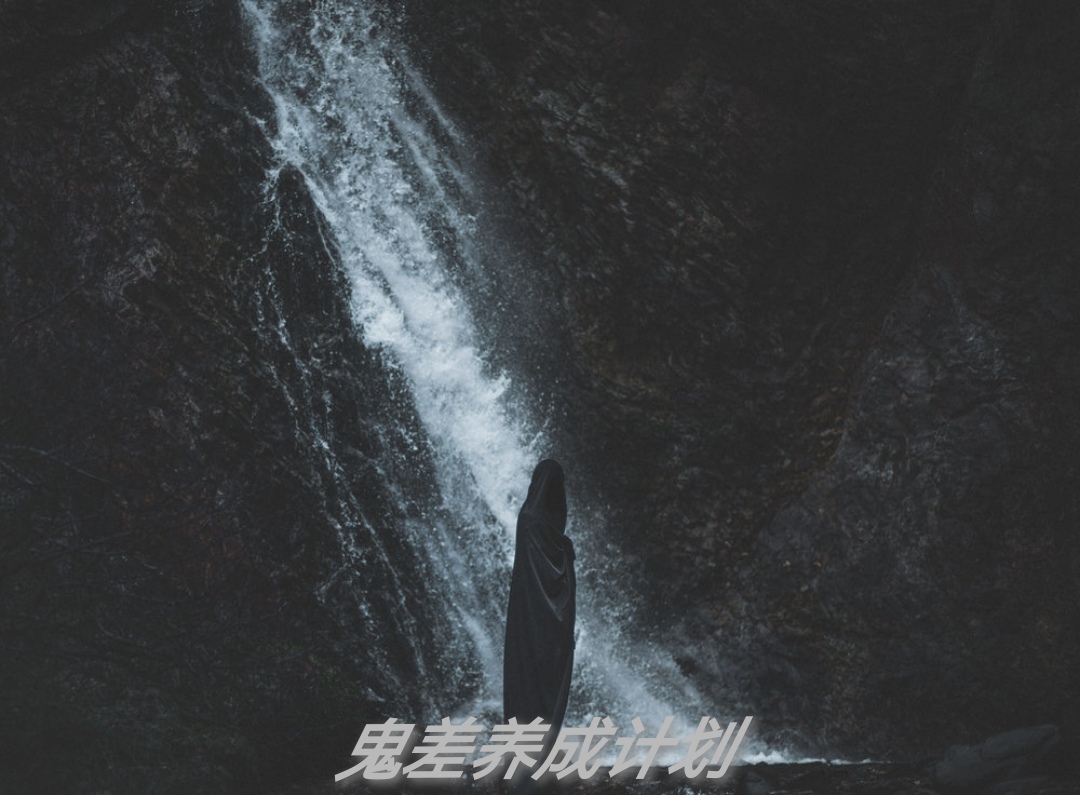守财以为自己把话说的粗俗些,便能更加符合自己的身份,显得情真意切。万没想到,这“亲嘴”二字一处,反倒招致了王太医的一阵嫌恶。
“混账东西,怎么敢在宗主面前如此放肆?”王念恩一拱手,道:“宗主,这等不知尊卑的畜生,实在不该留在府里,依微臣之见,不如打上几十板子,叫他懂些规矩,再带来问话。”
花月一惊,守财是钟妈妈手下的人,若是连他都逃过不一顿毒打,那么自己又算得了什么?少不得要被带到一处无人之境,一杯毒酒,或是三尺白绫,杀掉了事。悔之悔之,令儿到底是宗主身边的人,连王念恩都故意在偏向令儿说话,自己又长了几个脑袋,敢去动她?这不是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吗?
守财虽然察觉王太医在偏心眼,但毕竟跟钟妈妈手下多年,也见的一些大场面,尚且应付得了。便忙磕了几个头道:“小人没上过什么学堂,一时心里惶恐,就出了粗语,求宗主恕罪。宗主若是责罚小人,小人情愿领受,但小人有句话,冒死也要说。”
他拱起手,做一副正气凛然的模样,道:“宗主位列一方诸侯,但却没有擅自诛杀朝廷大员的权利,周玉的死是个烫手山芋,还望宗主以此事为重。”
涂博安把两道粗眉拧了拧,心里开始别扭。这个下人生的好一张利嘴,照这么说,他反倒是那个识时务的俊杰,我们这一文一武两个朝廷命官,反倒成了不知轻重缓急的人吗?
“宗主……”涂博安一拱手,便要插话,被元熙伸手拦住。
元熙低头望着跪在面前的守财,问道:“照你的意思,这事儿应该怎么办?”
守财看了令儿一眼,思量片刻,道:“小人知道令姑娘是宗主的贴身侍女,也知道令姑娘在宗主心中的位置。纵然宗主舍不得,但眼下已经到了危急关头,宗主应当舍小全大。至少要给朝廷一个交代,不然朝廷怪罪下来,宗主又该如何自处呢?”
花月怔怔的望着守财,默默地听他说,只待他说完,便胡乱的磕一通头表示赞同。
元熙长长舒了口气,凝了令儿一阵。
令儿反望着元熙,心里一阵心痛,自己从小就跟着小姐,熟知她的心思。她只要一个眼神,自己便知道她在想些什么。这些年来小姐一直要风得风,心想事成,几乎没遇到过什么让她惆怅的事情,因此令儿也就许久没有见到过这样的神情浮在元熙脸上。
看来,小姐这次是真遇到难题了。令儿咬咬嘴唇,虽然周玉不是她杀的,但兹事体大,若是小姐需要一个人出来顶罪,令儿愿意做这个顶罪的人。
令儿丹唇微启便要服罪,元熙却缓缓摇了摇头,示意她不要说话。令儿一时住了口,怔怔的望着元熙。
元熙静下来寻思片刻,忽的一阵心悸。这才察觉自己已经落入萧容深精心布置的一个圈套当中。周玉知道他的前任因何而死,自然不敢重蹈覆辙。他明明知道自己最擅查账,怎么敢顶风作案?得到的银子并不算多,完全不值得他如此大费周折。而且他用的手段也并不算太高明,但凡是个懂行的人便能一眼察觉。
答案只有一个——他是受人指使的。
是萧容深授意他如何贪污劳工的工钱,并授意他如何做账引起自己的怀疑。萧容深知道自己嫉恶如仇,看到账目有假,定然会追查下去。萧容深也了解周玉,知道周玉并没有太大的能耐,却心狠手辣,被自己逼迫得紧的时候,定然要狗急跳墙,炸毁矿山。还有一种可能,炸毁矿山本来就是萧容深的命令。
没有了矿山,归云州的军饷就无从筹办,没有军饷,军心就会动摇。这才是萧容深的终极目标,他想让容湛在归云州兵败,甚至是死在军中!
至于东林州这边,或许萧容深已经吩咐眼线去杀周玉,然后嫁祸给自己,或许守财本身就是萧容深的眼线,这个尚且存疑。无论如何,周玉已经死了,萧容深计划的最后一环已经启动,这是毋庸置疑的。
元熙不禁打了个寒颤,这一箭双雕之计,未免太毒辣了吧?
“把令儿带下去,先关押在后院的空房里,不许她自尽,也不许她逃掉。”
守财得了令,心下按捺不住的一股雀跃,知道自己的计谋这么容易就得了逞,换做谁都会心花怒放的。守财站起身,把令儿手臂往身后一板,像抓鸡一样把她带了出去。
令儿自然是不会自尽的,更不会为了这件事逃走,她知道元熙不会杀她,更不会相信自己杀了人。令儿含恨望了守财一眼,守财赢了一局,傲然望着她,满眼都是不屑。令儿又转头望向花月,花月亏着心,慌忙躲闪开来。
令儿冷笑道:“你们两个狗男女,这样做就真的不亏心吗?”
守财咬紧牙关,喝道:“杀人偿命,纵然你是宗主的人也没奈何。多说无益,还是趁早认罪的好。”
涂博安狠狠的啐了一口,暗骂道:“宗主府怎么出了这等小人?”他转头望向元熙,强压这一肚子怒火:“宗主,这分明就是陷害,您看他那个小人得志的样子!”
王念恩垂着手,默默不语,涂博安扯扯他的衣袖,道:“王兄,你不说句话?连我都看明白了,莫非你们还?”
沉思半晌,元熙才缓缓开口道:“吩咐下去,给守财加一个月的月例银子,再把花月赏他做媳妇。”
涂博安愣了一下,那种卑鄙小人,宗主还要赏他银子和老婆?这不是黑白不分吗?一把握住剑柄,道:“宗主若是不信,我去把那卑鄙小人痛打一百鞭子,看他到时候招供不招供!还敢不敢冤枉令姑娘!”
王念恩滞了一下,冲涂博安努努嘴,反问元熙:“宗主这样做,莫非是想探探守财的虚实?”
元熙唇角溢出一丝冷笑:“你看他像吗?”
王念恩又摇摇头:“不像,这个守财一上来就漏洞百出,连个谎话都编不匀实,若真是和亲王的人,再差也不会差成这样吧?”
“话虽如此,就不知道他是不是装的。”元熙将手叉错,凝神道:“即便他不是,也不代表咱们府里没有和亲王的人。眼下太子爷正在归云州与吕国作战,用的就是咱们东林训练的新军,依仗的是东林提供的金矿做军饷。可以说,东林州就是太子的靠山,若是咱们这里后院失火,对太子爷有害而无利。”
王念恩默然点点头:“宗主想放长线,钓大鱼?”
虽然是杀人嫁祸,但眼下最重要的并不是找出真正的杀人凶手。因为那个凶手就在眼前,而且骗术并不算高明。
萧容深的眼线虽然不及六爷手里的爪牙,但也绝非善类,不说无孔不入,但也称得上是见缝插针。周玉一死,萧容深的奸计已经得逞。倒不如,反守为攻,把他的眼线先钓上钩,再借那眼线设个局,反将他一军,把他部署打乱,或许还有翻盘的机会。
“若我没有猜错,从我回到东林州开始,到现在所发出的一切,都是和亲王有意设计的。”
一语惊醒梦中人,元熙这话一出,把王念恩和涂博安都吓了一跳,不由得啊了一声。
“周玉的死,应该就是和亲王计划的最后一环。只要他借机扳倒了我,就等于断了太子的后路。”元熙默然道:“这事儿怪我,是我明白的太晚了。”
涂博安把脑袋摇了摇,愣生生的说道:“我到现在还没明白呢。”
王念恩一点即通,听了元熙的几句话,便猛然明白了萧容深的整个计划。失声道:“莫非,他是要断了归云州的军饷?!”
“那样太子爷不就跟着完了?”涂博安说着,打了个冷战。他是从军中调上来的,没有军饷对于一个正在打仗的军队来说意味着什么,涂博安再清楚不过了,也失声叫道:“宗主,咱们不能坐以待毙啊?”
的确不能坐以待毙,元熙眯起双目,萧容深想让她一败涂地,那是做梦。老天让她重活一世,是为了赢,自己绝不会再栽在他的手里。
元熙凝神静气,幽幽问道:“咱们府里还压着一个东林州的师爷,东林州的头把交椅惨死在咱们府,这秘密绝对瞒不住,咱们只要抵死不承认就行了。咱们越是不承认,和亲王就越要到宗主府里找证据,你们不妨猜猜看,他的人在府里会与谁联系?”
“万师爷?!”涂博安和王念恩异口同声的叫了起来。
元熙轻轻嘘了一声,又道:“关押令儿,不过是做做样子,把水搅浑,才好一网捞上大鱼。借以诱导和亲王下错关键的一步棋。”
涂博安心里的一团疑惑算是烟消云散,轻松的挠挠头,道:“我还纳闷呢,连我都看得出令姑娘没有杀人,怎么宗主和王兄竟然糊涂了?原来如此。”
王念恩唇角露出一抹狡黠的笑意,看来元熙是想把萧容深的眼线钓上钩。既然有了主意,王念恩才又了心思开玩笑,道:“怎么?你以为你忽的比宗主还聪明了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