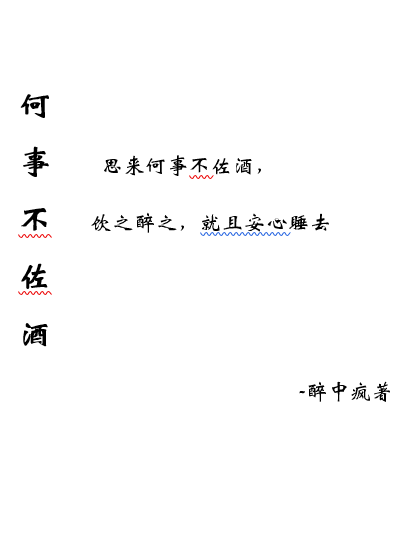8
随着去茶楼约定碰面的时间越来越近,马天目开始变得坐卧不宁。他始终拿不准主意——是自己贸然前去,还是坐视不管?贸然前去的话,想想都觉得是个笑话。那个苦苦寻找组织的人,想必是望眼欲穿,急切盼着找到组织的这天。但邱老板一死,自己显然成了孤家寡人,谈何代表组织?那岂不成了笑话;如若不去——马天目想到这里,断然否决了这个看似合乎情理的想法。那些在街上东奔西走的日子,已让他饱受寻找和等待之苦;想必对方也是受着同样的煎熬。如果这次失约,好不容易取得的联系必将中断。再找起来,定会石沉大海。还是去吧!马天目这样劝着自己。自己就代表一次组织又怎样!况且尚存一线生机——如果小马能够尽快找到那个他所认识的人,到时候联系上,自己妄称“组织”,也就变得名正言顺了。
准备赴约这天,马天目特意精心装扮了一番。换上一身长袍,戴了一顶礼帽,又临时凑了一副圆框墨镜。对于墨镜的配置,完全出于他个人喜好。对于接头时那种神秘的想象,已让他开始兴奋起来。皮包是从家里带来的,显然很符合他的这身装扮。皮包里装了上次从书店新买的书。作为接头信物,也是再合适不过。具体到见面时的种种细节,由于没了邱老板的指示,也就只能见机行事了。
他早早到了约定的茶馆。由于时间尚早,茶馆内鲜见客人。要了一壶茶,坐在一处靠窗的位子上。从这个位子看过去,不但能看到外面街上的情形,坐在茶馆内喝茶的客人,以及走进走出的来客与去客,也尽收眼底。
一个上午的时光慢慢耗尽。马天目显然成了茶馆内最奇怪的一名客人。起先他双目炯炯,茶兴方浓。由于戴着墨镜,别人是无从看到他目光的。只能看着这个戴墨镜的人将头转来转去,大口喝茶。一壶茶很快喝完,便要了第二壶。等第二壶喝完时,马天目便频繁去上茅厕了。到了第三壶茶上来,马天目便显得无所事事起来,偶尔将放在桌面上的书端着,饶有架势地看上两页。又想到书是接头信物,是该端着,还是应放在桌上?实在拿捏不准。有一段时间茶馆内涌进大批客人,看来是茶客登门的高峰期。而马天目所坐位置,是一位熟客常坐的。那位熟客显然在这一带名气很大。茶馆里的伙计不卑不亢地来和马天目商量:先生是否还要续茶?马天目说,续茶,当然要续茶!伙计说,如果续茶的话,先生就请换一个位子,这位子是别人预定了的。马天目一愣,装作不高兴的样子。伙计说,看您来得早,以为到了这个点儿,先生的茶也早该喝完了,所以事先没跟您打声招呼。马天目听出伙计话里的轻薄,只能乖乖换了另外一个位子。这位子处在茶馆比较显眼的地方,也不便东张西望。只能定下心来,被动等待对方来找自己接头。
几壶茶水下肚,马天目只感到腹胀如鼓。由于坐在这个显眼位子上,也就不能丢下桌面上的东西,随意去上厕所了。正等的焦躁,小便憋得难受之时,一位客人在他对面悄然落座。
马天目抬头看,见此人虽穿着周正,却骨瘦如柴。面色黑黄,嘴唇呈猩红色,像是一个痨病鬼。马天目神情专注起来,从墨镜后偷偷打量这位茶客。见客人要了一壶最便宜的茶水,看也不看马天目,神色淡然地小口啜饮着。
等了半天,对方竟毫无反应。马天目有些扫兴。却不想那客人对他悄声发话:先生是来这茶馆应聘的吗?他说这话时,头也不抬,嘴唇贴在杯沿上,像是在吹杯口的浮茶。那话听上去不像是在向对方发问,倒像自言自语。
马天目转转眼珠。擎头说,是啊!
那你是从哪里看到的招聘讯息?
马天目又转了转眼珠:华亭路和延庆路一带。
哦,客人点点头。放下茶杯,看着马天目,说,那就对了。
马天目摘下墨镜,看着对方。眼神中闪过一丝惊喜神色。却不想客人又低下眼睛,看也不看他,低低咳嗽着。咳了一阵,掏出手帕,抹着嘴,端起茶杯,喝了一大口,像是那茶水是止咳的良药。这才低了眼睛,说,可我记得,这家茶馆没有去那一带张贴什么招聘广告呀!
马天目顿时愣住了。对方的这句问话,显然超出他的应对范围。一时不知如何作答。如果揣摩前面所讲,对方无疑是自己要等的人。却忽然冒出这一句,又显然不合对答的情理。踌躇之际,马天目又无所适从地再次将墨镜戴上。暗想一不做二不休,就按事情的原委回他算了,便答道:我一是来应聘,更主要的,是来找亲戚。
说到这里,加之神情紧张,膀胱涨的实在难受,马天目站起来,故作提示说,先生,我去方便一下,烦请你帮我照看一下桌上的东西。特别是那本书,丢不得的。那是我亲戚特意要我带的。
陈烈已来茶馆待了一段时间。坐在一个更加隐蔽的角落,静心观察所有出入茶馆的客人。但等来等去,都不见符合要求的接头人。直到马天目频繁去上茅厕,陈烈这才将他发现。如按照时间来推算,这位举止怪异的年轻人显然是在等候着什么。那几个围坐一桌,消磨时间的老年茶客除外,他是在茶馆内呆得时间最长的一位。况且那几个老头完全不符合接头要求。谈笑风生有余,却全然不顾周围的环境。只有这位年轻人,举目四望,坐卧不宁。而带在他身边的一本书,确也符合了接头要求。只是除了这本书之外,应该还有另外一件重要信物,那却是马天目未曾想到的。也是陈烈迟迟不来搭话的缘故。
他有太多的顾虑。但迫切需要和组织上取得联系的渴望,最终打消了他的这些顾虑。况且他已对茶馆内外有过仔细的观察,确认没有任何异常。这才上前和马天目搭话。所幸的是,除了缺少那件重要的信物之外,马天目所答,虽磕磕绊绊,却完全正确。
不多会马天目回来。见对方已完全换了一副神情。大概是喝了一壶热茶的缘故,陈烈的脸色好看了许多,高高颧骨上泛着一抹潮红。待马天目落座,陈烈隔着桌子,伸手触了一下马天目搭在桌面上的一只手,马天目只感觉他的手指冰凉。身体倏地一颤。
只听陈烈说道:我找你们好久了。话音未落,又迅速将手抽回。
正是那手心与手背的短暂相触,顿然让马天目百感交集起来。他近乎哽咽般说道:我也找的你好苦!
陈烈说,还是长话短说,请你务必记住——回去转告娘家亲戚,就说我有值钱的东西要交给他们,让他们做好收货准备。另外……陈烈低下头,显出为难样子,沉吟半晌说,另外,就说我最近日子很苦,需要他们的接济。我也知道,他们定有难处,但这段时间,我实在撑不下去了……
他的话被一阵痒痛打断。喉咙里轰鸣做响,仿佛隐着一串惊雷。
马天目忧心看着他。说,好!看他如此难过,便俯身问道:你是不是病了?
陈烈歇了咳嗽,眼里泛着泪光说,老毛病了,也无大碍……说到这儿,陈烈忽然问,这次来,你怎么没按暗语上的要求带全接头信物,险些误了大事!
马天目一愣。却故作镇静,望着对方难堪一笑。指着桌上的书说,这不……
暗语中不是写着嘛——读书识字的优先考虑。你只带了一本书,而没带字帖呀……幸亏来这儿喝茶的读书人少,如果每人都带一本书来,你让我怎么识别?
马天目顿悟。却掩饰说,都怪我粗心,把字帖忘家里了。
陈烈看着他,一丝疑虑的表情从脸上悄然划过。却很快消失不见。
此时马天木想到自己假扮“组织”的身份,又看对方如此落魄,想来生活一定窘困之极。暗想等找到真正的组织,说不定是猴年马月的事。自己从家里带来的钱还有一些,何不先接济他一下,便说:我们约一下下次见面的时间,我先带些钱过来,你找医生去看看病。
陈烈思忖一番。感激地冲他点头。说了下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又补充说,下次碰面,你就仍带这本书好了。字帖就不用带了。
马天目拈起桌面上的书,调个方向,将书名呈给对方,问:就这本吗?
陈烈点头。额头冒出细汗,手撑腹部,胃又疼起来。掏出手帕擦擦额头,有些忧心地说,如果我不能来,就让我爱人去和你联系。到时候,她会系一条暗红色丝巾。接着,陈烈又将头凑过去,对马天木说了一些什么。
等准备起身离去,双方要各自付饮茶的费用。马天目见陈烈在衣兜里掏摸,摸了半天只摸出一两个铜板。便抢先付了账。又将自己身上所带银元全部送他。陈烈自然推托。马天目将钱放在桌上,率先走出去。
那一天天气出奇地好。酷热已消,秋日将近。门前的梧桐和银杏辟出大片阴凉。抬眼看街巷远处,天空在屋宇间切割出参差的蓝色深渊。让江韵清感到今天是一个好日子的同时,又莫名感到一丝忧伤。她想起遥远北方家乡的秋色,天空也该是如此碧蓝。除有稀疏云朵点缀,更能看到远处黛青色山影。天空澄澈,与之对应的,应是那恬静河流,像两块封冻的琥珀,彼此镶嵌。
犹感一丝伤怀之余,江韵清更多注意着巷口。这已是她第三次从家里出来。之所以这样惦记,一是她期望陈烈此次前去和组织接头,一切顺利;二是担心他的身体,这么久矣不回,能不能撑得住!她在巷口站了一会,听到有邻居开门,正准备转身回去,忽见一瘦弱身影从巷口那边晃进来,被阳光衬着,很虚幻的样子。她皱皱眉头。看他走得摇摇晃晃,没走几步,便在街边台阶上坐下。勾着头,像在歇息。她凝神远眺,直到他再次摇晃着起身,向这边迈开步子,这才确定,那便是陈烈。快步迎上去,什么也不说,一路搀扶着他回家。
从巷口走回家里的那几步,似乎耗尽陈烈全部的力气。刚一踏进屋门,便轰然跌在椅子里。江韵清猛地揪心起来。看他的脸色,以及袍子上扑满的灰土,料到这次出去碰头,肯定凶多吉少。又见他脸色虽难看,却难抑喜色。喊过在摇篮旁照顾弟弟的华姿,手抖抖索索,从兜里掏出几块糖来。
江韵清洗了一块毛巾,弯腰给陈烈擦脸。陈烈说,我来吧。接过毛巾,艰难抬起胳膊,自己擦着脸和脖颈。
江韵清轻声问:咋样,顺利吗?
陈烈点头。说,一切顺利。他细细给江韵清讲述整个碰头的过程。但令江韵清不解的是,既然顺利,何至于将自己搞得这般狼狈。她用毛巾揩着陈烈胸前的污渍,问:这是咋弄的?
听到江韵清如此问。陈烈难堪一笑,说,都怪我,如果我直接回家,就碰不到这倒霉事了。接着便讲起来:我走到半路,给华姿买了两块糖,又想到天气就要凉了,小弟还没有一件御寒的衣服,恰好我对那一带比较熟,知道拐过两条街,便有一间卖旧衣服的市场。便拐过去。刚过第一个街口,迎面遇到一支游行队伍,举着横幅标语,是因前几天日本浪人火烧毛巾厂,打死打伤路人和巡捕,给政府施加压力、讨要说法的。我与他们擦身而过,本来大家相安无事,却不想大批巡捕正好赶来,说刚刚接到上司命令,不准再搞这种扰乱社会秩序的游行集会。双方交涉无果,巡捕便采取武力驱逐。我被人流裹挟着,朝另一条街口跑,却哪里跑得过那些身强力壮的人,跌了几个跟头,身上又被踩踏了几脚。后来又被赶上来的巡捕抓住,好一番盘问。那些巡捕见我身子虚弱,这才好歹放我回来……唉,小弟的衣服没买到,倒遭遇了这么一场风波,真是晦气。也让你担心了。
江韵清埋怨道:家里还有两件大姐穿过的旧棉衣,我抽时间改改,华姿和华川过冬的衣服也就有了,何苦你来操心。见陈烈面色难看,知道他不愿动大姐用过的东西。便岔开话头问:你饿了吧?我这就给你热饭去。
江韵清正在厨房忙碌,忽听华姿凄厉的叫声。那叫声怪异,惊得她毛骨悚然。三步并作两步奔向客厅,不想却和华姿撞了个满怀。华姿满脸惊恐,拽住她的衣襟,指着屋内说,快,快去看看我爸。
陈烈手脚摊开,死人一般仰坐在椅子里。嘴角挂着一抹暗褐色血渍。那血渍呈喷溅状,洒在胸口,在他身前砖地上淤积了好大一滩。人似已窒息过去,却不知是陈烈见了血,加之又饿又怕,急火攻心,只是一瞬间的晕厥。等江韵清用毛巾将他嘴角身上的血渍揩净,陈烈倏忽醒转,听到江韵清和华姿低低的啜泣,便不禁将华姿揽在怀里,说,乖,没事,爸爸没事的,不要吓着了,啊!
将陈烈安置好,江韵清开始翻箱倒柜,将家里不多的几个铜板全部凑在一起。陈烈看着她,虚弱地问:你要出去,去做什么?江韵清不答,扭身穿着外出的衣服。待到江韵清准备出门之际,陈烈凄苦笑着说,我知道你想去做什么……你想去请医生,给我抓药。但你手里的那几个铜板,又能去哪个医生那里抓得药来。江韵清在门口站着,背对他。陈烈说,没用的……江韵清后背一阵抖动,猛地转身,又去屋内翻箱倒柜,出来时,怀里抱一堆衣服,有自己从家里带来的衣服,也有姐姐江汰清留在家里的衣服。将衣服堆在桌面,又去找一块兜衣服的包裹。陈烈安静仰躺在沙发上,华姿和坐在摇篮里的小弟张着眼睛,呆呆看着江韵清的举动,不知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陈烈叹息一声,说,我这病,本来不想治。但如果不治,恐怕撑不过这个冬天。我要走了,你大姐不在,我又担心你和孩子们,还有那些“东西”……咳,那就死马当活马医吧。那些东西你不用拿出去典当了,我这里有几块银元。你拿上,一块银元抓药,一块银元买些杂粮,也好熬过这段日子……
江韵清松开包裹,停止了动作,背身流泪。等情绪平复,走到陈烈身前,从他手里接过那沉甸甸的银元,说,姐夫,你瞧你说的这都什么话。你听我的没错,吃两副药,身体保准能好起来。你的身体垮了,你让我怎么撑下去!
陈烈牵牵嘴角,眼底涌出一汪泪,却假作欢颜说,我听你的……对了,你去望平街南京路转角,寻一家叫做“济善堂”的诊所,找陈求真医生,他是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的毕业生。刚出道不久,功底却是深厚。我去年到他那里看过几次。那里收费虽高,但碰到穷苦的病人,是不收任何诊费的。你提“林攀”的名字,他应该记得。就说是老病灶了,他会给你开方抓药,省了我去的麻烦。
那天夜里天气骤变,先是刮着大风,后又下起骤雨。冷雨敲在窗上,不禁令人心生寒意。后又有密集的冰雹落下来,擂着屋顶,远远近近之处,听来的全是那坚硬声响,时而密集,时而疏落。好在屋子里并无多少寒气。那茶红色药汁冒着腾腾热气,给人带来一些安慰和希冀。陈烈喝下一碗药汤,额上发了些细汗。来不及催促江韵清去睡,自己便疲乏地沉入梦里。江韵清在他的床边呆坐良久。停了电,她又找来蜡烛,一直陪坐到烛油耗尽。见陈烈睡得安稳,这才去另一间卧室里和两个孩子挤在一起,草草睡了一会。
第二天相安无事。
到了第三天,陈烈的病情看似安稳了些。虽断不了咳嗽,吐血却是止住了。整个人恹恹躺在床上,茶饭不进。用手一探,只觉额头发烫,却原来是发了烧。江韵清又跑了诊所一趟,对陈求真医生说了病人的症状。陈医生说发烧是免不了的,但病人总该吃些东西……现在来问诊的病人太多,我抽不开身。要不这样,你告诉我地址,等我明天抽空去一趟,当面诊断,也好对症下药。江韵清自然巴不得陈医生去,但想到陈烈的叮嘱,却不敢将家里的地址擅自讲出来,便懦懦退了出来。回家路上,天瞬间晴了,但气温骤降。一阵风吹过,头顶的树叶钱币一样哗哗摇落。江韵清缩着手脚。走得心内不住泛起一阵阵悲凉。
那天夜里,陈烈病情加重,咳血不止。人眼看就不行的样子。江韵清徒劳地用毛巾为他擦拭,那些黑褐色的败血,在灯光下闪着怪异光泽,犹如湿重棉絮,沾了她一手一脸。甩不脱,擦不净。她跺着脚,气急败坏对陈烈说,你挺住,等天亮,我就找陈医生过来。
陈烈喉咙里咯咯有声,瞳孔内的余光虽是越来越暗,却愈加温和。他抬手朝某一个方向指了指,江韵清起初不解,倒是一旁的华姿对江韵清说,爸爸在找什么东西。
江韵清环顾屋子四处,一脸茫然。低头问陈烈:你在找小弟?
陈烈摇头。抬手又指。
还是华姿机灵,转身到衣柜旁,手扶衣柜的把手,侧身看着他的父亲。
陈烈点头。华姿打开衣柜,逐一指着柜子内的衣服。拿起一件,陈烈摇头,再拿起一件,陈烈仍旧摇头。脸上是一副烦躁样子。抬起的手指,上举,嘴里吐着微弱气息:丝……丝巾……
柜子上面的隔断华姿够不到。江韵清三步并作两步,抢到衣柜旁,拿起一条暗红色丝巾,举在手里。陈烈点头,抬起的手放下。
待江韵清将那丝巾递到他手里时,他竟回光返照般精神了许多。手捧丝巾,凑在脸上。那丝巾团成一团,蓬松拥着他失血的面颊。鼻翼抽动,显然是在嗅丝巾散发出来的味道。那样子说不上贪婪,却让人看了,着实觉得有些残忍。
陈烈动了动,示意江韵清俯身过来。江韵清将耳朵凑过去,听到陈烈用微弱的气息说,七天之后,上午十点,你,你去“联合书局”……带,带上这条丝巾,去和接头人联,联系。记住,要务必小心,不落实好他的身份,不,不要暴露我们的住址……不,不要,轻易把文件交出去……
江韵清脑子里一团浆糊,唯恐遗漏陈烈话中的每一字。便择重要讯息再次印证了一次,并一一记在心里。这些话讲完,陈烈已耗尽体内最后一丝气力。他示意江韵清退下。抬手将女儿华姿招过来,也不能说话,只微笑着,抬手擦着华姿腮上的泪,又轻抚着她的发辫,动作越来越缓。他想让江韵清把儿子抱来,看上最后一眼,却再不能张口。手指停滞在华姿额头,软沓沓向下滑落。划过华姿的眼睛、脸腮、嘴角,等滑到下巴上时,便再也不动了。
华姿等着,领受着父亲的抚摸。转眼看父亲的情状,不由扯开嗓子,嚎啕大哭。
江韵清发出一声母狼般的嗥叫。却马上意识到什么,抬手捂住华姿的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