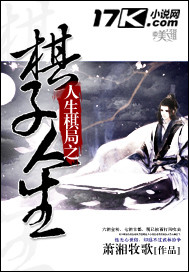经过一季炎夏的炙烤,塞外是最先凉快起来的,当南人还在为夏末秋老虎的淫威而屈服的时候,塞上之人已经开始准备一冬的粮食了,届时,人们才能吃上新鲜的窖藏大白菜,喝上准备了好几季的家常烈酒。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夏天过得颇不平凡,连续了好几天的大旱灾让许多百姓田地里的庄稼颗粒无收,不仅没有余粮交给他们所在的州县军阀,就连自家能糊上一张口的粮食也是捉襟见肘,只能靠平时省吃俭用下来的一点点藏在隐蔽处的余粮来打发日子。
但是这毕竟不是办法,当凶形恶煞的小吏催命般地来向他们收饷银的时候,他们只能拿出一点点省了又省的几串铜钱来应付差事,而这已经是他们所能作出的最大努力,但是那些奉了上司死命的官差们又怎么会仅仅收到这点钱财就算完事呢?
于是,一个个不可避免的悲剧便发生在了这片已经遭受了无数战火的土地之上,无数家破人亡的百姓流离失所,拖家带口地向着他们心目中的那些美好家园行去,期间,或有人倒在了饥饿疾病下,或有人死于流兵贼寇的打劫。
总之这不是一个平静的秋初,也不是一个普通的秋初,历史从这个秋天开始走向了无数条分支小路的一条,而这一条却令其后中国千年的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后世人有知能在这样的情况下生活的话,他们会发原来所熟悉的能倒背如流的史实全部偏离了原来的轨道。以一种不可思议的角度向前发展,而且这样的发展方向无疑是好的方向。
同样是塞上,同样是初秋,云州的日子也与北边的大部分城池没有什么不同,人口、土地、军力、器械,一切看起来都很普通都很平凡。
或许唯一的不同可能就是原来统治云州的一直都是大唐委派的官吏,而现在的云州却是由着一支外族人所控制,这在一些有着中原正统顽固思想的人的头脑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怎么能让那些荻夷占我边寨城池呢?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他们或许没有想到的是,沙陀人南下到长城以内已经是大唐几百年前的事了,沙陀人的杰出的族长硃邪赤心当年曾经帮助大唐平过边寨的叛乱,因而立下了大功,这让这个外族第一次获得了中原正统政权大唐帝国的好感,所以才允许他们住在了长城以内而不把他们当做关上那些个蛮夷之族来对待!
说起沙陀人,这可以追溯到曾经被大汉帝国追杀得体无完肤的突厥之上,沙陀人正是突厥西突厥的后代,传到大唐这一代,他们以硃邪为姓,世世居住在塞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进到被视为禁地的中原地带,然而,现在的他们却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或许,这从他们勇敢地帮大唐平了屡为边患的吐蕃赞普之后就已经注定了!勇气和武力才是这个世界里通行无碍的凭证!
如今,沙陀人从原来的一个几乎可以被人忽略小族发展到了现在拥有着边关大城云州、带甲万人的边关大势力,他们族人的骑射能力简直是中原那些所谓的雄壮之师所不能仰视的,就如当今沙陀人李国昌的儿子也是唯一继承人李克用来说,此人少骁勇,军中号曰“李鸦兒”;一只眼睛瞎了,所以又号“独眼龙”,他的威名盖于代北。曾经从群豪射猎,或挂针于木,或立马鞭,百步射之无不中的,群豪都敬他以为神。此人,也是未来云州人的希望!
饥饿的恐怖并没有因为沙陀人的强壮就没有降临云州,相反的是,处于干旱集中地的云州基本上可以说是颗粒无收,相对于其他城池人口要远为多的此地,饥荒程度是最为严重的,那些汉人百姓因为闻名于沙陀人治下的云州是一处好去处而曾经拖家带口移居此地,到了今日才发现原来的决定是多么的错误,虽然沙陀人对于要民众课税这一最能让普通百姓害怕的举动不是太热衷,在他们的治下每个成年人每月只要纳米十斗就算是承认了沙陀人在云州的统治地位,也就保住了自己在云州的居住权,而在城外的那些庄稼们就可以任自己开垦任自己耕种了,这对于以农业立国的古代人来说简直是无上的好事了!
然而,灾害同样在那时是没有什么方式可以阻挡的,干旱一到,千里禾苗毁于一旦,一年里所种下的希望化为泡影,生存面临着无上的考验!
云州的灾害情况尤其严重,这让沙陀人最高的统治者,年近七旬的李国昌,这个曾经为沙陀人命运而带领族人奔波于长城内外的老人,感受到了一丝异样的气息。
这个时候的他站在云州高大的城楼之上,看着秋日里稍显凉意的天地,发出一了声长叹。
满目所看到的,并不是已经长成的庄稼,反而是一片异常空旷的空地!这片本该满是黄澄澄的希望的土地变成了一片空旷,这让他的心感到悸动。
这片天地是这样的空,这样的旷阔,令人心惊的旷阔!!!
李国昌向来不是一个以感情用事的人,但是看到这样的影像还是不由自主地叹了口气,为整个云州的百姓为整个沙陀人的希望而叹息,老天,为什么你又要在这些已经饱受折磨的百姓已是伤痕累累的作品之上再添上一把盐巴呢?到底想怎么样呢?
天地不仁,在这个时代里简直不仁到了极点。未来,或许有更为恐怖的事情发生,在前方空旷的天地里,塞满的可能不将是空旷,取而代之的可能是尸山和血海!
斜阳如血,李国昌略为佝偻的身体在光线的照射之下却又是显得那么的屹立不倒!如同一坐山般的屹立!
或许,这就是不甘心于天地的驱使而为此站直了的身体!有了千千万万这样的腰板,还会畏惧天地给人带来的灾害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