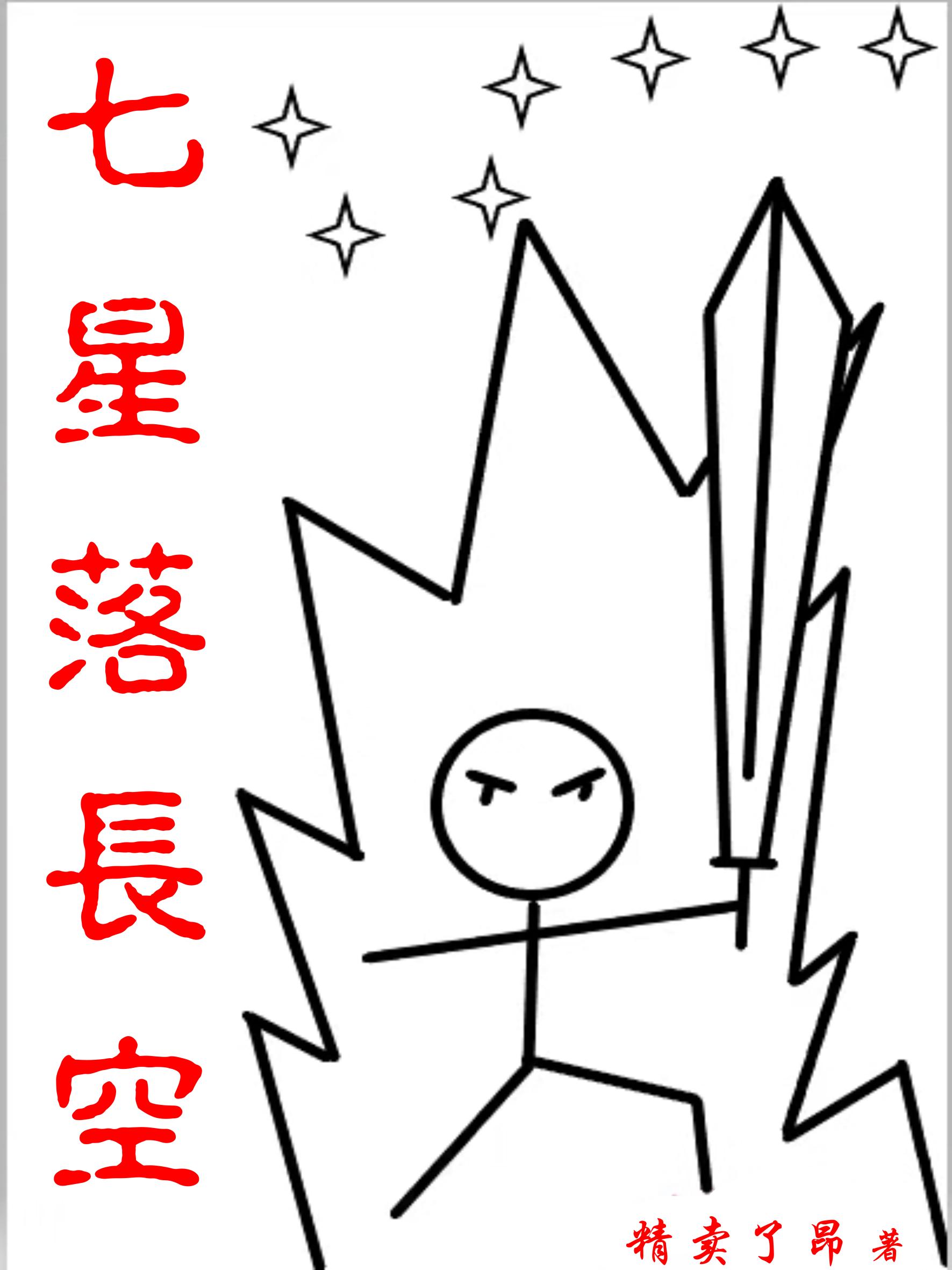客室里陈亦卿板着脸问:“你还是要如此一意孤行?”
朱玉轩站在他面前,经过激烈的争吵脸红脖子粗地别过脸,用坚定的眼神表明心迹。
陈亦卿无奈地挥挥手,苦笑叹道:“好,好,那你就去吧!”
朱玉轩眼中一抹喜色看着陈亦卿,表情还有狐疑。
呆坐在一旁的玲珑“呼!”地站起身,用近乎绝望的声音对陈亦卿说:“不可以,你怎么能允许……”。
如同歇斯底里的疯女人般,玲珑扑到朱玉轩的身边。他高大的身躯挡住了从门口刮入的寒风,玲珑想拉住这温暖的源泉,可她只能颤抖地伸出手在他身上捶打。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这么固执,为什么要丢下我,你去查那些又有什么用!我当初……当初清清楚楚的听到爹说是官兵,你有多大的本事!你为什么就非要……”
玉轩含着不舍的苦笑看着失去理智的姐姐,他伸出手拉住因情绪激动站立不稳的玲珑,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地告诉她:“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从那死人堆里走出来的唯一理由,是我活在这世上的人生目标。我很想知道,到底是谁让我们的家就这么没了?!”
他将我们的家说的很重,他并不奢望玲珑能跟他并肩作战。但他希望姐姐能够理解并支持自己的决定,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想让他如缩头乌龟般继续沉迷在这样安稳的生活中。
朱玉轩越说越激动,他握着玲珑双臂的手加大了力气,她有些喘不过气来。眼前的男人像极了曾经从山上围猎回来的父亲,那个杀红了眼的令她又爱又怕的男人。
朱玉轩骨子里是像他的父亲的,那个看起来平凡又寡言的普通村民,可在每年秋猎的时候,他却是朱家村后山上最凶狠的猎户。
陈亦卿默默叹口气,打开他轮椅的扶手,原来这里竟也是中空的,他从里面拿出一个伸缩拐杖。这也是他自上次遭遇了赵二狗的突袭后做的改装,他的轮椅扶手里现在不仅有拐杖、碎银两,还有匕首。
他平时用来辅助行走的双拐并不在身边,所以只能借助这支小拐杖移动,显然不足以支撑他的身体。虽然他整日里坐在轮椅上,大概是玲珑经常给他做些鱼啊鸡汤啊补着,他的个子并不矮。即便瘦,但全部体重靠一条腿,一个拐杖行走还是困难。
不过几步的距离,陈亦卿在这腊月天里都走得出汗了。他从玉轩手里接过摇摇欲坠地玲珑,淡淡地开口对玉轩说:“你若真是下定了决心,便走吧!”
他又转而拍拍玲珑的肩膀轻声道:“玲珑,玲珑,你听我说,如果你阻止不了他,那倒不如就当从此便失去了他。”
朱玉轩的神色很复杂,当初逃离朱家村的时候陈亦卿曾对他们说过:“从今往后,我们三人是只能相信、依靠彼此的至亲,但是也必须是最没有关系的三个人,我们不能成为彼此的负累和软肋。
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们遇到追兵,你们一定不要想着来推我,不要管彼此,只需要跑,自顾自的跑,能有多快跑多快。”
当初听到陈亦卿这么说的时候,他还不过是个十岁的孩子,并不清楚这话里的重量。可是经历了这五年,他们从一无所有到如今在浔阳商界小有名气,他的五年可是比别人的十年都要来得成长迅速。
摸着下巴上渐渐长出的青涩胡茬,玉轩觉得从一开始陈亦卿就是算计好了的,他们这些人注定只能同富贵,却无法共患难。
他失落,但是他也感激陈亦卿。
即便如今他的语气和态度显然是要跟自己划清界限了,可是,陈亦卿不仅将他从朱家村带出来,给了他生存的可能,还让他积累了不少财富,不然他连走到京城都不可能,如何能打探到更多的消息。
更重要的是,这几年跟在陈亦卿身边,他学到的那些做生意的手段和思路,让他很有自信,即便现在离开了陈亦卿的庇护,他依然能给自己创造活下去的条件。
玲珑不理解,可陈亦卿能清楚地感受到朱玉轩的心情。同时,他也比大多数像朱玉轩一样不理解女人心事的大男人们,更能体会玲珑的感受。
被生活压地几乎生不如死的时候,女人身上往往有股坚韧的力量。这力量或许来自她们强大的内心,又或许因为她们天生的母性,她会为了自己想要保护的人强大得坚如磐石,韧如蒲草。
就如同当初十二岁的朱大妞,她可以不畏死人,不惧危险,用稚嫩的肩膀将他的宝哥哥抬出来。又用最温暖的笑容,最温柔的语气不断的鼓励幼弟。
可女人也很脆弱,当她们拥有安稳的生活,便如同易碎的瓷器般,经不起生活的磋磨。
就如同现在的玲珑,过去的岁月中曾有过的伤痛如一颗珍珠,被她自己揣在腹中,不断不断用自己的心血将它包裹打磨,甚至在记忆中美化,这样至少没人去挖她就不会痛。
她会编织谎言骗自己,迷惑自己,让自己相信她从一开始就是如此安稳美好的姑娘。而以后她也只想守着自己的书桌画美丽的衣服,守着她的针线框子,绣漂亮的图案。
可朱玉轩不同,他是男人,他是热烈的不可妥协的热血少年。
面对风霜雨雪他宁可来个痛快,让自己如同被大风刮折的树般,即便倒下仍旧是掷地有声的,他受不了生活中细碎的消磨。
所以当初在地窖中,三儿不断试图要冲出那个井盖去跟那杀害自己父母的匪徒拼命,哪怕是看一眼到底是谁杀害了他的父母。他需要清楚明白的死,他宁肯要个这样的痛快。
当他被高出他半头的姐姐死命地捂着嘴,拉到地窖的另一端时,他只想着有一日我要高过姐姐,那便是他当时的目标。
当生活安逸,他又不愿只沉浸在那细腻的儿女情长中,他需要为自己不断的寻找目标,去解答心里的疑惑,去创造更能让他有成就感、满足感的生活。
此刻的陈亦卿,他也在不断的调整目标。
一开始,自废墟中醒来,他的眼前只有一张小脸如花猫般的大妞。对于现在自己所拥有的这些温暖的房间,可口的食物,还有不断积累的财富,他根本不敢想或者说是没有时间想。
他只有疲于奔命,先活下来。
从能吃一顿饱饭,到能有瓦遮头,再到如今比起说是目标,更准确来说,他的心里对于自己所做事情的定位,已经变成是一场追逐的游戏,又或者说是他想摆脱那些阴暗晦涩的想法而给自己的刺激罢了。
所谓的目标,不就是在你每个不同的阶段,那个指引着你走下去,让你有生存的动力,不同于安于现状吃饱就行这样的无趣人生,又和能吃一顿饱饭一样重要的,活着的动力。
陈亦卿的这个目标,就如同已经运行起来的火车,不断的加速。
现在连他自己这个驾驶员都不知道,自己接下来会想要驶向哪个轨道,这辆车上现在有工作人员在和他并肩行驶,也有不受他控制的乘客在推着他前行。
可是只有这列车飞速的运转着,疯狂的往前跑,他才能感觉到生命的鲜活,生存的乐趣。
比如赵孬蛋,他和娉婷去找来的那摊看似无用的烂泥。
他交待赵孬蛋,或者说现在有了人样的赵全,去打听徐臻臻的下落,不过两日他就一板一眼的来汇报:“徐臻臻自从在宝月阁受伤被冷藏后,一直到宝月阁被浔阳士子们逼着结业,她跟宝月阁上上下下的人就没什么来往,交谈也不多。
宝月阁关门后,许多没有签卖身契的下人就各自散了去,或是回老家务农,或是到别家做工,也有的姑娘们找个差不多的人家就嫁了。
徐臻臻一开始并未离开浔阳城,而是靠着积蓄租住在浔阳的贫民区,中间还去找过一个同乡亲戚,可她那个说是姐姐的人,也过得不好,并未能帮上她。再后来便有人见她出了城,至于是回家了还是去哪里了没人知道。”
赵全拍着胸脯跟陈亦卿保证,“臻臻姑娘肯定不在浔阳,要是在城中不论是去哪家做工或是嫁人了, 我肯定能打听出来。”
并且这赵全还有所进步,不仅认真的打听了徐臻臻的下落,还主动问陈亦卿:“公子可否需要我托人到她家乡再打听一下?”
既然人已经出了城,陈亦卿便不再执着,对于徐臻臻的遭遇他有同情有愧疚,但追究下来事情的起因到底是她自己犯错在先,他的处理并无不对。
何况当时她走的时候,陈亦卿不仅没有扣工钱,还给她多结了半个月的。陈亦卿自问扪心无愧。不过她就这么走了,陈亦卿有些可惜少了个人才,也对一个姑娘孤身上路觉得担忧。
既然留不住徐臻臻,陈亦卿亦不再执着,那日在古月寺门口,他悟明白了一些道理,这些道理跟他身后讲究“四大皆空”的佛寺显得格格不入,但让他觉得又充满了斗志,生活变得有意思起来。
他还有好多事情要想、要做,徐臻臻很快便被他和赵全忘到了脑后。
浔阳城中人口众多,熙熙攘攘来来往往的人群中,赵全和平时没有两样。可他近来却多了不少朋友。这些人中有些原本就是他的旧相识,有些是新近喝酒认识的。
这些人的身份都差不多,都是这城中大户人家的厨房管着采买的大厨或二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