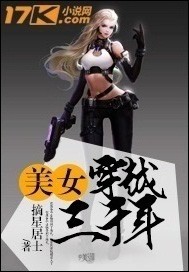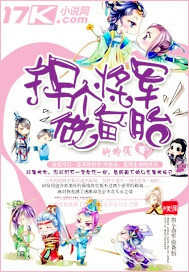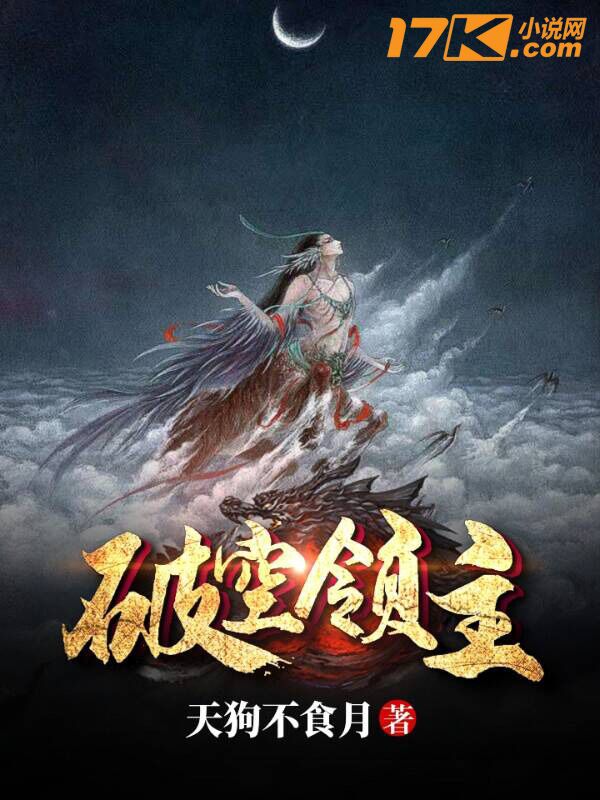陈亦卿到底是年轻且因着“掉了玉佩”那板子只是打在表面,雷声大雨点小,刚开始是皮肉有些疼,却疼了不足半日回来看也并未红肿,在家休养了两日喝了几副汤药便好了。
再去竹枝巷看王启顺,他在的那一间牢房关着的都是些小生意人,并不太懂牢里的世故,即便知道了也宁肯自己挨过去也不舍得辛苦赚来的银两。王启顺因为挨了板子只能趴着,伤口还未愈合倒又烧了起来。
“对不起”陈亦卿垂着头,轮椅放在王启顺的床头,屋子里只剩下他和王启顺。
“你这道的是哪门子欠?”王启顺嘿嘿一笑,道:“又不是你打的我。”
“可是……因我而起……”
陈亦卿的情绪异常低落,为了显示自己是理直气壮做生意的,既按时上缴赋税又与犯人张常胜并无甚瓜葛,从出来那天,陈亦卿依旧是生意照做门照开。连日里玲珑招呼宝阁衣柜,玉轩照料河西味道,与平时并无两样。
可在家休养了几天,略好些就赶忙来看王启顺,经过玉桥街,眼见一街两巷的店铺都寥落了许多。张家大门上贴了封条还有人把守,张家的店铺,连着自己刚刚买来的那四间也都暂时查封。是由州府发包出去还是没收就此封了,还没有消息。
白家的铺子因也是张常胜的产业,白奶奶的租子打了水漂不说,店铺也是不能再开了,更可怜的是白奶奶,一把年纪挨了打受不住,回来没两日又赶上风寒,竟去了。
经过白家门口,里里外外都是挂着白麻布,还是在锦绣布庄采买的。白家孙女白珠哭得异常哀恸,自幼最疼她的便是奶奶,如今不过是租了张家的铺子,被带进府衙问话,可也就是一天话的功夫,人竟没了。
白珠刚刚嫁了船老大许大仓家的儿子,可许家的船也因着是张常胜的产业一并被查封了。刚刚做了新娘子,还没开始幸福生活,夫家就没了依存,娘家又是这般情景。
百姓只知道人死了是要去衙门告状的,但人从衙门出来便死了,又可以上哪说理去。
想着那个最八卦的白奶奶,那个关心着自己婚事总打自己主意的白奶奶,那个在河西味道刚开铺时充分发挥玉桥街“宣传委员”职责,替他们不遗余力宣传店铺的白奶奶,陈亦卿如同被子捂了头,闷得他喘不过气来。
而王启顺的铺子是他自己辛苦半生盘下来的,与张家并无关系,若不是自己刻意的结交张夫人,王启顺便不会受此劫难。陈亦卿恨自己的小聪明,恨自己利用完王启顺又利用张家母子。
这一切都超出了他的预料,他不过是想在这一世平凡普通的渡过一辈子,不求通达不求富贵,安安稳稳的能吃饱饭能穿暖衣。享受一下没有雾霾的空气,再于秋日坐在自家桂花树下晒晒太阳就可以了,终究还是自己贪心了,他常说做生意不能贪心,可是对于金钱的渴望让自己还是背离了生存的初衷。
“我,是我……是我结交的张常胜,是我惹祸上身的”陈亦卿不敢去看王启顺的眼睛,只能低着头忏悔道:“我以为我搬走了,你和念恩就不会被我牵连,我以为远着你们,你们就能和竹枝巷人们一样安安稳稳的过生活……是我错了……”
“呵呵,呵呵”王启顺竟笑了起来,“你知道张常胜要出事?”
陈亦卿摇摇头。
“你知道他犯了什么事?”
陈亦卿依旧摇摇头。
“那不就得了,你根本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怎么能是你的错呢?更何况你结交他了么?你若真结交了他还能坐在这里跟我说话?”王启顺含笑道:“我们这些小家小户的人又不是张爷的朋友,不过是偶尔入了他的法眼,他赏我们些生意罢了。他在我们这里一年喝的汤加起来还不如他去醉仙楼一顿饭花的银两多。
就算说是有张夫人帮衬着,念恩和玲珑才能做起成衣生意又如何?如今我们打开门做生意,谁都穿得我们的衣裳,怎么能预料到谁要出事就不与其来往了呢?”
陈亦卿欲言又止,但听王启顺一席话到底心里还是放下了些,至少在与他最亲密的人眼里,他并无不妥便够了。
“唉,你看你白奶奶,租了张家的铺子年年也不过是将租子交与他的下人,连话都未与张常胜说过,不还是……唉!这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呢?舞象之年的孩子,心思别太重了,让自己喘口气吧,如今你有了锦绣布庄的利钱,就算歇几天也饿不死的。”
陈亦卿苦笑道:“说起白奶奶,我还是要去上柱香的。这几日,便留玉轩在家照料您吧。铺子里自有伙计们,我就几个店巡视着便罢了。”
白家的院子里,逼仄又显杂乱,白奶奶家也是从外地迁至浔阳的,故而在这里也并无太多亲戚,倒是玉桥街并着周围几个巷子的街坊邻居们都陆陆续续来悼念了。虽然是从她这里总守不住别人秘密,传了不少别人的糗事,可以说是玉桥街第一狗仔队了,可她生前总有人找她牵线搭媒的,不少人仍是惦念这个热心肠的老太太。
白珠依旧在灵前跪伏着哭得跟个泪人一样,她的新婚丈夫来劝了两回,赔了三日,见劝不住她便叹叹气先家去了,毕竟许大仓也因张家的事情被抓走了,还未放出来,一家人还要靠他这个儿子回去商量营生。
见程祥推着陈亦卿进来,他端坐在轮椅上,虽是不能行动,且也刚刚经历牢狱之灾,但依旧看起来风姿还是不同自己家人的落拓。
陈亦卿着了一身素衣,虽身上无甚装扮,却显然看起来同从前不一样,也不知是不是常听奶奶念叨他如今是做大生意的人,生意都做到北街了,竟觉得他看起来到底是带着些贵气了。
想着奶奶曾念叨过将她配给陈亦卿的话,再看看如今自己娘家和夫家都没了收入来源,可陈亦卿却出落得比从前更好了,真后悔当时嫁了这个不争气的,自己怎么就没王家妹妹那福分可以守在陈公子旁边!白珠忍不住想扑到陈亦卿身边,靠一靠他宽厚的肩膀。
陈亦卿看着白珠跪在那里哭得伤心,殊不知她是在心里骂她那挨千刀的相公没本事,于是好言相劝:“白珠妹妹,请千万节哀,保重身体要紧。”
听着他温温柔柔的喊自己“白珠妹妹”,白珠哇的哭得更伤心了,不住的念着:“亦卿哥,亦卿哥哥……”
倒是听得陈亦卿有些毛骨悚然,好像她哭得不是白奶奶,跟没的是自己一样。于是赶紧给白奶奶上了香,便急急地离了白家。这一晚上陈亦卿可没少打喷嚏,也不知道是被白珠念叨得了,还是真的有些伤寒。
皇城里的权贵,或许双手并未沾过鲜血,甚至未握过兵刃,自有元帅将军为他们浴血杀敌。上位者或许并无意要人姓名,也总有揣测上意者替他遇佛杀佛。几年前的朱家村是这样,如今的浔阳城又是这样。
权利到底是什么东西?追逐它的人们为他着迷乐此不疲,被它踩在脚下的人们,却命如草芥不值一提。也不知远在京城的天子可知这穷巷里有位为了家人辛勤一世的老人,因着一顿打便没了性命。不知道近在北街的官府里端坐着的大老爷们可知,他们的审判调查牺牲了无辜的性命,竟让浔阳城如此不宁。
或许他们根本不知道,但或许他们知道也不在意,即便略表遗憾却仍不会改变他们的手腕。与他们口中的天下和大义比起来,这些寻常百姓的悲欢离合,实在不值一提。
从白家出来,二月底的春风和缓地吹着那些白幡,似是白奶奶游走的魂魄般在陈亦卿眼前晃来晃去,他捂着心口,想哭却流不出眼泪。
不足半个月雷厉风行的拘捕、查证,张常胜的罪名坐实,一干与其罪案有关人等均已被一网打尽,其家人也已落网,而其子被手下高宁救走,这高宁也算是条汉子,竟单枪匹马还带着个十岁的孩子,逃过玄武军右营的追捕,可终究体力不支与他的小主人一起滚下悬崖尸骨无存。
看着案卷,玄淇有一丝忧虑,但却对玄武军有足够的自信,是来自潜意识无条件的信任。于是合上案卷,挥手招来跟前的侍从,道:“去看看景副尉那里还有没有什么遗漏,若没事就告诉他,我们可以回京复命了。”
“真的么?”听来人汇报可以回京复命了,景林高兴得从椅子上一下子弹了起来,虽然他在京城也常奉命稽查案件,但是比起这样穿着官服坐在衙门一审就是半月的时间,他更喜欢演兵杀敌,或者捉逃犯之类的刺激活。
“咳咳咳,待本副尉整理了这些案卷,就去向玄参领回话。”景林正正官服挥手打发玄淇的侍从退下。
这边见他刚出去就立马把案卷往一旁的典仪沈心桌前一撂,“沈大人速速把案卷都整理好,我要去更衣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