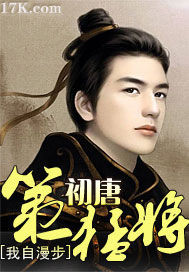吕方是水泊里的一个有名的人物,在水泊中打混讨生活的不管是那路神仙都要给他几分面子。因为他是这八百里水泊中,头一号水匪,世居水泊南面的船山岛上。船山岛,顾名思义,象一艘船,两头高中间低,易守难攻。作为水泊盗匪们的盟主,他出身世家,外人眼里他家世代渔民,知道的便明白乃是水盗世家。
这几天他觉得有些不对劲,往日里他站在岛的背面山崖上,不消半个时辰便能看见有水匪经过,不管是伪装成渔船或是商船,他一眼都能认出是真还是假。按打小养成的习惯,他每天下午都要在山崖上坐到黄昏,看着那一艘艘出发或者归程的船只,他甚至知道哪艘船是哪个贼群的。可这几天,南下找食的船只越来越少,今天他已经坐了快三个时辰了,天色已经快完全黑下来,竟然一艘贼船都没看见。这是怎么了?
他心事重重的走下山,随从见他闷闷不乐,也不敢多说话,只静静的跟着。吕方一面走一面思索着,是不是前些日子在淮南抢够了?不对啊,收成再好的时候也有人南下找食的,这几天非年非节的,都上哪里去了?
吕方感到一种深深的不安,一种恐惧弥漫起来,他忽然停住脚步,侧耳听了听,什么声音也没有,只有呼呼的风从身边刮过。吕方招手把随从召过来,说道:“你去前院里,让金石坚今日夜里安排三班巡夜,命全岛弟兄不可脱衣而眠,家伙全要带在身边。”说完便自顾自的走了。
随从有些讶异,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寻常日子岛上只一班人巡夜,就算是官军捕盗最凶狠的那年夜不过是两班弟兄守夜,怎么今日风平浪静却要安排三班?他心中虽满是疑问,可也不敢怠慢,急忙忙跑去寨子最前头大院里,寻到二当家金石坚,把吕方的话说了。
金石坚也是大皱眉头,对此有些无法理解,最近弟兄们出去打猎辛苦的很,每日早早便睡了,找谁来值班?可也不敢不听,吕方是大当家,自己如是不从大当家之令有的是苦头要吃。无奈之下,金石坚自己走出院子,来到寨中看看哪个房间还有着灯火,便进去拉人出来值夜。不消说,没几个愿意的,只有连哄带吓拉出一队人来。金石坚心道,大当家虽是说了这话,可我也是尽力了,只有两队也是够了。
金石坚安排两队值夜人马,一队在码头附近看守,一队在寨中值哨,自觉万无一失也独自安歇去了。剩下被从家中强拉出的那队人直骂娘。好端端在家中坐着却要我巡夜,自己倒是回去睡觉,一队人虽不敢回住处,却是全走进前院里围着火炉一排坐下,这春天夜里凉得很,便这样到天明罢。
轮着今日值夜的人倒没什么怨言,只是心中发笑。带头的呵呵一乐,说道:“兄弟们,朱老酒怕是正在骂娘咧,这倒霉的被二当家拖出来陪咱们在外面喝风,明日里咱们去笑话笑话他去。”
他手下兄弟纷纷起着哄,也有机灵些的问道:“大哥,朱老酒不是昨日刚值过夜么,怎的今日又要来?”那带头的笑道:“谁知道?听闻是大当家吩咐的,今夜要三班值夜,二当家满寨子找人,谁叫朱老酒这么晚不睡?活该他倒霉。”
又有人问道:“大哥,今天是什么日子,怎要三班?往常却从未有过的。”带头的自己也是心中犯浑,斥道:“大当家做事,你管那许多作甚?干好自己的便成了。”
有人建议道:“我刚见朱老酒好像带人进前院里了,这么久不出来,怕是在那烤火吧?要不咱们也去烤烤,这天寒地冻的,脚都麻了。”码头上风大,着实有些冷,这队人守这码头不住跺着脚。
带头的有些心动,却又有些不敢,犹豫道:“这要是被两位当家的知道了,要吃棍子的。”有人轻推了他一下,说道:“大哥,还是像往常那般,留两个守着,其余人上去,一个时辰一换,夜里风大,弟兄们吃不住。”
带头的正被风吹得打个冷战,紧了紧身上的衣服,想着暖烘烘的火炉,咬牙点头道:“好罢,先留下两个,一个时辰换一次班,留下的招子放亮些,盯着点。”一群人围着争论一番,终于扔下两个倒霉鬼,匆匆跑上坡进院子烤火去了,剩下的两人无奈的相互看看,哭丧着裹紧身上衣服,在风中瑟瑟发抖。
半夜时分,天空中下起雨来,正轮着值班的两人急忙找了艘船的舱房钻了进去避雨。雨越下越大,夜愈发的黑了。春雨绵绵,看这样子,夜里是不会停了。两人坐在船舱里倒还暖和,可比外面强多了。
“你说,大当家这几日是怎的?我几日见他都是冷着脸,和往日大不一样”一人说道。
另一人轻笑:“是不是他那毫州城里的娘子和旁人好上了?”
“莫要乱说,被人听见可讨不了好处。”先前那人忙着止住他。
这人全然不在意说道:“这大冷的天,谁来听咱们说话?也不怕冻死?再说这么大雨,你听得见甚么?”先前那人靠着船篷听了听,唰唰的雨点打在船篷上,哗哗作响,稍隔远些都听不见声音。一想也是,正想说话,却忽然听见外面似乎传来“哗啦”的一声响。
那人扯扯同伴问道:“你听见外面有动静么?”同伴笑道:“就听见你说话,没别的动静。”那人说道:“我方才似乎听外面有水声,要不出去看看?”
同伴有些不耐,说道:“在水上不听水声听什么?要去你去,莫要拉我,我又不是那朱老酒,有舒服的不做,去外面淋雨。”那人想要再说,却又听见外面哗啦一声,声响却是比刚才大了,这次两人却都听见了。
同伴嘀咕道:“是不是下着雨,鱼到水面上透气?”那人接道:“不像,却是象有人趟水。”正说着,忽觉船身一震,象是被什么撞了一下。这时两人俱是坐不住了,在低矮的船舱里摸摸索索的走了出去。刚出舱门,两人都是惊呆了。只见码头上已是靠满了船只,船上不住的往外下着人,那些人下来便直接向寨子扑去,寨子里还是静悄悄。可大门却是洞开,一列列手持长枪的兵士冲了进去,寨子的外面也隐约站着不少人,手中俱是拿着家伙。
两人相视一眼,不敢吭声,一缩脖子,便想躲回舱里去,不想突然有人有人对他们打个招呼:“站在那别动,不准叫喊,叫一声便死。”两人一看,一个方脸的大高个正眼睁睁的看这他们,他披着一个斗篷,头发湿漉漉的,手里拿着一把七八尺许的长刀,刃口开的极长,锋利已极。两人僵在当场,手一松,手中兵器掉落地上,动也不敢再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