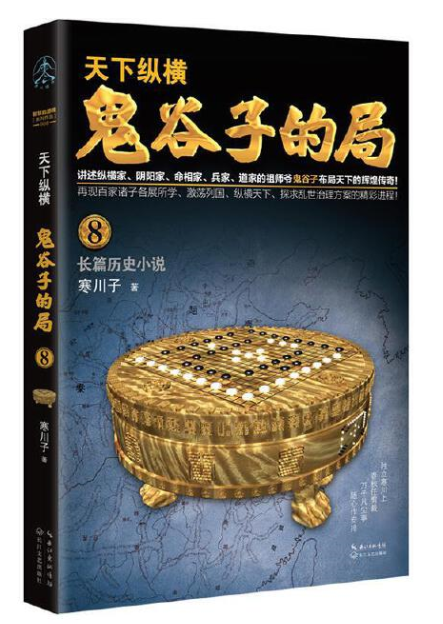覃雁飞脸上一红,他第一次承当如此大的大事,忍不住有些发飘,也难怪,他毕竟也是血气方刚的少年啊。
萧镇远见他如此,知道以他这般样子去了,非坏了大事不可,当下厉声道:“少林寺的厉害你是晓得的,稍一轻忽,你就是粉身碎骨的下场。你在那儿长大的,我是不是吓你,你的心里比谁都清楚!”
这一番话说得声色俱厉,覃雁飞也着实地吓了一跳,脑门上的冷汗便滚落了下来,忽又觉手心暖洋洋的,正是萧秋雪将手放到了他的手心里,当下心中有了着落,抬起头向萧镇远道:“不会的,我想就算少林易主,局势也未必会很明朗,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先把情况摸清楚了,然后才做替爷爷反正的事!”
萧镇远此时脸上才露出了一丝的笑意。
萧秋雪望着爷爷,轻声道:“爷爷,我……”
萧镇远见她神色忸怩,知她心意,摇头道:“你这次就别去了,少林寺里高手如云,雁儿此行若然不成,虽然硬碰不过,以他的身手,全身而退困难不会太大,但要分心顾你,可不大一样了。”
萧秋雪的心中颇不乐意,瞧了瞧覃雁飞,知他心中也没个主意,指望不上的,当下闭了口默默不言。
覃雁飞知道妻子要陪他去,那是因为担心自己孤身犯险,一旦智计不周,有所闪失,后患无穷,不由心中既感激又悄悄抓了她的手,轻轻地摇了摇。
三人正商议着,忽见有四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乡农抬着一支软床,急匆匆进了来,一个大叫着道:“萧老先生,快出来救人啊!”
萧镇远从饭桌上站了起来,出了门,覃雁飞趁着屋里自己和妻子的当儿,悄悄地将她揽到怀中,萧秋雪可没想到他会如此肆无忌惮,忙欲挣脱了,却听覃雁飞悄声道:“好雪儿,我真是好福气呢!”萧秋雪脸一红,知道自己的心思已经被他看穿了,不由又羞又急,却又无可奈何,只得轻声责备道:“爷爷在外边呢!”这时,却听院中的萧镇远“哈哈”大笑道:“果真报应得不爽,竟是你!”
覃、萧两个一呆,心想:“爷爷遇着谁了,这般地欢喜!”覃雁飞放开了萧秋雪,携着她的手出了来,却见院落当央软床上躺着的不是别人,正是昨日里重伤逃走的“八骏”之一的阴阳剑廖苍松,原来昨天他被覃雁飞的龙潭拳重伤,逃出没多少路便伤重倒地,仗着功力深厚,勉强捱过了夜,今晨遇着路过的几个乡农,便被救了回来,他却怎么也想不到那几个乡农抬他去治伤的正是萧镇远的医馆,你说巧也不巧?所以廖苍松睁了眼睛见的却是威风凛凛的萧镇远时,双目暴突,活活吓死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覃雁飞来到廖苍松的尸体前,与萧镇远对望了一眼,伸手给他搜了搜身,找出了随身携带的数千元现金,那把软剑也在他腰间围着,惟独不见的就是他昨晚劫去的那本《太极拳剑经》,不由皱了皱眉,但转念一想:“太极神功教人虚怀太清,对根除戾毒之念大有裨益,它被人拿了去也未必不是好事,说不定这世上又多了一个像殷岩泉那样的大侠呢!只是这本书却是三丰仙长手迹,落入了俗人手中撕了扔着玩或是垫桌脚夹鞋样子可当真是明珠暗投了。
萧镇远当下令人买了口棺材,将剩下的钱分给了抬他尸体来此的众乡农,算做了是封口费,又亲笔给殷岩泉去信细细说明了廖苍松之死的真相。
第二日,殷岩泉派人取走了棺椁,留信道:“知道了,多谢!”五字,萧镇远知他痛心,也不和他计较这些虚礼了。
第三日,福寿寺僧众将了尘棺椁抬去火化,并将一部分舍利子存入了白塔之内,而将大部分舍利子交给了覃雁飞,佛经中原有佛祖释氏圆寂,其舍利子分散置于天下寺庙中供奉的故事,因而其礼节与世俗大异,覃雁飞出身寺院,于之知之甚详,见他们以得道高僧的礼节对待自己的爷爷,心中反而感到一阵心慰。
当天下午,萧秋雪做远行前的准备,还不忘了在覃雁飞耳边叮嘱一些细节问题,覃雁飞从未被人如此细心地牵记过,心中的甜蜜却非任何东西所能比喻的了,但,转而想离别在即,又忍不住有些惆怅,自古多情伤离别,既然心中有了牵挂,也就放不下了,萧秋雪见他表面上虽仍与自己言笑晏晏,甚而还开一些无关要紧的玩笑插科打诨,但却愁眉暗锁,心事缠绕,知他心中舍不得自己,放下了手中的活儿,悄悄走到他的跟前,低头伏在自己的怀中轻声地抽泣了起来,覃雁飞伸臂抱住了她,想说几句安慰她的话,但却咽喉梗塞,一个字都说不出了,其实,此刻的情境说什么有用呢?有人讲,一个人如果活着不开心,即便能够活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又有什么意思?要是开心自在地活,只是要一分钟也就足够了,这一刻他们的心紧紧地靠在一起,谁也分不开,他们坚信他们对爱情的忠贞昭昭日月,天地同鉴,他们也坚信自己的生命从此不仅仅属于自己,以后,他们不会去想,或许他们会长久地分别,或者会遇到他们爬不过的山,涉不过的河,但生也好,死也好,总之是有过了这轰轰烈烈地一瞬间,再过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这一瞬间还是存在着,谁也抹不去了。
萧秋雪渐渐地平静了,但也没肯再起来,覃雁飞听她呼吸匀称,料想她可能睡着了,便将她抱到了床上,想想这几天的日子,虽然过得快乐,去也依然不是风平浪静,想萧秋雪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儿,一下子又怎么可能适应这么多的大起大落和这么快的角色变换。虽然他不可能去替代她,但他却是唯一能够帮助她应付目前的被动和困难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