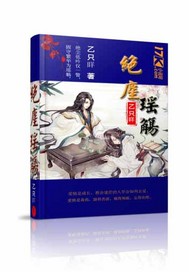门外的侍卫,刚才被法器所控制,所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听至彼岸的叫声后,马上觉察有些不对,冲进来一看,当时就傻了眼。
这里怎么又是一地的血啊?太可怕了。
不一会就找来的医女,医女为葫芦上了最好的药。
彼岸捡回来了葫芦的耳朵,问医女还能不能接上。
葫芦本是上古神兽,耳朵又掉了时间比较短,医女说可以试试给他接上。
医女给葫芦上着药。
彼岸则在一边抚摸着葫芦,柔声的安慰道:“葫芦乖,等医好了,我给葫芦做最爱听的肉松点心。”
葫芦了认真的点了点头,眼睛的泪水和血水,不断的流着。
他妈的,想它也是一个上古神兽,刷干了灵元,居然被人拿去割了耳朵,戳瞎了眼睛。
等老子有了灵元的,非把你们的耳朵都切成片,一双招子都挖出当泡踩。
火灵不知如何找了来。
他原本在后山做苦役,小葫芦一直跟在他身旁。
今天上午他被支走去倒夜壶,不想回来后发现葫芦不见了。
他问了好多的人,没有人知道葫芦去了何处。
他马上意识到不对,他打倒了守卫,偷偷的跑出来找葫芦。
彼岸见了黑了很多的火灵,想着他在做苦役,一定吃了不少的苦。
火灵见了重伤的葫芦,马上就炸了毛了。
“我去杀了那个贱人。”火灵的眼睛中,燃烧着鲜红着的火焰。
“火灵,你且先冷静一下,你一定要找人医好葫芦,葫芦的仇可以以后再报,一定要为它接好耳朵,治好它的眼睛。”彼岸哭着劝道。
火灵听了彼岸的话,也觉得报复并不急于一时,还是葫芦的眼睛和耳朵最重要。
马上抱着葫芦去找灵医,临行前嘱咐彼岸一定要多加小心。
彼岸送走了火灵和葫芦,望着带血的木板。
彼岸从衣服上撕下一条布,将木板上的血擦干,然后将布叠整齐了,放在怀里。
有朝一日,她若能沉冤得雪,一定会为金儿她们立上一个墓碑,再将这布放到墓里。
天色慢慢变黑,彼岸呆坐在干草上,望着空木板。
突然一道闪电划破长空,接着豆大的雨点,一点点砸了下来。
下雨了,院中的血很快就被雨水冲刷得很干净。
彼岸望着电闪雷鸣的夜空,想着今天落可的所作所为。
她一定不会放过落可的,她彼岸,一定一定不会放过那个落可的。
还在刚才在场的每一个人,外加那几条吃了人骨头的狗。
雨越下越大,彼岸总觉得听到破屋有嘎吱嘎吱的声音。
她借着闪电的光亮,在四周找了几次,也不能找到声音来此于何处。
最后她还是回到干草上。
到了下半夜,外边的院子里已经积了好多的水。
彼岸根本睡不着,她还在想着金儿们活着的样子。
这一夜注定无眠。
屋子里的声音越来越大,从“嘎吱”到“吱纽”的声。
彼岸觉得有些不对。
为什么落可已经几天没有来过了,今天却大张旗鼓的来了呢?
以前她来的时间,会带着那些女人。
可今天她来,只是自己带着宫婢来的。
院子那个时候段的异常,就好像所有的东西都停止了一样。
对了,还有一样东西也很异常,那就声音。
这冷院内的声音那么大,为何外边的侍卫却一点反应都没有呢?
按这几天侍卫的表现看,应该是莫忘不许有人再进这冷院,所以落可这几天才没有来。
今天落可一定是动了什么手脚,才避过了外边的侍卫。
可是为什么是今天呢?
只是因为今天是祭天之日,这样莫忘就没有办法管这后院了吗?
她冒这么大的风险来了,却没有将她如何,这一点却是最奇怪的。
让狗吃了金儿们的尸骨,虽然可以折磨她的精神,割了葫芦的耳朵,也可以算是变向的打击报复她。
可以是她怎么就那么痛快的走了呢?
这说明白她目的达成了,那她的目的又是什么?只是为了打击她吗?
不,一定不会就这么简单。
那声音越来越大了,彼岸走到墙角。
墙角好像有水渗了进来了,彼岸低头细看。
墙的底部与地面连接的地方,不知何时出现了一道裂缝。
彼岸马上明白了落可的目的。
她转身向外跑去,可刚跑一步。
天空就有道闪电而下,接着又是一声震耳欲聋的惊雷声。
破屋就在那雷声的掩盖下,瞬间倒塌。
彼岸没有来得急跑出来,整个人被压在了废墟的下边。
不多时,有侍卫发现了院中的异常,跑进来后马上又傻了眼。
今天真是见鬼了,好端端的地上出了好多的血迹,还跑进来一只受了伤的灵宠。
现在房子无缘无故的就倒了,也不知道里边的人,还救不救得活。
马上喊人来帮忙。
这冷院,其实是妖界最初的妖殿旧址,这些年虽然已经破败,当初建造之时,却是用了上好的木料。
整个破屋,正是正殿的所在。
屋子坍塌之后,变成一堆废墟。
侍卫们顶着雨,在里边挖着彼岸的身体。
他们个个都明白,这人若真死了,他们都得变成尸块。
下午他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见了血迹后就差人去禀了殿下。
可殿下正在闭关,无人能打扰。
现如今这种情况,又差人去禀了,还是没能见到殿下。
雨一直下到第二天早上才放晴。
侍卫们在冷院忙了一晚上,几个大的柱子已经被挪开。
一些边角的位置已经被清理干净,目前他们还是一无所获。
侍卫们一个个耷拉着脑袋,已经过去这么久了,就换成灵力强大的人妖,也许还有几份活着的希望,但现在压着的可是一个凡人。
莫忘是第三天的午时才出的关。
他出关后,站在他面前的是抱着受伤葫芦,双眼猩红的火灵,及在一具冰冷的尸体。
彼岸的尸体保持着死时的模样,她的一只胳膊向上,另一只手抱着头。
她满身都是污渍,七窃里是干的血迹。
身体蜷缩,很多骨头都已经被砸碎。
莫忘呆呆的站在哪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这是什么东西?”半晌后,他才问出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