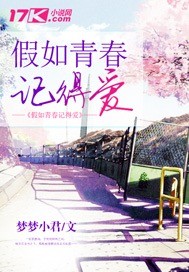第52章 长住医院了
身体越来越重,腰越来越酸,呼吸越来越困难,那种困难难以形容,就好像你连呼吸都要小心翼翼,若有一点疏忽,下一秒就会窒息而死。
那种感觉持续了好几天,我已经忘了那几天是怎么度过来的,只觉得难受。
而且我还发现了我身体的一个新的症状,小便的问题,医生查房,一般都会问体温,大便是否正常,以及小便的颜色。
因此,我形成了观察这些的习惯,我的小便开始泛黄,黄变橙黄,最后,我在小便中发现了血。
然而,还不止这些,发烧像是大姨妈一样,一个月一趟,这次依旧如约而至。
灾难,那个时候,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就是块残缺不全的破布,这边的一个洞,医生好不容易将它打好补丁,那边又破了。
那边的破洞还没来得及补,这边刚补好的破洞再次漏了风。
这样的生活什么时候是个头……
很久没有悲观的情绪,我强撑着身体坐在自己搬好的板凳上靠在墙边,电脑里放的是《新三国》,我本来想看完全剧,顺便涨点知识。
但现在,眼神望着前方,毫无焦距。满身体都是难受,满脑子都是害怕,满眼都是紧张。
爸爸妈妈回老家还没来A城,外婆留下来照顾我,我跟外婆说这些事的话,她也不懂,还徒增她的担心。
但跟上海的医生打电话,他又会让我吃激素。
我不想吃激素……
我依旧是多喝水,多休息,连电脑也不玩了,吃完午饭就睡觉。
身体的疼痛没有减轻,反倒加重了,我连被子都叠不起来了。
那个时候还是夏天,盖的薄被子,我连拿被子的力气都没有,痛,腰痛。
我知道拖不下去了,我终于舍得跟刘主任打电话了。
果然,刘主任听到我说的情况后,让我吃甲泼尼龙片,一顿吃四粒,一天吃三顿。
每天吃十二粒激素,我吃了三天,腰彻底不行了,走路都得一步三挪。
妈妈知晓后,当天就来了A城,我不知道当时的我是什么样子,让人看到会有什么感觉。
但我自己是难受的,身体难受,心里更难受,因为这么多天的忍耐,我觉得委屈极了。
“妈妈,腰好酸,都直不起来了。”我哭笑不得,其实我想哭的,不过可能是习惯了白血病带来的种种折磨,我只是叹了一口气,表示自己也很无奈。
妈妈回A城了,她又带我去了Dr医院。
现在想想,也许一切都是注定的,如果我当时没有将疼痛忍耐到极致,如果医生没有让我一天服用十二粒激素,又或许是,我将所有药都停了……可能也不会有现在的我。
我们到了Dr医院,检查结果,尾椎骨裂,尾椎具体在哪个位置我也不是很清楚。
只记得,刘主任的初步判断是尾椎骨裂,但他不是骨科专业医生。
于是刘主任把对面W医院的骨科医生请来给我会诊,W医院的医生让我侧躺在床上,然后他将手放在我的脊柱的末端,腰中间的位置,按了下去。
疼,锥心的疼!
“这里疼,是吗?”他按着问我。
“嗯。”我咬牙点头。
骨科医生终于把手拿走了,我全身轻松了一大半,他接着回刘主任,说:“估计是尾椎出现问题了,具体情况可以拍个片子看看。”
“嗯,要不然做一个……”
几个医生在商量我的病情,我当时被安排到一个四人大病房,侧身的时候,身体是靠着墙的。
我想听清医生们的话,便翻了个身,姿势成了平躺,紧接着我想坐起来。
但是,骨科医生急忙扶住我,说:“你别乱动,现在尽量平躺着,你的状况很有可能是尾椎骨裂,万一骨头那里又动到了,很容易引起尾椎错位。”
骨科医生说完,又转了头对刘主任说:“这个病人最好让她睡硬一点的病床,这病床软了点,对骨头不好。”
“嗯,待会我让护士把她调到小病房里去。”刘主任此刻完全是骨科医生的下手。
骨科医生的话,我有点不懂,我懵脸问他:“尾椎要是错位了的话会怎么样?”
“严重的话,下半身可能会直接没有知觉,所以你最好是平躺,枕头不能枕太高,床的话……换成硬板床比较好……”
医生说了一大堆注意事宜,我听着心里的紧张感一度度加深。
医生说最错误的姿势就是躺卧,而我在不知道自己尾椎骨裂的前提下,最常做的姿势就是躺卧。
医生说如果要坐起来的话,要尽量挺直腰背,而我因为挺腰的时候,腰酸疼的厉害,弓腰的状态更常用……
我在想,如果我在家的那段时间,稍微一个不慎,尾椎错位了……那我是不是一辈子都要躺在床上了?
带着这样的后怕,我再也不敢乱动了,一直是平躺在床上,就连翻身都不敢随意挪动。
第一次觉得,原来躺着,也是一种折磨。
骨科医生走后,当晚,刘主任就把我换到一个二人病房内。
“自己能走吗?”妈妈问我。
“嗯。”我点头。
二人病房和大病房之间只隔了几个病房的距离,我觉得,这点路我还是可以走过去的。
妈妈扶着我顺着走廊一路走到新换的病房,那个病房还没有住其他病人,目前就我一个人,我走到床边,看到床板上本来铺好的被子给拿掉了。
现在就空空一个床板,上面铺了一层床单,然后是被子。
这可能就是骨科医生说的硬板床吧,我一步三挪的走到床边,脚尖稍微一踮,屁股就坐了上去。
很硬,没有以前睡的病床舒服,第一晚就睡得很煎熬,但一想到睡硬板床也是为了病好,我又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去Dr医院的时候,我还发着热,因此,又是一波退热治疗,一年间,我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这样的治疗。
我开始想,每次都是在激素停了之后,又或是快停了的时候开始发热。
而且几乎每次都是低热,难道我发热,是停了激素的原因。
没吃激素,肺部感染就严重了,然后导致发热。
这是我做出的解释,我将我的猜想跟妈妈讲,妈妈竟然也这样觉得。
“激素真不能长期吃,容易造成钙流失,你看医生让我们每天都要吃钙片就知道了。”
我听到后,心中一直困惑的问题,像是终于得到解答了一样,我问妈妈:“那我现在尾椎断裂是不是也和吃激素有关系,那时候我一天还吃了十二粒!”
我不自觉的张大了嘴巴,心里震惊又后怕,如果真是激素的原因,而我们还傻乎乎的一直在吃。我会不会因此吃死?
如果真是这样,那我真想问问医生了。
当时只想问个清楚,因为我不希望我的病,要一辈子依赖激素,直到身体越来越差,差到所有功能都衰竭。
可是,我不知道的是,我的问题,是造成医生和患者之间出现信任危机的第一步。
记得当时刘主任查房的时候,我问了激素的原因,刘主任没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但他的脸色绝对不是好的。
他没回话,我也不敢再问了,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
不过,之后他就把我激素的量减少至一天两粒,仅他这一个行为,我能想到,我的想法十有八九是对的,刘主任的行为可以说明。
病房新进来了一个病人,我又有病友了,我有点开心,还有点期待这个病友会是什么样的性格,好不好相处。
是个女病人,医院一般都会把同性别,同一个主治医生的病人安排在一间房,这样方便些。
和大多数白血病人一样,她戴着口罩和帽子,我不清楚她几岁,不过我知道她的名字。
因为她的白色口罩上面绣了她的名字,一个“璟”字。
“周小璟。”每次刘主任来查房都这样叫她的名字,我自然就知道了。
她的普通话说的很好,不带一点口音,刘主任和她的对话的时候,我似有若无,都会听到一些。
周小璟,也是一个苦命的人,骨髓移植没有成功,现在又来化疗,准备做第二次移植。
做过移植的病人都清楚,第二次骨髓移植,说明身体又要经受一次清髓过程,但有过一次骨髓移植的身体已经不能和第一次相比较了,移植的成功率会更低,而且人也可能承受不了第二次清髓。
和她相比,好像我的情况还好一点,我有点同情她,可是我们是同样的病,我清楚,她需要的,从来都不是同情。
她比我想象的要乐观,病魔所迫,我们不得不乐观面对生活,因为我们都知道,悲观没用,死可以解脱,却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我们都拥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
她有一个平板电脑,大部分是用来放一个人说书,我是听她说,才知道,那叫评书。
说评书的是一个男声,声线听着很过瘾,剧情的起伏被他说的恰到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