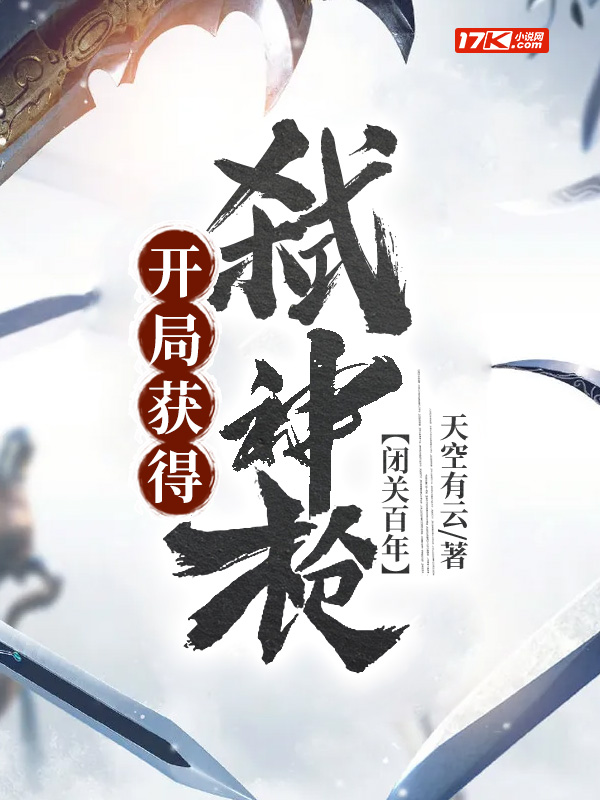第32章
被上帝挑中的孩子
我甚至不觉得这世上真有人的骨髓会和我一模一样。电视里的白血病人最后因为骨髓的问题只能在医院干等着的报导看的太多,我对此不报任何希望。
不过,医院那边还是来了关于找骨髓的消息,妈妈存有刘主任的电话。
电话里刘主任说,让她去一趟医院,说关于移植的事。
M区的房子很大,虽然是老式的两室,没有客厅,但房子很大,有电视,还有床。
床头是出院时医生开的药,还没吃完,妈妈去了医院,我一如往常的靠在床上看电视,等着妈妈回来,同样等着她带回来那个是否有匹配的骨髓的消息。
“找不到和你相匹配的。”
这是妈妈从医院回来后告诉我的,意料之中,但听到后,我的心脏处还是紧了一下。
“那是不是要做半相合的?”我急忙问。
妈妈回我说:“暂时还没确定,要等你爸来,我们再商量,看看现在是做移植,还是怎么样。”
还没确定?是不是意味着也可能不做骨髓移植,我的心凉了大半截,突然期待着想快点做移植。
我问妈妈:“爸爸什么时候会来?”
“已经跟他打了电话,就这两天吧。”妈妈说话的情绪也不高,她接着问我:“晚上想吃什么,我给你煮。”
我口腔溃疡还没完全好,现在也想不到吃什么,就说了句“随便。”
但是,世上最难做的,就是“随便。”可能妈妈听到心里了,以为我生气了,她又说了那句话:“梦梦,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力救你的。”
这句话,从我生病到现在,已经是听到的第三遍了,我突然觉得,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为了安抚我,但更多的是,安抚她自己?
妈妈是不是也害怕失去我……我想到自己刚才说的“随便”两个字,心里酸酸的。
“我哪有那么容易死的啊,之前那个温州的阿姨不是说了嘛,上天就是嫉妒我们太优秀,才让我们得病的,被上帝挑中的孩子,肯定不会差的。”我笑着对她说道。
听到我的话,妈妈脸上的表情也恢复了常态,甚至还带了点斗志,她说:“对啊,拿出信心来,没有全相合的,咱们就做半相合的,医生说你这个年龄是做移植的最佳时期,可以做半相合的。”
“嗯。”我点头。
……
一夜的火车,第三天,爸爸赶到了上海。
为了移植的事,我全程在家,他们在医院和医生商量的移植的内容,我一点都不清楚。只是,他们回家后,告诉我这么一个消息。
“决定让你妈妈移植给你。”这句话是爸爸说的。
“已经做了配型吗?”我问,还有他们谈话的内容,我都好想知道。
妈妈回我说:“还没配型,今天抽了血拿去检查了。医生说,父母和子女配合的点一般都是一半,但因为我们是同性,才决定用我的。”
“如果你妈妈的不行,就用我的,再不行,还有你弟弟。”爸爸补充道。
听闻,妈妈脸色严肃,说:“你不行,我们家唯一的劳动力,万一伤了身体怎么办?”
伤身体?我听到后,有点害怕,我问:“捐骨髓,对身体不好吗?”
“医生说对身体没影响的,我是觉得你妈有胃病,会有影响。”
“你就是嫉妒我能献骨髓。”
爸爸:“……”
我:“……”
和大多数父母一样,我爸妈也是经常一言不合就会吵起来,我也习惯了。
“不会配不上的,除非我是你们捡来的。”我双手撑着下巴,幽幽的说了句。
爸爸:“那我们早把你扔了。”
“哈哈哈……”
欢声笑语,短暂的轻松后,马上就是过年了,医生将移植的时间安排在了年初,我们也觉得过了年后再入舱移植比较合适。
除夕,中国的传统节日,一年的终结,2010年的除夕,我们是在上海度过的,为了迎接第二年的移植手术。
我和白血病的战争,好像才刚开始。
第一次在异乡过年,第一次过着没有年味的年,第一次,和白血病共同过的年。
那天,年夜饭不是传统的鸡鸭鱼肉,我们三个人吃,妈妈只买了条鱼,还有青菜。
我生病,不能吃辣椒,因此红烧鱼的菜单硬是变成了蒸鱼,青菜的卖相倒很好,绿油油的,只是,两个菜,三个人吃,加上临时挂在墙上的白炽灯,这情景顿时有种苦哈哈的赶脚。
“别人家是团圆饭,我们家都没团圆呢。”我笑着说道。
弟弟在老家和外婆在一起,我和爸妈在上海,可不就是不团圆嘛。
其实我的心里酸酸的,但因为不想把气氛搞得太凝重,也不想心情太沉重,我只好笑着说了。有种苦中作乐的感觉吧。
爸爸咽下嘴里的饭,安慰我说:“做了移植,明年就可以一起过年了。”
“明年过年,让你妈做一桌子好吃的,管够。”
“好啊。”我盈盈的应道,回想着在老家那个有点破的房子过年的时候,竟也有点怀念。
年夜饭,一荤一素,无汤无酒,吃了晚饭后,妈妈给在老家的外婆打了电话,问了家里的情况,还有弟弟。
弟弟十一岁,上五年级,我想到匹配骨髓的事,如果爸妈的没配上,要用他的骨髓的话,脑补着那个小时候就胖乎乎,跟在我后面傻傻的家伙躺在手术台上的画面,我就有些揪心。
“砰……”
是烟花绽放的声音,在天还没黑就有放烟花的声音,只是那个时候在远处,听的不是很响,现在天全黑了,小区周边也有人开始放烟花,震耳喧天的烟花声,让我真正领会到“夜上海”这三个字。
在上海的第一个除夕,其实很多事都不记得了,除了晚上此起披伏的烟花声,还有烟花绽放在空中印在脸上的光,那晚,是个不眠夜。
正月初八,全国开始正式上班,但我还没进隔离舱。
原因,还有一些东西没备齐,进隔离舱的东西。
护士长将一张清单给了爸妈,上面列的是进舱要带的东西。
棉质睡衣四套,棉质袜子四双,内—裤四条,拖鞋一双,帽子两个,口罩两个,毛巾三条,浴巾一条,不锈钢杯子两个,不锈钢脸盆四个,烧热水机一个……
还有好多,我不记得了。不过,在这之前,我从不知道,进隔离舱竟然要带这么多东西,这感觉,有点像进监狱。
但爸爸妈妈用了个仿若更恰当的词,嫁妆!
“梦梦,这是给你提前准备了嫁妆了。”妈妈提着在超市里扫荡了一下午的东西回到家,对我说道。
我:“……”
笑着说:“那以后再嫁人,是不是就不用买了?”
“大姑娘家的,就说嫁人的事羞不羞。”爸爸适时插话道。
爸爸骨子里是很传统的人,在他面前,我尽量保持乖乖女的形象,所以没再接茬了。
清单的最后一行,是将所有衣物绣上自己的名字,以便区分。
这一点,毋庸置疑,真的特别像进监狱的犯人。
所幸当时我正绣着高中班主任送我的十字绣,《唐顿庄园》的大大小小的树已经被我绣的七七八八了,我的针线活也有了进步。
妈妈便将这事交给了我。
“君小梦。”从没有在衣服绣过自己的名字,绣上去第一件衣服衣角处的字,就是歪歪扭扭的,不过还能看。
有了经验后,我绣第二件衣服的时候,想了个好办法,先用铅笔在衣角处写上自己的名字,然后按着铅笔线绣。
果然,工整的三个字出来了,很好看。
我有些骄傲,剩下的衣服的衣角,胸前,裤管,都有自己的名字。
然!
当我拿到内—裤和袜子的时候,有点哭笑不得,“为什么买红色的啊?”我问妈妈。
还是那种大红色的,丑,丑毙了!
“它上面不是说要买红色的吗?”妈妈问道。
“哪里有?”医院连买什么颜色都要规定啊!我又看了一遍清单,最下面那行字“用红线绣上自己的名字”顿时让我凌乱了。
“它上面是说用红线绣名字,不是让你买红色的衣服。”我指着清单上的字给妈妈看。
“还真是。”妈妈给了我个憨笑。
爸爸在另一间房捣鼓其他东西,听到谈话后,跑过来,“唉,红色就红色嘛,嫁妆就是要带点红,红色也挺好看的。”
我:“……”
谁说的提嫁妆羞人的。
在为移植忙碌着……
进隔离舱的那天,我恐怕这辈子都忘不掉了,如同生命般的经历,一生仅此一次。
隔离舱也称无菌仓,专门是移植的病人住的,舱内的一切都是无菌,拿进里面的东西全部要消毒,包括人。
当然,病人是泡消毒水的,然后用被单裹着,坐上轮椅,有专门的护士推进你的无菌病房。头发细菌多,一点不能留,就算是一点点都不行。
所以,在进医院前,我就找了家理发店,又剃了个光头。
一系列繁复的程序过后,我来到了那个只听过没见过的无菌病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