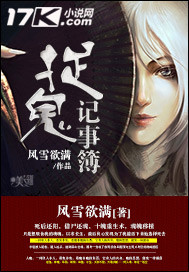魏知行见齐召面有嗔责之色,忙叩头道:“陛下乃圣明之君主,岂为朝令夕改之人?是臣下没有看清陛下的体恤之意,罪该万死。恳请陛下下旨降罪,撤了微臣大司农之职,专以盐铁丞之职,督监沧澜山太湖盐铁之事。”
说完,魏知行一跪到地,虔诚叩首,与原来冷然清寂的态度迥然不同。
齐召不由一怔,沉默了片刻方叫魏知行平身,嘴角现了几分笑意,眼珠却是一转,故作恼怒道:“魏知行!!你当朕好欺瞒吗?那殷氏私下称你为‘义父’,所知者众。即是义父义女关系,成婚便是有背纲常的**!求朕赐婚,岂不是陷朕于混浊之举、叫天下人齿寒!!!”
魏知行脸色登时慌了,连连叩首道:“陛下明查,微臣与殷氏女之间,绝无义父义女关系,陛下不信,可查官籍卷宗。”
齐召却不以为然道:“义父女关系,非官籍所能证也,不入官府备籍者大有人在。此事不提也罢、此婚不赐也罢!!!殷氏即被封了县主,再又有了魏氏义女身份,朕自会上心,与皇后商议,摘与之匹配之人嫁之,庆功宴那日,朕瞧着耿尚书的嫡孙耿肖、陈院使的庶子陈良都不错,配魏家义女,绝无委屈之理。”
魏知行的脸色登时 黑一阵、白一阵、紫一阵,五彩纷呈,好不热闹。
耿尚书是兵部尚书,三品官员,草莽出身,一身武艺,能动手时绝不动嘴,传言他的十方妾室中,有七方都是被他暴怒时一掌拍死的,其他两个,是犯了错误被大刀砍死的。所以,耿尚书至今只存活了一妻一妾。
耿尚书的嫡孙耿肖,是耿尚书第三个儿子,庆功宴那日据说表演的是大刀操练,那大刀光净重就有三十二斤六两,耿肖耍起来,就如同小娃子手里的柳树条一样轻松,吓得众小姐花容失色。
明月若是落到这样的莽夫手里,估计小命早晚要玩完。
再说那陈院使,是从三品督查院院使,文官,满口的仁义礼智信,二十多年来,以文作伐,弹劾掉了几十个官员,其中有一半受他唇齿相讥后上吊而死。
而他的庶子陈良,最具陈院使之风范,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架势。可见,陈良这张嘴,比耿肖的大刀 ,有过之而无不及。
明月这个不守礼法的性子,只怕不是被陈良说死,就是将陈良砍死,结局十分之不乐观。
魏知行硬着头皮道:“陛下,微臣岂敢欺瞒陛下?臣与殷氏确无父女关系,此事,李少将军也是知晓的,应该能为臣予以证明。”
“哦?”齐召颇有兴味的看着一脸窘迫的魏知行,觉得这样的表情出现在一个不苟言笑之人身上,是颇有兴味的一件事,遂对身后的太监道:“去唤了李少将军 来。”
因刚刚立了军功,又得了赏银,李放并未着急回北疆,反而如同被放回林中的鸟儿一般,白日与朋友打猎驯鹰,夜晚笙歌漫舞,以弥补他后宅清空的寂寥,日子过得好不惬意。
日头落下之时,太监才从一处勾栏院里将李放寻到,满嘴的酒气也顾不得,争匆匆进了皇宫面圣。
齐召今日心情显然不错,并未嗔怪李放吃了酒面圣,而是直接询问魏知行与殷明月是否有义父女关系。
李放嘻笑着点指着魏知行, 先是点了点头,又是摇了摇头,在魏知行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才兴灾乐祸道:“回禀告万岁爷,末将确实听过殷氏女唤魏司农为‘义父’,魏司农也从未否认过。”
魏知行的脸色登时变成了猪肝色,本以为庆功宴上李放相护明月,成功取得县主之位,定会站在他一方,没想到此时反将了一军,看来,自己还得另寻捷径,解决自己与明月那一段尴尬的关系。
魏知行脑中正飞快的转动着如何打破自己与明月的关系之时,李放已经嘲讽的一笑,从怀中掏出一本书来,颇有兴味的递与皇帝身的太监道:“骆公公,请将此书册呈与陛下,自见分晓。”
看着李放递与骆平的书册,魏知行头脑轰的一声响,可谓是喜忧参半,福祸所倚。此物,非是他物,正是留着骆平、明月、魏知行、李放四人题字的《白虎通》。
若是皇帝只以为李放与魏知行之间的打趣,不再深究另二人的笔迹,此事,便皆大欢喜,“魏知行”便是李放调侃赐名的“魏一夫”,魏知行与明月之间,自不是义父、义女关系,而是亲昵唤作“一夫”的情人关系;
若是皇帝好奇,让人彻查另两人笔迹,骆平倒还好说,若是牵出明月画的画册来,只怕皇帝会认为明月是一个浪-荡之女子,恐怕不仅亲事犯了波折,明月小命只怕不保。
皇帝果然颇为兴味的看着《白虎通》,一向缠绵女子榻上的中年天子,不由得看得面色潮红, 又气又恼道:“你们二人,真是叫朕如何分说是好。一个是自命 风流、游戏花丛的少年将军,一个是自命不凡、清心寡欲的三品司农,竟、竟偷看如此粗鄙之物?还在上面留有墨宝!简直、简直.......”
齐召已经找不出合适的词来形容这二位了,半天也没说出合适的指责话,更没有说出如何处罚。
李放与魏知行面面相觑,心领神会,知道齐召,并不是真的生气,否则早就叫人将二人拘到午门外打板子示众了。
果然,不一会儿,齐召便敛了气恼之色,静默道:“也罢,如此证明,魏爱卿不是他人所听到的‘义父’,而是李爱卿所赠之字‘一夫’,此‘一夫’非彼‘义父’,是众人以讹传讹。即然如此,朕便全了魏爱卿的拳拳之心,降三品大司农为四品盐铁丞,专职督监沧澜山盐铁之事。但需将三年祈福事毕方得完婚。”
魏知行这才舒了一口气,微不可查的向齐召身后的骆平点了点头,暂时放下心中的忐忑,三叩九拜而去,李放略有醉意,更是没有留下来出丑的必要。
齐召怔怔看着魏知行下殿的背影,入了里间,轻趴在贵妃榻上,对骆平招了招手,骆平会意,跪下身子,给齐召松骨按摩起来。
按得舒服之处,齐召喃喃道:“骆平,你知道朕为何讨厌魏知行吗?”
太监脸色一素,随即似无知无觉的继续捶腿道:“奴才不知。”
齐召轻敛了眼睑,似自言自语道:“魏知行的父亲魏大学士,为救父皇,以肉相啖,尸首不全。 若是魏家如泯王般挟恩求报,朕便会释然。偏他姐弟二人,一幅无欲无求的模样,皇后没有皇后的威严,震慑不住妃嫔,屡让魔妃当道,残害朕的宠妃子嗣;大司农又没有大司农的自觉,为了刘氏嫡女,长年游历各地。这几个月来,为了殷氏女,他三番两次哀求于朕,今日又见他偷看禁书,多了诸多烟火之气,朕反而不那么讨厌他了。”
骆平的手不由一顿,齐召的眉头轻皱,骆平忙放柔了手劲儿继续捶腿,赦然道:“万岁爷英明,即全了魏大人求娶殷氏女的心思,又全了皇家赐婚与他的尊威.......”
齐召轻轻叹了口气道:“沧澜山今非昔比,盐矿与铁矿尽聚于此,寻常人,朕不放心,也压不住那些魑魅魍魉;魏知行,一是揣摩透了朕的心思,二是想离北疆近些,与朝阳县县主殷氏女在乐阳郡双宿双飞。”
骆平知皇帝陛下不过是自说自话,并未要求自己回答,便让皇帝翻 了个身,帮着皇帝的脖颈儿舒缓疲累。
齐召舒服的轻吟一声,满意道:“骆平,你这一手松骨的功夫,倒是与你叔父在伯仲之间,以后,便在内务府做副总管吧。”
骆平忙不迭的跪倒谢恩,脸色却淡然的如这冬阳,昏黄却不见暖色,心中则寂然,他,经过“一桶江山”之庆功宴,和一手叔父所授的松骨本事,让他终于变成了和叔父一样的宦官。
一个人前被恭维、背后被骂阉狗的大内副总管,与叔父的大总管,不过是一步之遥。
权势在手,富贵在怀,只是,他却十分怀念,那个吃他亲手做的公鱼与鸬鹚鸟的少女,不知道,他与她的“殷厝”里的公鱼与鸬鹚,是否长势正好?
将明月送到魏知行手里,骆平纵心有不甘,却也是最放心的所在。
齐召虽惯用平衡之术、读心之术,偶尔也会一叶障目,自做聪明,窥不得玄机,就如同他眼中的魏氏姐弟。
在皇帝眼中,只以为魏氏姐弟淡然无欲, 却看不见这波涛汹涌下的漩涡袭卷。
就如同这后宫女子,哪个是无欲无求的,哪个是心慈手软的?看到的,不过是想让你看到的“真相”而矣。
在这偌大的后宫里,这些年来各种原因死去的妃子和子嗣,谁又能说得清,哪一桩哪一件,与皇后固宠、太子保嫡无关?
魏知行的游历山水,不挟恩要功,这些年暗下伏手绊倒的敌手无数,谁又说得清,哪一桩,哪一件,是与他狐凭鼠伏、保全魏家无关?
骆平甚至在午夜梦回之时想过,只怕,自己亦在不知不觉中,也成了被魏知行运于股掌之上的棋子之一。
只是,在那个危机时刻,即使自己知道了魏知行的计谋,只怕也会义无反顾的去救她,唯愿她,一切安好.
魏知行此举主动降职,求得实权,为皇帝效力,不是真正的愚者,就是真正的智者。
愚者,被皇帝以明月为饵,永远牵制制肘;
智者,被魏知行运筹于皇权外,保一世富贵安康。
而愚者与智者,不过只一线之隔,谁又说得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