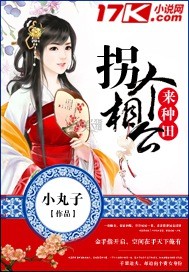李放大踏步向门外走去,爽朗的笑声震彻了相府,只是刘相爷夫妇已经无瑕顾及于此。
李放一语点醒梦中人,魏知行为情一怒,九年前闯了大殿,顶撞了陛下;九年后又在大殿上同时回绝了殷明月和刘家的求嫁,亦顶撞了陛下。
情景如此的相似,只是结果刚刚相反,如李放所说,一个如此重情重意之人,怎会拒绝了怀有自己子嗣的心爱女人呢?
相爷眼色一陈,对管家道:“将枫童找来。”
枫童是刘嘉怡自朝阳县二次回来之后,照顾刘嘉怡起居的家生子。
枫童很快来到厅前,跪倒请安。
刘夫人脸色阴沉道:“枫童,你应该知道谁是你真正的主子,你的爷娘掌握在谁的手中,问你话要俱实回答,若有半点诓言,你知道手段。”
枫童身子一颤,连声答“诺”。
刘夫人问道:“你家小姐今日赴宴可拿了麝香?”
枫童脸色一凛,犹豫过后还是点头称是,答道:“小姐说魏司农身上常年是竹花的味道,竹花的寓意不好,花期一过,竹子必亡,便送了最新送来的麝香。”
刘夫人气得一摔茶碗,怒道:“小贱婢,你不知道小姐怀有身孕吗?若是滑了胎,你九条命也还不起!!!来人!!来人!!!将这贱婢杖毙了!!!”
枫童忙跪在地上求饶,没想到自己只说了一句话便要小命呜呼,忙在声求饶道:“夫人饶命!奴婢是用盒子装得严严实实的,而且、而且,小姐早就在上个月便滑胎了!!!”
刘夫人大惊失色,遣退了下人,这才让枫童说出事情的来笼去脉。
原来,自三个月前魏炎给开了安胎药,刘嘉怡几乎躺着没有下榻,连用膳都是在榻上用的。
如此这般,直到一个多月前,刘嘉怡突然精神恍惚,时不时发呆,枫童吓得不敢离开小姐半步,生怕小姐精神不济,影响了胎儿。
枫童正担心之时,刘小姐却意外的开始下榻行走,饮食起居均恢复如常,枫童只以为小姐精神和身子均大好了。
没想到的是,一日枫童起夜上茅房,发现小姐鬼鬼祟祟的从房中出来,在树下埋着什么东西。
枫童好奇心胜,将小姐埋下的东西挖了出来,挖出来的,竟是几条用过的葵水带。
枫童吓了一跳,心里便笃定,小姐发呆的那几日,便是已经滑胎了,只是一直隐瞒不说。
刘夫人惊得一瘫,显些栽倒在地,原来,女儿早就滑了胎,竟然瞒着府中的所有人。
刘相爷恨铁不成钢的拍打了下桌案,气恼道:“这个孽障,好好的胎保不住不说,还要出去给刘家惹祸,这个女儿,怕是留不得了。”
刘夫人眼睛一红道:“老爷,千错万错,她也是咱们的嫡亲女儿啊,幸亏喝茶的是李少将军,男子喝了应该无甚大碍,即使影响的子嗣,李少将军后宅里的妾生子得有七八个了,到时候过继给正室一个便可,还有,若是、若是李少将军有意,将怡儿许给他也中,怡儿的长相在京城也是上数的......”
刘相爷无奈的窝在太师椅中,人一下子老了十几岁,哀怨道:“夫人好糊涂啊!老夫一生,弟子门生三千,所从者众,到头来,三个儿子文不成武不就,一个嫡女屡次陷老夫于险地,先是受制泯王,后受制大司农。夫人以为李放前来,是冲着怡儿来的?他是冲着老夫来的,冲着老夫的相位来的。只要怡儿在世一日,他便要胁老夫一日,永远受制于镇国侯府。枉老夫苦心钻营一生,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啊......”
刘相爷一脸疲色,哪里还有位高权重的左相模样。
刘夫人一脸哀色,原本刘相爷对这女儿就诸多失望,如今又没有保命的魏家子嗣,莫不是真要“病死”府中吗?
刘夫人咬紧了牙关,轻声道:“老爷,怡儿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她也许做的是对的,滑胎之事,你知,我知,怡儿知,无第四人知晓,魏知行也定不知晓,左右也是暂时不娶怡儿,待临盆之日,找个替代的,到那时再......”
刘相爷眼前一亮,先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叹道:“魏知行在朝堂之上,话里有话;李放方才离开之际,亦是话中有话。有些话,老夫不方便问怡儿。你是当娘的,去问了怡儿的准信儿,娃子的爹,到底是不是魏知行?”
刘夫人眼睛圆瞪,怒道:“这事还能有假了?问了怡儿不是戳怡儿的伤吗?她这半年来,都是追着那姓魏的身影跑,哪里还有别的男人?”
刘相爷亦是一甩袖子怒道:“别忘了,你女儿和离后,可是被泯王掳到朝阳县的!”
刘夫人登时 一怔,半天才自言自语道:“那老家伙六十多岁,朽木一个,应该结不出什么果子来......”
突然感觉身侧空气一冷 ,刘夫人抬眼看见刘相爷正一脸冷色的看着自己,蓦然想起,自己的相公与泯王年纪相仿,岂不是也成了她口中所说的“结不出果子的朽木”?
刘夫人忙噤了声,回头命管家,将枫童拉了下去,枫童脸色惨白,终于明白夫人所说的“没有第四个人知道这个秘密”是何用意,自己,根本就是不应该 知道这个秘密的第四个人。
处置了枫童, 刘夫人紧接着去了刘嘉怡房中,问了女儿一些难以启齿的问题。
刘嘉怡先是脸色惨白,随即脸色羞红,将那夜的柔情蜜意、巫山云雨,事无巨细的说给了娘亲听。
刘夫人这才放下心来,只要是魏知行的种,一切都不是问题,只要孩子顺利“生”下来,依刘伯农左相的地位,魏知行想要不认帐都是不成的,只是,未婚先产,女儿的声名只怕又要一落千丈了,和女儿的命比起来,这些似乎不那么重要了。
......
魏炎和“大桌子”身子软软的瘫在椅子里,一脸惊色的看着面前的明月,万万没想到,以“叙旧”为名的明月,原来的主子明月,堪比亲人的明月,竟然在茶里下了药,饶是魏炎诡计多端,也是毫无防范,完全着了道。
魏炎紧张的吞着唾沫,胸口燥热的如同万马奔腾,汗水如岩浆一般,涌出了一层又一层,层层不断。
明月则是气定神闲的啜着茶,眼皮轻撩,颇为慵懒道:“说吧,魏知行,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半天无人回答,魏炎和“大桌子”,完全一幅视死如归的表情。
明月撇了撇嘴,不屑的看着“大桌子”道:“临回京城前,你不是对你娘说,是我害得魏知行身中剧毒,还逍遥自在的生活,分明是个忘恩负义的女子吗?到了我面前不敢说了?还是认怂了?”
“大桌子”眼睛一瞪道:“我有什么认怂的!!你就是忘恩负义、薄情寡义、给我和魏郎下药.......”
魏炎努力的咳了两声,伸手虚弱的去扯“大桌子”的袖子,“大桌子”眼睛翻了翻,虽然仍旧不忿,却还是将话硬生生咽回了肚子里,不再言语了。
明月嘴角翘了翘,不以为然道:“‘大桌子’,你错了,我这个人,一点儿也不忘恩负义,我可懂得感恩了!在我受伤的时候,都是魏炎给我拿的药,我得好好‘感谢感谢’他。”
明月拍了两下手掌,江暮一脸兴味的自屋外走了进来,调皮的向明月眨了眨眼道:“放心好了,都是小吏家的嫡女,长得环肥燕瘦,各有千秋;性格温婉娴淑,含羞带怯,怕魏侍卫放不开,我还特地请了十里香的花魁调教过,啧啧啧,魏侍卫果然艳福不浅,江某都舍不得便宜他了.......”
魏炎一脸骇色,紧张的看向“大桌子”秋海棠,秋海棠的脸色已经由白转成黑碳色了,怒道:“殷明月,你、你什么意思 ?”
明月掩着口呵呵笑着,一脸“真诚”道:“‘大桌子’,这你还看不出来?!我在‘报恩’啊!魏来都有儿子了,魏炎却身下无子,自然得开枝散叶,一个暖榻的哪够,一起五个才对得起魏侍卫的-----‘恩情’。”
明月的脸子一落,冷然对江暮道:“江大人,还不动手?!”
江暮历来就是个不怕事大的主儿,张牙舞爪的上前,一把撕扯开魏炎的衣裳,露出里面大半儿的胸-脯,江暮还得逞的在上面揩了一把油,嘻笑道:“魏侍卫的身子骨不错,定能‘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就是力有不怠也莫要担心,江某在房中备了大力丸、不倒翁、九转丹,定让魏侍卫娇羞而来、尽兴而归。有道 是春宵一刻值千金,先上榻后补轿子、先进被窝后给名份,划算得紧......”
江暮眉飞色舞的看了眼“大桌子”,不明其意的摇了摇头,随即将衣裳狼狈的魏炎拖进了房中层层的纱帘之中,随即传来了数声女子的尖叫声与嘻闹声。
秋海棠目光如裂,气急败坏道:“殷明月,你放开魏郎,骂你的是我!气你的是我!你若恨,冲着我来!别为难魏郎!!!”
明月惊得掩了口,无辜道:“‘大桌子’,你莫不是动了纳男宠的心思?这个怪我,今天没有准备男子,明个儿、明个儿我定会准备五个,不,十个......今天只能看着你的魏郎接受我的‘恩情’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