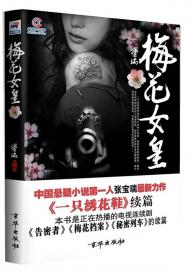袁大郎好言相劝袁氏自己服了解药,哪怕是为了孩子小雨和石头也好,袁氏心底终于升腾起了一丝希望,若数九寒天里的一盏烛火,恰黑色暗夜的一线微光,终于,在她绝望 的最后关头,袁大郎选择了正室妻子的她,拯救她于生命的最后边缘,放弃了救袁四娘的机会。
袁氏的身子虽然因吃了绞肠散的毒药而越发的沉重,心情却越发的欢喜,撑着身子回了伙房,从房梁处取下一只篮子,篮子里有一块红色帕子,打将开来,里面包着唯一的一只黑色的蜜丸儿解药。
袁氏拿起蜜丸,张开嘴巴,只要她愿意,解药随时送入口中,在蜜丸已经碰了嘴唇之即,袁氏却迟疑了,药与嘴之间的点滴距离,竟似比天涯还要久远。
解药久久没有被送入口中,重新放回了袁氏的手掌心儿,静谧的回到了房中。
此时的房中,只见袁大郎已经从怀中拿出一只红色的帕子来,打开帕子,里面现出一块碾得粉碎的桂花糕,袁大郎小心翼翼的拈起一小块儿,递到了袁四娘唇边,袁四娘含笑用嘴接过,小小的舌头,调皮的剐蹭了袁大郎的手指一下,害得袁大郎羞红了脸,连手指甲都臊红了,他却坚持着没的收回来。
桂花糕虽然让人唇齿留香,回甘好食,却是有些干,袁大郎尽快倒了一小碗的酒,递到四娘唇边,看着她豪迈的一饮而尽。
袁四娘的眼中难得的展现了一丝温柔,轻柔道:“大哥,你竟找到那桂花酒了?你掺了别的酒吗?怎么味道和纯桂花酒不大一样?!还有,这桂花糕是我最爱吃的,上次因为被抓而没吃到,你不要告诉我,这碎糕渣子还是上回的那些.......”
袁大郎眼睛腥红,隐去伤感,如轻风徐来,展颜笑道:“你藏的东西,我就是不吃不喝也会找到的,你说过埋在了桂花树下,便是桂花树下,即使桂花树被砍了,酒也会在那里的。”
袁四娘的眼泪再也忍不住,扑籁籁的落了下来,从小到大的种种场景,全部浮现在脑海里,她的大哥,原来,一直都在她的身后,只是她自己一直不得而知,总是苛求太多的不可能,害自己到了今天这步田地,也害了大哥为她担惊受怕,担心吊胆。
袁四娘轻叹了一口气道:“大哥,我、我.......其实先前我没有中毒,只是、只是想知道四娘在大哥心目 中有多重,饭前便将院中挖来掺猪食里的猪毛菜给吃了,这东西吃多了身子虚、肚子痛、流汗多,看着像中毒,你、你不会怪我骗了你吧......”
原来,竟是如此,果然如袁氏所说,她根本就没有下过什么毒药,不过是袁四娘试探袁大郎对她感情的诡计。
只是试探的结果让人始料不及,袁大郎不再避讳与袁四娘的畸型之恋,袁氏不再掩拭对袁四娘的厌恶之情,甚至不惜下了真毒药。
这毒药是寻常农家家中备用的,防止长蛇进屋的“绞肠纱”,药如其名,相当的霸道,蛇吃过之后亦会翻江倒海的疼痛半个时辰方死,可谓受尽了折磨。
袁大郎无所谓的摇了摇头,将袁四娘剩下的半块桂花糕就着黄酒自己吃了下去,柔声道:“从小到大,我何时嗔怪过你?哪怕是你惹了天大的祸事,大哥这条命都是舍得的,反而是你,被大哥所累了,大哥怕石头误食了‘绞肠散’,在家中只备了一份解药,你不会怪大哥让袁氏吃,而不救你吧?”
袁氏将身子往袁大郎怀里缩了缩,自打吃了桂花糕,喝了桂花酒后,腹部的疼痛迅速的得到了缓解,四肢百骸竟无比的便服,只是头脑有些昏昏沉沉,似要睡过去一般。
袁四娘强打着精神,嘴角噙着笑道:“大哥总不会抛下我的,我知道,从小时候起四娘就知道,只要在大哥面前,我才能真正的任性,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次也定会依我,对不对?”
袁大郎嘴角亦噙着笑,似宠溺的依偎在袁四娘身边,眼色蕴着无限深情道:“我的四娘,怎么可能有错?千错万错都是大哥的错,大哥不忍你逃亡受苦,不忍你四处奔波,更不忍你孤苦伶仃,远赴黄泉,大哥,永远都在.......”
袁四娘的呼吸已经渐趋渐无,脸上却仍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袁大郎眼睛掠过一抹哀色,模糊的对着袁氏笑道:“对不起,又要让你当寡妇了.......”
袁氏眼泪扑簌籁的止不住往下落,满面哀色道:“你,你这又是何苦?你若是舍不得她,我将解药给她了便是!何必如此折磨于我,我下半辈子背着两条人命该怎么活?”
袁大郎拉住了儿子石头的手,放在了袁氏手心里,看了一眼刚刚掐了袁氏的脖颈儿而显现的紫痕,不无愧疚道:“刚刚实在对不住,我不是怪你下了药,我只是怪你用了‘绞肠散’,让四娘多遭这份罪。原本,原本,我打算三天后再离开的.......”
袁氏的心,渐渐的沉了下去,现在的她才知道,在他心中,从来没有对妻子、对儿子的挂牵,只有他的四娘。
三天后,是袁四娘问斩的日子,原来,他早就打算抛妻弃子,随袁四娘而去,自己的意外下毒,只是提前成全了他们的双宿双飞。
渐渐的,袁大郎的眼睛亦模糊了,脑海中如海市蜃楼般闪现着过去的种种,有浪漫时的四娘,有娇嗔时的四娘,有嫣然时的四娘,唯独没有,狠毒时的四娘。
原来,那郎中没有骗人,果然有一种毒药,让人安乐的死去; 那酒保亦没有骗人,果然有一种纯酿,让人一枕黄梁不复醒。
袁氏拼命的摇着袁大郎的尸首,一声歇斯底里的怒吼若滚滚月亮河水呼啸而出:“袁大郎,你何其残忍.......
只是,声音寂寥,没有任何人回应于她。
袁氏毅然将自己的解药送入口中,站起身来,挺拔而坚定的身影,让她不再如过去的痴情怨女般的怨天尤人,看着紧缩墙角的成高儿,眼色亦是浓如深潭,看不分明。
成高儿不由得打了一个冷颤,在第一次被绑驾时,那袁四娘的眼色便是如此,有种破釜沉舟人的魄力,却也有种夺人心魄的恐惧。
成高儿连连后退,心如擂鼓,默默的祈祷着,自己的“放屁”神功能发挥奇效.......
似乎是回应成高儿的祈祷般,远处响起了几声狗吠,渐行渐近,若下饺子般的吠声此起彼伏,随之映入眼睑的,是两条大黄狗,和她们所生的八条欢脱的小黄狗,大黄狗斜眯着眼盯着袁氏,生怕她伤了小主子; 小黄狗则毫不迟疑的扑向了成高儿,热情的无以伦比,只是这方位太过不敢苟同,不约而同的嗅向同一部位 .......
.......
莽莽的月亮河水滚滚流淌,如同三房院内的热火朝天。
霍知州亲自坐阵,将三房院中和老宅院中挖得千疮百孔,仍不见起色,愁得霍知州嘴上的泡里三层外三层,感觉怀里的十万两银票如同火一般的炙烤着自己,看向成鸿略的眼色也不甚友好了。
成鸿略自然接收到了霍知州眼里的嗔怪,甚至能想象的到霍知州的所思所想,这时的他,估计十有八九在大脑中偷偷盘算着,为这十两银子冒这样的风险成本有多高,必竟,那殷明月可是他的继女,且来了个人间蒸发得无影无踪。
找盐之事如此停滞不前,再不立新功怕是真要祸及了成家。成鸿略心中一突,想将霍知州的视线转移到殷金身上来,遂附耳至霍知州道:“大人应查之事是贩盐之事,何必究住殷明月和殷家老宅不放?为何不在那殷金身上找突破口?那殷金可是贩了盐的,盐的出处定然知道。”
霍知州委屈的摇了摇头,他何尝不想找,可是那殷金打得快断了气,也只说是什么神树显灵,浑身是盐之类的浑话。
成鸿略耐心的劝解道:“大人,将那殷金押在大牢也不是办法,不如押到此处,让殷金那斯触景生情,说不定心里一慌,我们便瞧出些端倪来。”
如今殷家老宅、殷家三房的青石屋、甚至旁边两处土坯房,都被找了无数地,地面也被挖得千疮百孔,这审问殷金之事,也只有死马当活马医了。
霍知州命人将殷金从县里大牢提了过来,这也是殷金失踪后,成鸿略第一次见到他,即使以前再仇恨殷金陷害刘氏,再不耻殷金之魑魅魍魉之行径,此时却说什么也恨不起来了。
只见殷金四脚被穿了重镣,之所以说“穿了重镣”而不是“套”或“扣”,是因为那镣铐从骨头中间穿过,真真正正的洞穿而过,两条锁链又在身下交叉而过,害得人的四肢,只能如狗般的四脚拖地而行,如同蛹动的软身虫,让人不忍直视。
与过去的阴险诡辩不同,此时的殷金,目光呆滞,衣着邋遢,毫无生气,霍知州不耐烦的怒叱一声:“殷金,你还不从实招来?!盐从哪里来的?”
声音一出,吓得殷金“扑通”一声跪倒,边磕头边恨得咬牙切齿边颤声道:“报应!神树报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