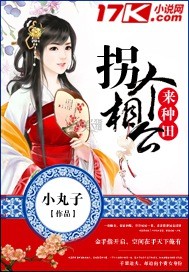赏花宴马上就要开始了,出乎意料的是,宴席并没有在凉爽舒适的花园里或是宽敞奢华的正殿举行,而是设在了正殿前的空荡荡的广场上,四周摆满了盆栽的花儿,有菊花、牡丹、芍药、茶花等,可谓是百花齐放、姹紫嫣红、芳香四溢。
虽然赏心悦目,但在如此秋老虎般的日照下,估计用不了一刻,这些人就有被晒成人干儿的风险。
宁公主是个爱美爱享乐的,自然不会让自己遭受这份罪。
在诸席上首,是一个宽大的华盖,下面摆着桌案,桌案后是舒适的红木雕椅,上面放着冰丝软枕和竹垫子,华盖两侧摆着冰筒,因冰遇热而腾腾的冒着寒气。
桌案上的摆着果盘,呈着葡萄、荔枝、苹果等各色水果,被洗得光净如新,上面还挂着晶莹的水珠,即使看着,也会让人打心里清凉不少。
与清凉的上首席位不同,下首的桌案按孔雀开屏式摆设,最前方为两席、四席、八席、十六席、三十二席、六十四席等等,每席可坐两至三人,桌案上同样摆放着水果盘,只是由于天气炎热的缘故,水果已经被晒得蔫头耷脑,连看客都没有了吃的心情。
桌案前更没有什么舒适的冰丝软枕和竹垫子,而是一张简单的布垫子,只起到清洁的作用,完全没有舒适与冰凉的效果。
与往常分品阶落座不同,没有婢子引领,没有标注男女席,应当又是宁公主的别出心裁,让众人随心所欲、不分品阶、不分男女混合而坐。
饶是如此,除了几个不开眼的想引起宁公主注意的小官吏,其余均是谨守礼仪,品阶高的自然排在前面。
魏知行官居三品大司农,品阶在一众男子中算是出类拔粹的,自然而然的坐在了左边最前席,洪丰已经有了心上人,无奈还未婚娶,又是大理寺少卿,不能不敷衍而来,很自然的坐在了好友魏知行身侧。
齐阳郡王与他的庶女嫡子们,则脸色淡然的坐在了右侧最前席。
两席之后的四席,分别是户部侍郎李大人、礼部侍郎邹大人、鸿胪寺少卿于大人等朝中四五品官吏,第四张席位却是耐人寻味,是两个生面孔,其中一个怯怯懦懦的不敢看向诸人,另一个则毫不忌讳的扫视着诸人,嘴角下弯弧度,一幅恃才放旷的模样,让人看着分外的不舒服。
众人心下轻叱,知道这二人定是新晋为官的“不懂规矩”、又急于上位的外地小吏。
女子们由于害羞,大多居于十席之后。
众人找到了各自的席位,纷纷落坐,刚一坐定,顿时一皱眉头。
这青石被秋老虎的日头烤着,如火一般的烫,众人一坐,如坐在火盆上一般。
魏知行、洪丰、李大人、邹大人等四品以上官阶大人,什么阵仗没见过?
伴君如伴虎。每日上朝,很可能前一刻云淡风轻,后一刻电闪雷鸣;前一刻嘉许封赏,后一刻抄家灭族。
此刻别说坐的是烤热的青石头,就是竖满钉子的钉板,这几位亦是照坐不误,连个眉头都不会皱一下。
相较而言,第二阵营的那个胆怯小吏就有些尴尬了,身体“腾”的一下站了起来,手不自觉的捂着屁股,后知后觉在前三个阵营之中,只自己一人突兀的站起来,忙又重新坐了下来,只是,屁股欠着、身体前倾,有种卑微匍匐的丑态。
宁公主扫了一眼众人的神态与行态,转回身来,亲昵的靠在安太妃身上,发现纱制的幕离太过碍眼,伸手一挑,便将幕离挥手扔开,幕离飘飘荡荡,恰好飘荡在了那个胆战心惊的小吏身上,吓得他本就没坐稳的身子登时一个前扑,险些栽倒在地,大粉色的幕离挂在他的头上,随风飘荡,他却一动不敢动,如木偶般定在那里,说不出的滑稽可笑。
惹得宁公主哈哈大笑道:“如此桎梏,除去也罢,今日在本公主府,一切都按民间的规矩来,就是----没有规矩,幕离都除去了吧......”
众女子却是一动未动,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她们皆不戴着幕离出门,但这是正式的皇家规制宴席,不犯错误都能治出罪来,何况不守规矩,留以话柄。
安太妃叹了一口气,宠腻的刮了刮宁公主的小鼻尖,无可奈何道:“你这个没规矩的小家伙,拿你真是没有办法。”
语气虽颇为嗔责,但手上己率先将自己的幕离除去,和蔼可亲的向诸位小姐一挥手道:“今日安公主是主,诸位是客,客随主便,尽皆除去吧,还有,那个你----”
安太妃指着一动不敢动的支着幕离的小吏道:“就是你,好好的坐着,莫一幅小家子气模样!今日来此的,皆是京城官家子嗣,你,是哪家府上的?哀家怎从未见过你?”
小吏忙叩首,结结巴巴半天也没说明白是谁家府上的。
旁边恃才放旷的男子站起身来,施礼答道:“回太妃娘娘,卑职姓常名远,乐阳郡人,仁武十年进士第五名,身侧这位仁兄同是乐阳郡人,姓郑名大仁,仁武十年进士第二十一名,刚刚谪派为官,郑兄被派任藏洲郡泰来县县丞;吾被派任藏洲郡安侯县县令,因听闻公主府上花草品种繁多,便有了一窥全貌的心思,此事是得公主准许的。”
宁公主恍然点头道:“太妃娘娘,宁儿确实特批了一些人士进来赏花,都是有些真才实学的,这个常公子,听闻在乐阳郡的斗诗会上,将风头正盛的江暮江大才子给打败了,江暮羞愧得再也没有露面。 还有那个,”
宁公主指着远处第八九席位上的神色紧张的几个少年道:“那个穿紫色绸衣的,身为男子,竟然会绣双面绣;那个穿蓝色绸衣的,画的冰雪图栩栩如生,竟如真的冰雪一般;还有那个......”
宁公主心情雀跃的指指这个,又指指那个,每指一个,便站起来施礼一个,一口气指出了二十多个,如同将军沙场点兵,又如皇帝选妃翻牌一般。
将一众自认出身高贵的公子小姐的脸色,说得青一阵、紫一阵,这哪里是赏花宴,分明是宁公主的选夫宴,而且还是大混选,社会上的商贾、寒门一应俱全,怎不让养尊处优的贵胄们懊恼?!
如此一来,女子们摘不摘幕离却是个问题了。
摘下幕离,势必让这些寒门学子甚至商贾们一睹真容,在贵胄小姐们看来,这是一种极为侮辱的行为;
不摘下幕离,又似乎有不拿太妃娘娘的话为重的嫌弃,虽然太妃娘娘是己故先皇的妃子,不得宠幸,未留子嗣,没有家族,但毕竟代养过皇帝和公主一段时间,在皇帝、皇后、公主心中还是有一定份量的。
如此一来,摘不摘幕离也形成了两个阵营,犹豫不决。
好在太妃娘娘与宁公主并不在意此事,宁公主已经雀跃得如同一个未曾出阁的少女,叽叽喳喳的对这些个特批入府的男子们品评个不停,说了半天,有些口干舌燥,拿起琉璃酒壶,对着嘴“咕咚咕咚”就喝了起来,有种侠女般的不拘小节。
常远因为在答着安太妃的话,一直躬身施礼,被宁公主如此一搅和,半天也动弹不得,后背又被太阳炙烤着,不一会儿就浸出了一层汗水,连衣裳都浸湿了。
半天,宁公主才后知后觉道:“太妃娘娘,让大家落坐吧,站着怪难受的。”
被点指站起来的少年们,这才如逢特赦般的坐下来,虽然坐下来如同被火烤着屁股,但站起来却如同被火烤着脸颊,两害相权取其轻,还是烤屁股比烤脸颊更为稳妥些,要知道,被这些贵胄们一起狠命的盯着,不死也要脱层皮。
后续的过程和皇家的宴席别无二致,不过是这府的小姐表演个舞蹈,那府的小姐弹个琴,看得宁公主呵欠连天,昏昏欲睡;
直到这府的公子表演个剑舞,那府的公子表演个梅花篆字,宁公主才提起了浓厚的兴致,鼓掌称快。
表演过半之时,座席上的看客,比表演之人流的汗水还要多,户部尚书家的小姐已经不胜其苦,直接栽倒在地晕了过去,下人们只好扶着去休息。
吏部侍郎家的嫡小姐,见此宴醉翁之意不在酒,自己显然成了陪称,害得妆容花了不说,头发被汗水湿成一绺绺的,纱制的裙子也熨贴在身上,继续留下来必定煞是狼狈,索性眼睛一翻白,如同户部尚书家的小姐一般“晕”了过去。
见少女们均有“身体瀛弱”之势,宁公主不由得摇摇头道:“李小姐与录小姐的身体如此孱弱,以后如何能替夫家传宗接代?明年的选秀也莫要参加了吧!”
只一句话,本来也有心思“晕倒”的小姐们,均不敢再“晕”过去了,就连刚刚“晕”过去的李小姐和录小姐,也强打着精神重新回到宴席上,即使不想参加选秀,被夫家知道身体弱也不是一件好事情。
而本想低调行事的贵家公子们,则如同热极了狗一般,呼呼吐着舌头,喘着粗气。
为了动上一动,本来不想上前表演的公子们,也都抢着上前表演了,毕竟,舞个剑还能被风吹上那么几下,写个书法还能净个手解解热......
如此这般,就连洪丰都上前去像模像样的写了篇歪歪扭扭的书法,净了净手,解了解热。
回来向魏知行使了使眼色,魏知行轻轻摇了摇头,仍旧一幅我自岿然不动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