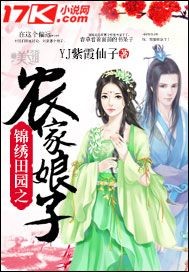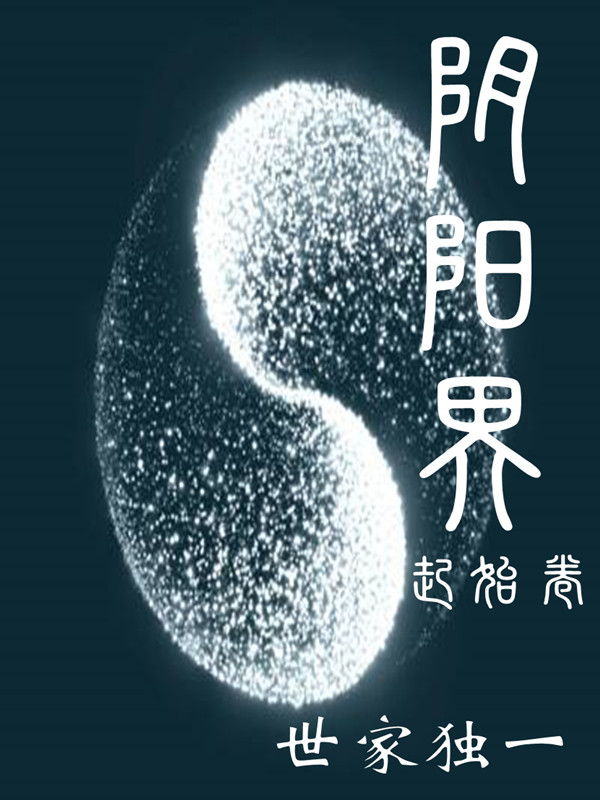一听说皇帝有除泯王之心,齐阳郡王神色不由的脸色紧张道:“父王,现在皇帝有动咱们的心思,不能坐以待毙,不如连夜逃回乐阳郡吧……”
泯王轻轻拍了拍儿子的肩头,多年为质在京城,让自己这个儿子养成了胆小怯懦的性格,抬头怕天落,风吹怕山倒。却又从小离家,做梦都想回到乐阳郡,远离囚禁他多年的京城,呼吸一下京城之外自由的空气。
泯王安慰性的将陨铁剑交到儿子手中,意气风发道:“君逼臣反,臣不得不反,只要师出有名。先皇的身份始终是个疑窦,本王已经从月亮公主身上找到一些线索,只要证明先皇不是皇家骨血,本王便可号天下诸侯反之,名正言顺登基做殿,你便是名正言顺的太子。”
齐阳郡王手掌颤抖着执着剑,做梦都没有想过那个高高在上的位置,如今被父王说的如此简单,仿佛感觉手里拿的不是一把普通的陨铁剑,而是整个家族的荣辱,整个天下的沉重,有种同仇敌忾,有荣与焉的使命。
多年京城为质、不受父王待见的怨怼,一忽间云开雾散,郡王的眼睛都赤红了。
猛吸了吸鼻子,有些疑虑道:“父王,月亮公主已经殁去几十年,先皇也驾崩数年,这证据早就随着他们一起入土了吧?”
时间可以掩盖一切,时间也可以留下被人遗忘的线索。
泯王嘴角闪现一抹微笑,所谓危机,有危险也有机会,端看你是不是有一将功成万骨枯的精神,也看你有没有壮士断腕的决绝,决绝,自己,从来都不缺。
泯王怜惜的摸了摸齐阳郡王的头,摸着三十多岁的男人,竟似摸着未到京城为质时三岁娃子的头。
齐阳郡王如被抚摸的猫儿,乖巧而尊敬的任由父亲摸着头,泯王眼中也难得现了一丝铁汗柔情,孺子情深,意味深长道:“齐儿,生在帝王家,有很多的责任与使命,你,也逃不脱。”
就如同,从墓冢中挖出的月亮公主,尸身不是处子,而是新产孕妇。死因不是天花,而是三尺白凌。真相的背后,往往是渗骨的冰冷。
齐阳郡王脸色一红,父王所说的责任,莫不是让我与他同仇敌忾,一同谋反?与其被困在京城,被贵家公子嘲笑,自己硬气一回又如何?
父王所说的使命,莫不是暗示我与他挥斥方遒,一统天下?自己将来就将这大齐,甚至大周,北俘……四海八荒尽皆臣服脚下……
齐阳郡王脸色红透了,如火烧云映红了半边天,烤的人心火热火热的。
看着难得不再懦弱的儿子,泯王心中叹了一口气,愧疚之情涌上心头,却是话到嘴边,如粳在吼。
生在帝王家,有滔天的富贵,也有血染的牺牲,这,都是责任与使命,自己的儿子如是,月亮公主亦如是。
当年月亮公主天之娇女,陪同太祖皇帝狩猎,回来便郁郁寡欢,足不出户,不到一年便天花而死。
从她死亡时间、死亡方式和非处子之身,泯王有一个大胆的猜想,就是,先皇不是太祖皇帝的儿子,而是太祖皇帝的亲外甥,是月亮公主与人私通所生,非纯正的皇家骨血,因太祖皇帝没有子嗣,又不愿将滔天的权势拱手让与本族侄子泯王,便有了偷天换日之计。
为家族,牺牲个人幸福只是其中一项,更多的,是见不得天日的荒凉,如从小为质的儿子齐阳郡王一脉,一妃五妾三子一女,十一主,三十余仆,欲登山之巅,必踩盆之渊,欲成大业,必抛却儿女情长。
泯王对齐阳郡王笑了笑道:“好孩儿,这几日父王带着你进宫走走,随后偷偷潜回乐阳郡调查皇帝血脉之事,你此后多带着贤儿、昭儿在人前应酬,多多进宫请安,迷惑皇帝与众大臣,拖延时日,为父派人接应你撤离。”
齐阳郡王点了点头,这是父王第一次要求自己做事,并许了尊贵地位,自己定要积极表现,为父王登基立下不世功勋。
父子二人,具是满面含笑,内心里,齐阳郡王,众志成城,泯王,忧心忡忡,未来,则是方兴未艾,要么万丈深渊,要么柳暗花明。
泯王不知道,未来的天下属不属于自己,只知道,他的儿子,怕是九死一生,为了他的建国大业,成了可悲的垫脚石,而他,明明知道这一切,却不能伸手去阻止它的发生。
让我的儿子为质吗?好,既然如此,就让我力挽狂澜,搅得这天下天翻地覆,让这天下,人人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国不成国,家不成家。
……
刘嘉怡带着一品居四大补汤,一脸喜色的直奔大司农府。
大司农府的位置完全符合魏知行的性格,虽然位于热闹非凡、贵胄云集的正德大街,但却位于最边角,独立门第,门可罗雀,府门上的廊檐下,甚至燕子衔泥,垒了一个鸟巢。
不知道底细的,还以为这是一座空荡荡的府邸。
与隔壁、隔壁的隔壁府邸的门庭若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仿佛它是误入牡丹丛中的雏菊,倔强而漠然的开放。
走进府中,与府门的简陋冷清相比,府内却是自有乾坤,园林景致鳞次栉比,池塘湖景宁静致远,依自然而生,又错落有致,尤其是占地数十亩的竹林,郁郁葱葱,生机盎然。
若是别人家的府邸是亭台楼阁中建着花园亭台,而大司农府邸则是自然景致中建着简陋的休憩之所,空旷的架构,让人心胸开阔,自由乾坤。
建筑的简陋,完全掩盖不了府邸的低调与奢华,入府最先映入眼帘的绿色猫头鹰雕花石壁,是丈长的翡翠原石,毫无瑕疵;地上四通八达的五彩石甬路,那五彩的石头,竟是各种玉石原石……
总之, 整个府邸,在行家看来,奢华的无以伦比,在外行看来,却又简陋的令人发指。
此时的魏知行就处于一片竹林之中,清风徐来,竹影横斜,竹香弥漫,好一处修心养性之所。
竹林间,桌案前,魏知行正目光如炬的盯着白色的宣纸,沉吟不语,过了好一会,才拿起紫金狼毫,挥墨泼墨,长长的发在风中轻舞飞扬,脸色恬淡无波,让人有种误入竹林深处,得遇天界阡陌上仙的错觉。
如此翩翩佳公子,身侧却有一个张牙舞爪,心急如焚的洪丰,生生破坏了画面的美感。
洪丰颇为不满的摇晃着手里的箭矢、短刃等物事道:“魏知行,这劲弩、短刃、铁蒺藜是锻造司上百名匠人,不分日夜,按你要求锻造而成,硬度,射程,攻击性都提高了一些,你还有何不满意的?江暮说的未必是真的,也许是在骗你银子。”
魏知行终于放下狼毫笔,指着图上的物事道:“这是他口述的行军铲,既能折叠,又能集砍、铲、挖、钜为一体,行军打仗最是实用方便,端是这份奇思妙想,就不是寻常之辈所能参透的。”
洪丰一副看傻子的表情看着魏知行,看了半天也没从魏知行脸上看出什么端倪来,不是他怀疑魏知行的眼光,而是这江暮,半月前还是一个欺世盗名的“才子文人”模样,突然一忽然间变成了下水可捞鱼、张嘴造武器的匠人模样,一开口就是十万两银子现银,如此狮子大开口,怎不让洪丰心生警觉?
见二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模样,洪丰更是气的七窍生烟,认为魏知行定是与殷明月一起呆的时间久了,脑子不灵光了,所以一同被江暮所骗。
“你是不是脑子笨成了榆木疙瘩?真给他十万两银子?愚笨女子上当也就罢了,你堂堂一个三品大司农,说出去会让整个大齐国笑话一辈子的,就说这铁锹,行军再方便,能抵上北俘虏十万战马吗?能抵上泯王的三十万兵将吗?”
魏知行向洪丰翻了一记白眼,神情笃定而淡然道:“针儿虽小,作用极大,不试试,怎么知道作用大小?这劲弩和短刃不是改良了许多?”
说及此,洪丰更加气愤,撅着嘴嗔责道:“江暮只出点子,还是半成熟半不成熟的,改良劲弩的速度,力度,大部分是老工匠摸索的,他就是骗财……”
见洪丰仍旧一脸怏怏不乐的神情,魏知行开解道:“一个点子,可能有的工匠一辈子都想不出来。这行军铲,铁蒺藜,看似不入眼,很可能会帮助挖通了敌军的营帐,绊倒了十万战马。若是如他所说,装备出一只铁浮屠,能刀枪不入,定能天下无敌,别说是泯王,就是北虏,也要乖乖俯首称臣。”
铁浮屠,如同其名,就是用铁器装备出一只上好的骑兵,从战士的铠甲,一直装备到马的牙齿,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相当于现在的猎豹特种兵,其防御性和攻击性堪称独一无二。
洪丰不由得冷静下来,自己不是愚笨的,只是被江暮屌二郎当的样子气着了,不想承认他而已。
魏知行拍了拍老友的肩头,调侃道:“况且,这江暮得了银子做什么?还不是继续杀太湖里的鱼和打捞太湖底的铁,最终受益的,还是我这个管盐和铁的大司农,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
男子清风徐来的面容,突然闪了一丝狡黠,让洪丰不得不承认,狡猾的江暮,擅长骗女子钱财的江暮,这次怕是真的被魏知行算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