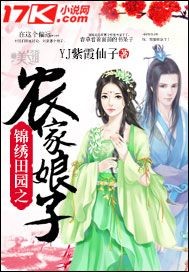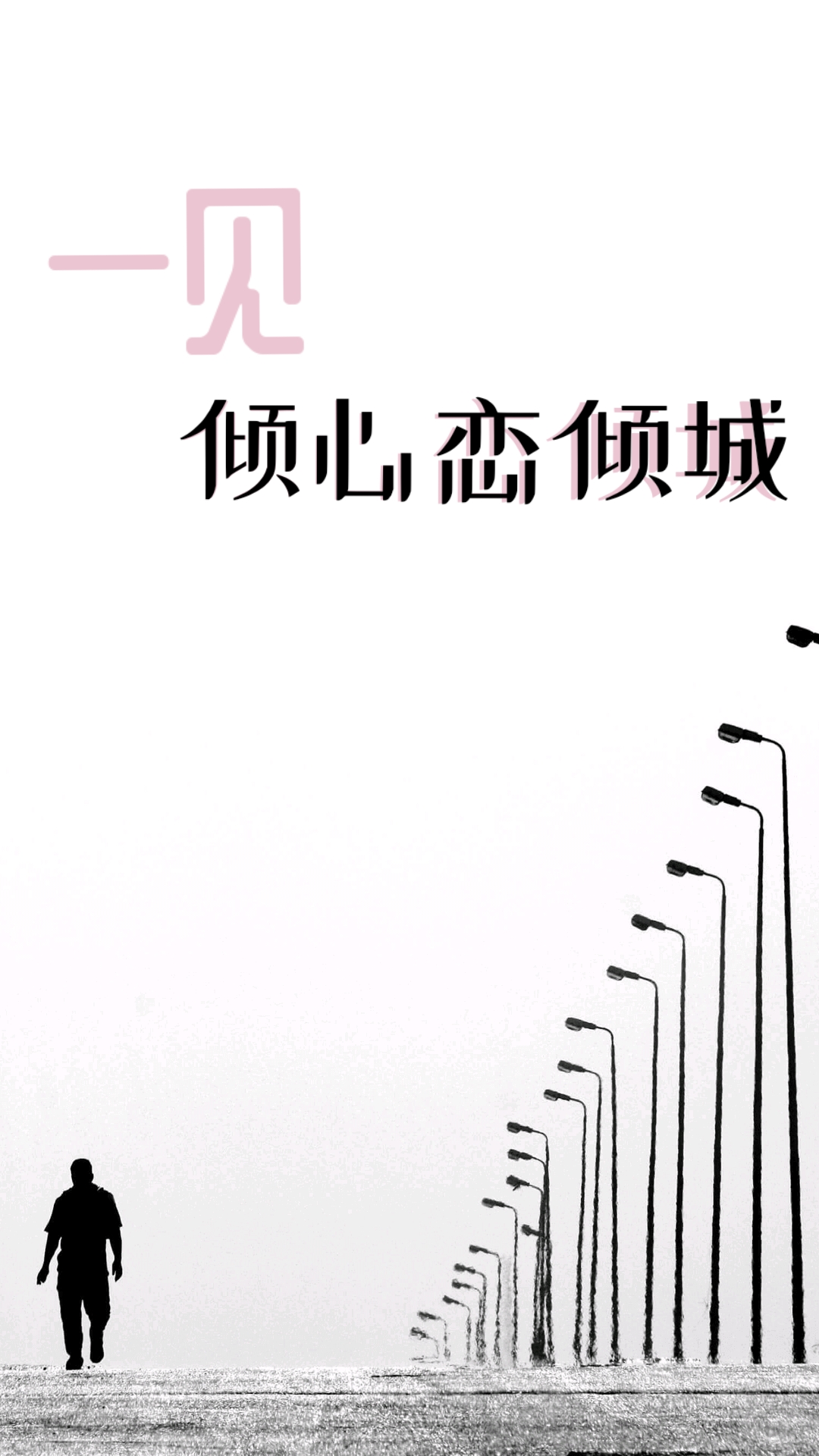成鸿略收拾着临时充当桌案的桌子,从上面捡起那件嫩粉色的亵衣,感受着上面的一抹丝滑,半红着脸递给成高儿道:“这个,给你干娘送去。”
成高儿飞快的跑到刘氏面前,亲昵的将亵衣塞到刘氏的怀中,脆生生道:“娘,这是爹让给你的。”
刘氏登时闹了个大红脸,忙将亵衣收起来,这毕竟是经了殷金手的东西,呃,貌似,刚刚成县令也用手拿了,还在上面揉了揉,简直羞死个人了,一会儿在没人处定要剪碎了它,将此事忘得一干二净才是。
亵衣事件在成鸿略的精心筹谋下,终于圆满的得以解决。
刘氏的脸红得如同大苹果一般,走到成鸿略与李成悦面前,施了施礼道:“多谢李捕头费心去搜寻物证,多谢成大人明查秋毫,还农妇一个清白。”单纯如刘氏, 到现在还以为事情的真相就是表面判定的如此,这殷金真的堕落到去偷全村妇人甚至八十老妪的亵衣。
得了小娘子的谢意,李成悦心里如渗了蜜般甜丝丝的,刚要答话,成鸿略已经抢下话来答道:“哪里哪里,月儿娘是高儿的干娘,自然不是外人;明月是你的闺女,自然也是我的闺女,当能让孩子受了委屈,千万莫要客气,以后,你家的事就是成某的事。”
竟然也不叫刘氐殷家娘子,改称月儿娘了,这几句话说的甚是热络,听得刘氏莫名的又红了脸,什么叫做月儿也是他闺女?什么叫做你家的事就是他的事?刘氏甩了甩如同浆糊的脑袋,心中自我安慰道:成县令定是看自己对高儿不错,又认了干亲,他也想着认明月当干闺女, 一定是这样,嗯,一定是这样。
成鸿略没有注意到刘氏的小变化,如沐春风的脸待转向成悦,立马变得如冬夜般寒凉,凛然道:“李捕头,你带着两个人将地上的血迹冲洗净了,切莫吓到月儿娘。以后别这么冲动,打人、骂人是莽夫所为,不仅于事无益,反而会逼得对手狗急跳墙,如果不是惹急了殷金,他也不会当着这么多村民的面儿拿出亵衣来,险些闹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以后要用脑子,知道不?”
李成悦两只眼睛顿时瞪成了牛眼睛,成鸿略只几句话,就将他入各户偷亵衣、到殷家埋亵衣、再找里正挖亵衣等等之功全都给抹煞了,还成了一个险些坏事的“莽夫”,虽然,他确实鲁莽了点儿,但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人家小娘子正感谢着呢,自己反而挨了训斥呢?功劳反而成了成大人一人的了,这,简直是明晃晃的太无耻......
一个衙役忙拉着脸色讪讪的李成悦离开,半天才拍了拍仍一脸懵懂的李成悦道:“头儿,你平时挺机灵的,咋这回就傻了呢?没看出来,县令看上那小寡妇了,眼睛都快长出钩子了......”
李成悦脑中一道闪电劈过,登时清晰了不少,所有过去想不通的事儿现在全都清晰了,原来,成大人也看上刘氏了......
这个认知让李成悦怔了半天,竟然无所适从,越想越是颓废。
论家世,成大人是耕读世家,识文断字;而自己从老子到儿子,全都是武枪弄棍的莽夫;
论财富,成大人为官多年,既然不搜刮民脂民膏,也比他这个捕快挣的多;
论权势,成大人只一句话,便再也没有官媒给自己说媒,连秋海棠的姑姑都不肯帮忙,自己却是束手无策;
论人品,成大人自发妻离世,一直洁身自好,从不与其他女子纠缠不清,而自己,除了死了的三房老婆,还是青楼的常客;
论关系,成大人儿子成高儿与刘氏情同母子,而自家的混蛋儿子连见都没见过刘氏,整日在镖局里打打杀杀......
半路杀出个成鸿略,李成悦越想越没有底气,卑微得快要钻到地缝里去了......
随着刘家的离去,殷金的被打,三房的日子渐渐趋于平静,成高儿更是如长在三房一般,日日如脱了缰了野马,与明阳与松儿整日混在一处,今日掏鸟,明日捉虾,一天一小吵,三天一大吵,吵完再和好,一个粉雕玉琢的小公子,早就变成了地道的农家小娃子,脸色黑黝黝的,身体壮实实的。
这一日,松儿满头是汗的跑进了屋子,拉着刘氏的手就往外走,刘氏急得忙扯住松儿,急道:“出了何事?明阳和高儿呢?现在河水开化了,莫不是掉河里了?快去救人啊!!”
松儿急忙摇摇头道:“娘,你别急,高儿和明阳就在山脚的地里呢,月儿姐也在那里晒豆子,没遇到野兽,更没掉到河里。”
刘氏长舒了一口气,刮了刮松儿冒汗的小鼻尖,嗔责道:“那你急个啥?吓死娘了,以为出啥大事了!现在是四月了,别动不动跑一身汗,小心着凉。”
松儿急得直跺脚,急道:“娘,你听我说完啊!咱家要出大事了!刚刚高儿又扯明阳的头发,我帮着明阳训斥他,高儿就生气了,说我和明阳才是一家人,将他当做外人。”
对于三个七岁小娃子的官司,刘氏己经思空见惯,完全不以为然,连成鸿略都不再为三个家伙“断案”了。若是每件事情都插手,这一大家子都不用忙活活计了,尤其是明月,忙着晒豆子酿什么叫酱油的东西,整日往山上跑,北疆的辣酱又要来取货,一大家人忙得脚打后脑勺儿,哪里有功夫给这三个小娃子断案。
见刘氏一幅敷衍的态度,松儿有些生气了,声音提高了不少道:“娘,成高儿正逼着明阳跟他成亲呢!说是成了亲,他们两个是相公与娘子,就是名符其实的一家人,反过来一起欺负我!!!我不依!!!”
“啥?成亲?”刘氏吓得一跳,忙向半山上跑去。
如今正是农历四月,春光正是明媚,溪水潺潺涓涓,林木郁郁葱葱,“撩汉”和“撩妹儿”撒了欢似的向山脚跑,狗一、狗二至狗八如黄色的球般在后面疯狂的追着,好一幅生机盎然的田园居图。
到了山脚下被青石圈住的地里,明阳和高儿正站于一处,明月一脸笑嘻嘻的站在身前,两个小家伙肃着脸,扑通的跪了下来,似模似样的对着天空拜了拜。
刘氏这叫一个急啊,迭迭撞撞的跑到明阳面前,将明阳拉起来,照着屁股就打了一巴掌,明阳登时委屈的哭了起来。
刘氏不理会明阳,反而对明月嗔责道:“你这闺女,咋不拦着点儿,小娃子瞎胡闹,你也跟着瞎胡闹?这亲能是随便成的吗?明阳和高儿可是兄妹!”
明月不以为然的耸耸肩,现出一抹笑意道:“娘,你怕啥,不过是小娃子过家家的游戏,算不得真,想玩就玩呗。”
刘氏的脸登时就冷了下来,痛惜道:“月儿,你咋还胡言乱语呢!这亲能是说订就订的?那是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再说,明阳和高儿是干亲兄妹,一日为兄,终身为长,万不可乱了纲常!!!”
明月眼睛登时就大了,怪异道:“娘,有啥不行的?姨表兄妹、姑表兄妹都能亲上加亲,为何到了干兄妹间就不行了?临村还有父子二人娶了母女二人的呢!再说,现在他们还小,将来年纪大些了,若还是两情相悦,我们成全他们便是。”
刘氏赶紧捂住了明月的嘴巴,小心翼翼的四处望了望,生怕被别人听到这胆大妄为的言论惹了祸事,见明月不再挣扎和言语了,才小心翼翼的放下手,小声道:“月儿,以后可别说这些大逆不道的话了。姨表兄妹、姑表兄妹结亲,是亲上加亲,就连京城的贵胄们也经常这样做;父子嫁母子,那是农家灾年无奈之举,却还是会被人垢病的,高儿的爹是县令,定会谨守祖宗礼法,明阳与高儿虽是干亲,但也算是兄妹,所以是万不可能的。”
高儿气得一跳脚,向山下跑去,边跑边气道:“我这就回去问爹,我就不信我永远是个外人。”
明月不由得哭笑不得,原来高儿“求娶”明阳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不想成为“外人”;成为殷家“内人”的心思还挺“浓烈”,不过,对于明阳而言,这个成高儿,除了经常扯头发,拿虫吓唬,倒也不失为一个合适的“青梅竹马”,最起码,上次遇到一条髭狗之时,成高儿最先将明阳护在自己身后,连松儿都慢了一拍。
明月懊恼的掀着铺了一地面的长了绿毛的豆子,翻了翻面,不再看刘氏一脸忧愁的模样。
相比于明阳与成高儿的遥不可及的“亲事”,明月则更关心它的酱油能不能酿制成功,毕竟,盐太过显眼,她脱不了手,而酱油不同,黑漆漆的,寻常百姓一般不会儿想到盐上来。
自从晒起了豆子,成越便自告奋勇的住进了地里的草房子里,一如当年训练明月杀狼捉熊之时。
看着一脸惬意的成越,明月呵呵笑道:“小越越,你是不是觉得山下的人越来越多了,你有些嫌烦了?”
成越不置可否,一人独居得久了,乍一入村庄生活,总觉得有些不适应,让他出山或融入人群,比杀了他还要难,他甚至知道,他这一生都会留在这沧澜山中,与山为伍,与水为伴,如果说与人类社会中有些投契的,大概也只有明月一人而矣,亦师亦友,他从不想深入了解明月的隐私,明月亦不想剖析他的过去,更不会强求他做些什么,这样淡淡的,保持着一个安全距离,互不奢求。
将豆子翻了个面,看着一望无际的豆胎,明月说不出惬意,对于未来的生活,更是充满了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