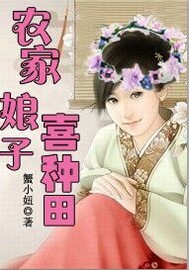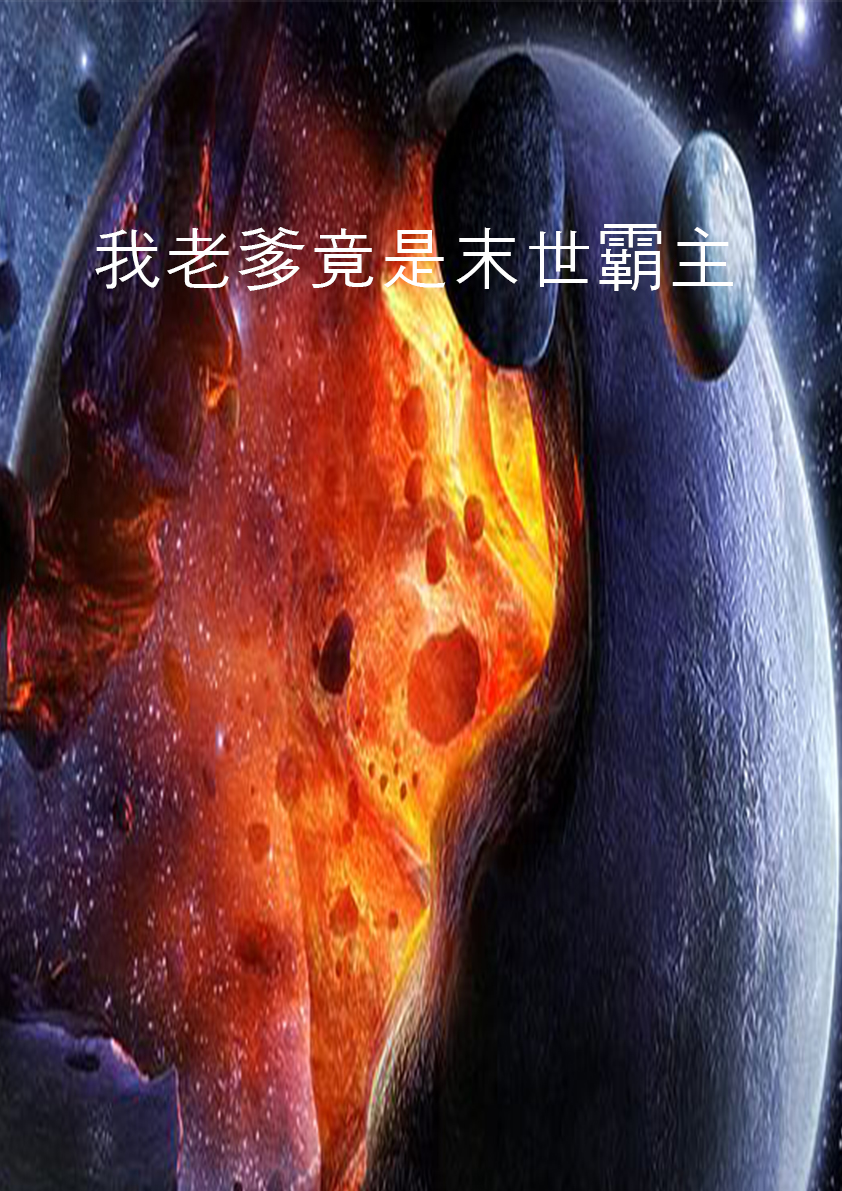“什么?”明月听了明松说的事情经过,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更是气愤于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宋氏,殷明朝也脱不了干系。
三房与老宅分明已经脱离了关系,没想到他们还是含恨在心、伺机报复,这若是松儿出了什么事情,明月会恨自己过去对她们太过仁慈,就应该如同对待赵二狗一样,来个人间蒸发得好。
明月脸色不由得沉了下来,攥紧拳头、咬牙切齿道:“宋氏,别让我再看到你,否则见一次打一次。”
松儿扯了扯明月的衣袖,呆萌道:“姐,我睡得迷迷糊糊中,听魏大哥好像得风寒症了,隔一会儿就咳嗽两声,洪大人脾气可不好了,对魏大哥拍桌子瞪眼睛,说什么要想杀大伯娘头,被贩的需是皇亲国戚,等我成了他小舅子以后再说,现在只能流放三千里。姐,小舅子是谁啊?比弟弟还亲吗?流放三千里是啥意思,是不是我们以后就见不着大伯娘了?大伯会不会恨上咱家?偷给咱家下绊子?”
明月毫无征兆的脸就红了,白里透着粉,粉里透着红,这洪丰怎么当着孩子面瞎说什么呢?这魏知行也是的,明明与自己一幅划清界线、老死不相往来的模样,关键时刻为啥不反驳一下?咦,他不仅是大官,竟然还粘着皇亲?那洪丰怎么敢对他吹胡子瞪眼睛的?等等,魏知行得了风寒症了?貌似,刚刚是在自己背后咳了两声......
姐弟二人一路无言、各怀心事,明松担心老宅知道宋氏被判流放后对三房不利;明月则是犯愁这魏知行的暧昧态度是何用意,还有这风寒是真是假。
二人回到刘氏的房间,见刘氏正端着粥喂着一个和松儿同龄的男娃,小男娃的脸上粉雕玉琢一般的好看,眼睫忽闪忽闪的,似煽到人的心里一般。
明月拉过椅子,直接将松儿抱到椅子上边,小松儿软糯的抱着刘氏的胳膊,一顿邀宠。
高儿一见登时不干了,抬手用筷子“啪”的打了松儿的手背一下,趁松儿松手呼痛的时候,如炸了毛的小獅子般扯回刘氏的袖口,嫌弃的用手擦了擦根本不存在的灰尘道:“小乞丐,离我娘远点儿。”
松儿在外颠沛流离几日,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最终辗转了多少地方,被救后,又饿又困,魏知行着急审案,又恐松儿不在身边有危险,所以连衣裳也没有换,确实是又脏又臭了些,可是,人家洪大人和魏大哥都没表示嫌弃啊?!
从头至尾一直紧强的松儿心里防线瞬间崩塌,登时就红了眼圈,强忍着没有流下泪水,将身子往刘氏的怀中靠了靠,明月安慰性的拍了拍松儿的后背,鼓厉性的竖了竖大拇指。
松儿如有了主心骨般,坚强的回瞪高儿道:“这是我娘,我亲娘,别说我像乞丐,就是掉到茅坑里,娘也不嫌弃。娘,松儿说得对不?”
儿子平安归来,刘氏早己喜极而泣,将松儿紧紧的、紧紧的抱在怀中,生怕抱得松了,松儿就会如沙子般流跑了,嘴里不住的答道:“娘哪能嫌弃我的松儿?松儿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球球,就是娘的命根子。”
高儿气哼哼的不说话,将筷子重重的拍在了桌子上。
刘氏从上到下的摸着松儿,嘴唇和手都激动的哆嗦着,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
最后忙将自己喝了一半的粥碗推到松儿面前道:“儿啊,小脸都瘦抠抠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娘的心都吓出来了,快吃些粥垫垫,娘一会儿亲自下厨做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高儿气得将自己吃剩下的粥碗一骨脑的扔进了粥盆里,气鼓鼓道:“这是我爹派人给我送来的吃食,扔了也不给小乞丐吃。”
明月一看气恼了,这谁家的熊孩子,这样的刁蛮任性,还浪费粮食,关键的关键,她还饿着呢。
明月轻哧了一声,毫不在乎的将被扔盆里的碗捞了出来,不嫌弃的直接就着碗盛了粥,“唏溜”吃了一口道:“松儿,有人不吃,咱来吃,姐不是教过背过《锄禾》吗?浪费粮食是可耻。”
松儿嘴角偷偷上扬,想伸手拿粥,偷觑了一眼如青蛙般鼓着腮的高儿,看着面前桌上的粥碗,却是娇嗔的抬了抬胳膊,轻呼了一声痛,扁着嘴对刘氏道:“娘,松儿胳膊痛,要娘喂......”
刘氏宠溺的刮了刮儿子的小鼻子,自己与松儿虽是亲生母子,但毕竟自小就分离,回来这数月,虽然关系近了一步,但还从未如今日这般邀宠的,这让刘氏心里不由怯喜,更不可能拂了小儿子的意思,将碗端起来,放在嘴边吹了吹,待温热了,这才递到松儿的嘴边,如喂着雏燕似的道:“大乖儿子,张嘴,吃饱了就不痛了。”
高儿气得脸都绿了,从小凳子上一下子就跳到了地上,重重的跺了两下脚,见几人不理会他,又气恼的将凳子踹倒了,扁着嘴,飞一般的冲出了屋子。
刘氏焦急的放下碗,想去追又莫名其妙耍脾气的高儿,被明月一把扯了回来,摇了摇头,示意刘氏稳坐不动。
高儿刚出了屋子,小翠、“大桌子”、宋娇娇忽啦啦都挤进了屋子,尤其是“大桌子”,笑得那叫一个前仰后合、好不开心,笑道:“明月,还是你有招儿,这公子爷快折磨死我们了,一会儿要这个,一会儿要那个,平时不让我们进屋,和婶子多说一句话就瞪眼睛,动不动就张嘴说大刑侍候,这县太爷家的公子爷真是难侍候。”
明月这才恍然,难怪这熊孩子一身的太子爷毛病,原来是成鸿略这县太爷家的独生子,完完全全的给惯出来了, 只是为何管自家的娘亲也叫了娘呢?
明月将心中的狐疑说了出来,刘氏忙摇着手解释,只是她嘴笨,越解释越结巴,好在明月是个会听的,断断续续将刘氏阴差阳错下救了高儿的事儿听全了。只感觉这世界真是奇妙无比,和县太爷家竟结下了这么个渊源。
几人正在屋中叙说离别之苦,不胜唏嘘,只见一个衙役快速的跑进屋来,气喘嘘嘘对刘氏道:“殷夫人,大事不好了,公子爷出事了!”
几人不明所以,纷纷跟着衙役向外跑,明月边跑边问那衙役道:“发生何事了?是那些歹徒又回来劫持成高了吗?你们这些衙役干什么吃的?快拿刀剑抵挡啊?!”
衙役老脸一绿,半天才憋出一句话道:“公子爷不让我们救,只让殷夫人救。”
什么情况?明月突然从中嗅出了一处诡异的味道,再往前跑两步,衙役的脚步一停,明月筋了筋鼻子,不仅嗅到了诡异的味道,还嗅到了特别的味道。
定睛一看,几人不由得面面相觑,驻足的前方,不是别的地方,而是客栈茅房的正前方。
刘氏不明所以,那名衙役不忍直视的指了指其中一个木制的茅房门,刘氏伸手推开门,众人抻着脖子、掩着口鼻往里观望,没人,也没有动静。
刘氏狐疑的看向那衙役,衙役叹了口气,走上前来,对着茅坑下面喊道:“公子爷,殷夫人来了。”
刘氏弯着身子也向茅坑下边望去,险些呕了出来。
这茅房外面是木制的结构,上面是木板条的蹲坑,里面则是挖得较深的茅坑用以囤积粪便,现在是隆冬,粪便掉下去,形成了一座高高的粪便尿水混合冰山,刚刚自诩干净、傲骄的公子爷,此时如一只猴子般站在“粪尿冰山”上,一动不敢动,浑身的腌臢不堪,那模样,连一身邋遢的松儿也不由得捂住了脸、不忍直视。
衙役叹了一口气,将手伸向坑下的公子爷,带着讨好与哀求的口吻道:“公子爷,殷夫人已经请来了,你这下可以上来了吧?”
高儿扁着嘴,眼睛一瞪道:“我让你去请谁?”
衙役倒抽了一口凉气,忙打了自己一耳光道:“公子爷,小的嘴误,不是殷夫人,是夫人,公子爷的亲娘。”
高儿这才满意的伸出了手,不是伸向衙役,而是伸向刘氏,撒着娇道:“娘,你嫌弃我吗?你能抱我出去吗?”
明月有些哭笑不得了,刚刚以为这高儿是个任性刁蛮的公子哥,现在看来,不过是个打小没娘疼的娃子,所以的行为,不过是想跟松儿抢一个娘!听刘氏刚刚说不嫌弃松儿脏,高儿羡慕妒忌恨,干脆心动不如行动,直接跳到茅坑里了!!!
刘氏心疼的双手一揽,将一身脏兮兮的高儿从茅房坑里抱了出来,不由嗔责道:“你这娃子,赁的淘气,娘怎么会嫌弃你脏哩,你这身上还有着伤哩,可怜的孩子。”
衙役眼明手快去准备浴桶与洗澡水,刘氏则抱着高儿往房里走,高儿的脸背着刘氏,对着后面的松儿扮着鬼脸,吐着舌头,仿佛粘了一身的,不是脏屎,而是骄傲。
只这一个动作,令松儿的小脸顿时垮了下来,也黑了下来。
明月看着这两个小娃子幼稚的行动,简直啼笑皆非,眼珠一转,到了屋中,对刘氏道:“娘,松儿的身上也太脏了,也要洗上一洗,就让这二人一起洗吧。”
“大胆!”高儿气得岔着腰,只是浑身的脏屎让他看起来毫无气势。
“绝不!”松儿气得掩着鼻,一幅我脏、他更脏的嫌弃样。
“必须行!要不然就没娘!自己选!!!”明月先刘氏一步表了态。
两个男娃子背对背,气鼓鼓的谁也不吭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