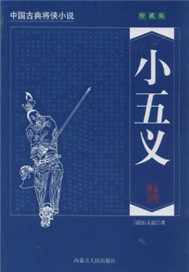几堵危墙,方寸草顶,奈何挡不住江湖的险。干燥的微风吹过,刮的人眼睛酸涩泛红。
雁南飞踩着软软的银杏叶,踉跄地走出破庙,几个人跟在后面,既没有上前,也没有落下,始终保持着一个微妙的距离。
这种凋零的时节,这样耐心异常的人,如果不是来送行,那便是来送葬,他们显然属于后者,只是要等的人还未到。
“我说,你受了这么重的伤,就别白费力气,耐心等一会不好么?”自负的年轻人抱着双手,懒懒地坐在树下,把玩着一把精致的刀子。
漂浮着灰尘的光束洋洋洒洒地照在他身上,让他看上去有种难以言喻的阴邪。他愉悦地笑着,仿佛在享受这种难得的闲暇时光。
虎落平阳被犬欺,不曾想这种宵小也能欺负到自己头上。
“哼哼……”雁南飞自嘲地笑了一声,凭着一股信念继续向前,用肢体的无言回敬年轻人话语的轻狂。
“看来不吃一点苦头,你是不肯老实了……不过没关系,我有的是时间陪你玩。”
年轻人熟络地将刀子挑上指尖,戏谑地吹了口气,一股灵力随之缠绕上锋刃。他随意朝一个方向拨出,动作优雅地如同拨弄一根琴弦。
“东西在哪里?”折磨人之前总会让他产生一种无法释怀的快感。
“东西在蓝草涧白家,有本事自己去取。”
“哦?是么?”
刀子飞射而出,毫不费力地在远处穿透了雁南飞的脚背,稳稳地钉在地上。年轻人弯了弯手指,那些包裹在刀子上的灵力便如春雨灌溉下的种子,在肉体下疯狂地生根发芽,一直牢牢抓进土地。
“这就是你所谓的蓝草涧白家吗?不过尔尔。”
雁南飞身子一斜,半跪下来,她低垂着头,深埋长发之下的瞳孔因剧痛而急剧放大,显然那种痛楚不是常人可以忍受,不过她紧紧地咬着嘴唇,直到将足下的痛楚彻底掩盖,她才缓缓松开牙齿,如释重负地“啊”了一声。
“白玉京的手段也不过如此!”她费力地抬起头,想要站起来,可口中却无法抑制地涌出鲜血。
一种混合了血水的叱笑,就如同一种意图明显的嘲讽,更加重了听者的戾气。
年轻人的嘴角微微上扬,冰冷的眸子毫无生气地看着不肯低头的女人,手指慢慢伸直,下一刻骤然握紧,一股无形的气息突然从他的袍子翻涌而出,“既然这么倔强,那你最好别这么快死掉,不然就太无趣了。”
前一刻还宁静的土地忽然之间开始剧烈摇晃,几条石手飞速地顶开地壳,爬上雁南飞的双脚,攀上她的身体。
雁南飞只感觉到一股不由自主的力量瞬间弯曲了她的膝盖,击碎了她的膝盖骨,让她重重地跪在了地上。
死亡近在咫尺,让人忽略了雁南飞原本也是个危险的人物,冥冥之间,有一股令人难以察觉的灵力在那副颓败的身体里流动。
年轻人麻木不仁地看着被他弄碎的膝盖在皲裂的土地上留下一条条血痕,心满意足地收回手。
“现在看上去好多了。”他的话甫一出口,几点银星已经到了眼前,他的目光骤然冷绝,电光火石之间,体内的灵力陡然激增,“冥顽不灵,真以为我不敢杀你?”
他远没有佯装的那么大度,他本来没打算在白子柒来之前痛下杀手,不过雁南飞彻底消磨了他所剩无几的忍耐力。
空气中是袍子翻滚咆哮的声响。
吞吐着锋芒的银针连同那一吹即散的面纱一起,慢动作似地倒飞出去,雁南飞跌在地上,冰冷的鞋底随之踩上她的脸颊,将她以一种最屈辱的姿势压在地上。
雾里看花最是妖娆,那种成熟女性无力躺倒时的娇媚就像是开在浓雾深处的妖花,让人欲罢不能。
这个天下的正人君子本就不多,眼前几个更加算不上,要说怜香惜玉,他们更愿意在床上。
年轻人用鞋底将她的脸挑起,兴致勃勃地瞄了眼背后摩拳擦掌的几人,又低头看着脚底的丰腴身体,邪气在他的脸上慢慢凝固成生硬的线条。
“你喜欢折腾,那就让他们陪你好好折腾一番,没了衣裳,东西应该就藏不住了吧!”
修长的手指扣上衣带,轻轻一扯,楚楚可怜的女人瘫在地上,目光涣散,无力应对这些羞辱。她的嘴巴张合着,仿佛呼唤着什么。
“我告诉你们一觉醒来天下就太平了,对不起,我要食言了。”
天空阴郁,一排凋零的银杏树仿佛一群失去孩子的母亲,在晚去的寒意中飘摇着惨淡的金黄。
一把锈迹斑斑的刻刀抽出,干脆利落地刺下。
“嘭嘭嘭!”一连串巨响。
刀子并没有如愿以偿地送进心脏,雁南飞隐约看见鲜红的液体一点一滴地从眼前砸下,而顺着那只握住刀锋的手看去,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年轻人,像极了当年那个男人。
――你可愿冠我姓氏,替我看遍华夏河山?
七尺的挺拔身躯,葇胰青葱的挽腰臂弯,那一年他们如此道别。
“取风?”鼓动的衣袂伴着轻盈的耳语坠地,一抹久违的笑涌上嘴角。
温和的年轻人张着嘴,灵魂出窍般盯着那张熟悉的脸庞,身躯兀自颤抖着,仿佛是无数油星子飞溅在他心上,烫得他一颤一颤的疼。
雁南飞,隐姓埋名也藏不住的情,北去的大雁终会南飞,原来你一直在盼我们回来!
“四姨,是我。”
这张深深埋在泥土中的脸白子柒不会忘,这把锈迹斑斑的刻刀他更不会忘,是风四娘教他和姐姐做花灯买的。
“我回来。”
黑夜中隔着白家那场大火对望,女子独自走上绝路,二十几年不曾在梦中回头。
白子柒哭了,风四娘却笑了,白子柒笑了,风四娘却又哭了。
碧落黄泉,命运辗转的压痕下,只剩满目疮痍的旧时亲颜。咫尺之隔,却仿佛隔着忘川河遥望,这边是不舍的愁绪,那边是难离的哀伤。
只是他们从未想到彼此还能再见。
“你还活着。”缥缈若无根浮萍般的话音伴着晶莹的泪珠砰然坠地,“太好了,小柒。”风四娘忍着剧痛,哭的像个孩子。
“对不起。”
记忆中的那个女人即使受在多苦也不曾流过一滴眼泪,此刻她却哭的梨花带雨,女儿家家。白子柒抱着昏死过去的女人,心疼地为她擦掉眼泪,小心地褪下身上的袍子,盖在她身上,然后旁若无人地走上前,从背后抽出那方木匣,重重地拍在身前。
他的目光沉静,谁也无法洞穿深邃的瞳孔深处眼下酝酿着什么,他弱弱地站在那里,就像站在一个常人无法企及的世界里。
“是谁把她伤成这个样子?”
没有灵力,没有手握刀剑,更没有江湖的快意恩仇,但此刻的白子柒却像一柄最锋利的灵刃,不怒自威。
淡然的话语间也听不出情绪,犹如白纸黑字陈述眼前,无法否认这些人将死的事实。
一众人听后嘲笑起来,完全没有将一个察觉不到灵力的人放在心上。
“你要为她出头,最好打听清楚站在你面前的是谁?”
“他么?”白子柒幽幽地将视线转向一旁的年轻人,冷冷开口:“就是你伤的她?”
“是又如何,听说你最讨厌杀人,不过……今天我封一寒就算当着你的面杀了她,你又能将我怎样?北落,叶望秋。”年轻人趾高气昂地抬起头,似乎对白子柒了若指掌,并没有因为他的出现而感到意外,话语间处处透着浓浓的火药味。
“怎样?”瞳孔微缩,白子柒一步踏出,伸手按着躁动不安的剑匣,“既然你认识我,那就更不应该伤她。”
他拔过狼舌,面对过死亡,也挥剑斩过仇敌……这些他都不怕,他唯独怕失去。
他的胸襟可容天下,却在一瞬间又成了这最狭隘的人,只因他无法失去更多亲人。
那方木匣开始轻轻地抖动,如泣如诉,蠢蠢欲动。
话音甫一歇止,土地瞬间亮了起来,金色的阵纹在脚下飞速旋转,一朵莲花赫然凝聚成型。
“半步莲华。”
欲进欲退,半迎半休,半步退而步步生。
酒鬼曾借着酒性使过,白子柒平素不爱杀人,只取了这半步,道是半步进退,莫置人于死,但杀人的招式即便你如何回避,它也是用作杀人。
白子柒的身形快如鬼魅,封一寒刚察觉到地面的异样,身前几步的地方突然绽开一朵金色莲花,他的眼前倏忽一花,便见白子柒轻踏花心,手下浑厚的掌风如涟漪阵阵,一浪浪,一层层向自己胸前涌来。
他骇然地看着那只充满威胁的手顶到胸口,下意识伸手搭上那截手腕,却并没能立刻中断那股不断渗透过来的劲气。
“真是小看你了!”
阴恻恻的嗓音自负而暴戾,苍白的脸上逐渐浮上死人般空洞的表情。
“不过不用上你那把剑,怕是不够。”
他的手猛然扣紧,源源不断的灵力涌出,如同一条条锋利的蛇,顺着五根修长的手指钻进白子柒的手腕,又从各个可以穿透的地方穿出,将那条瘦削的手臂啃噬的体无完肤。
白子柒一剑击败柳烟柔的实力虽然可怕,然而封一寒对自己的灵术修为同样有绝对的自信。
不同于剑修依赖手中长剑,也不似阵修需符法篆刻,灵修只要有介质,便可以自身灵力灵化为自己所用,而封一寒灵化的介质是无处不在的尘土,修到精深处,整个大地都可以成为他的武器。
只是他还没来得及将这种自信变为现实,一阵迅速的疼痛突然切断了他对手中灵力的控制。
“砰!”一阵急促的弦音。
视线中,怦然张开的金色阵纹飞速旋转收缩,仿佛一套枷锁,转瞬扣紧。而金光暗淡的背后,是白子柒凌驾众生之上的脸孔。
不用灵力瞬间连开两阵?
封一寒瞪着一双凸出的眼珠子,看着胸前那只仿佛感觉不到痛楚的枯手,感受到了真正的恐惧。
“君临,止杀!”剑匣嗡嗡低吟,白子柒伸直血肉模糊的手,缓缓下握,一柄剑凭空抽出。
以杀止杀,这一剑是回敬嗜杀的人们。
须臾,一股无法预知的灵力如溃堤的洪水倾泻而出,不是来自白子柒,而是来自他手中的那把剑――君临。
封一寒的脸色煞白,而几尺之外的白子柒面容依旧如止水平静,他的目光沉静,一点也不盛气凌人,可就是这种君王般的慵懒,却一点点将封一寒不可一世的气焰剥离体外。
空气中四处闪动着微弱的金光,在这种难以抬头的灵压下,封一寒的手已经无法抓紧,膝盖也忍不住要碎裂弯下。
“噗!”一口血喷出,他终于跪在了地上。
白子柒收剑,一脚重重地压上他的肩头,用力将他高傲的头颅踩到地上。
高高在上的年轻人从未受过这种羞辱,即使在白玉京他也是人中龙凤,如今却像条狗一样被人踩在地上,脆弱到毫无还手的余地。
他咬着一口森森白牙,满脸涨红,像是羞愤,又像是一种深深的不甘。
“人不是你们想杀便杀,至少在我白子柒这里不行。”不可置否的声音用一种平静的口吻说出,如同陈述一段无可争议的事实。
“今日你不杀我,他日我要你十倍偿还。”
来自脚底的咆哮,白子柒闭着眼睛,仿佛在倾听心底某处的声音,过了一会,他才松开脚,压下心中那股杀人的欲望。
如果自己随便杀人,和这些人又有什么分别?
他睁开眼睛,看了眼四周惊魂未定的人,走到剑匣旁,重新将它背回背上,然后在众人恐惧的目光中,带着风四娘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