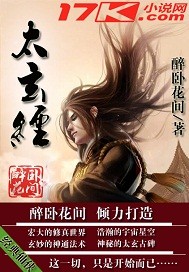酒馆角落里有个男人,只顾饮酒,似忘了吃菜。一壶饮尽,小二又端上一壶。
他却不豪饮,他在品,如品香茗,品酒中的滋味,一口滋味到了尽头,又倏尔将整杯酒灌入喉中。
仿佛剩下的,已不须再品了。同一壶里的酒,每一杯都是一个滋味,每一滴都是一个滋味。
其实他心知这是错的,纵使是同一壶酒,每一杯、每一滴,乃至每一丝,都应是不同的滋味,就像人潮之中的每一个人,分不清彼此,却不能否认他们各自存在的模样。
然他已无心再品了,酒的滋味不在酒本身,而在饮酒之人的心。此刻冷萧的心,只有这一种滋味,所以,已经无须再品了。
半醉的酒客手指点落在他身上,醉意似乎清醒了些,又仿佛醉得更深了。他眼中所见,如有一团浓雾,将那人深深地裹挟在其中,他被一双深邃而冰冷的眼睛凝视着,直看进他内心深处。
他大叫一声,身体瘫软了下去,旁人只笑他醉了,他口中却流淌出一丝白沫。其有人惊讶,前去探望,却跌坐在地,失声叫道:“他……他死了!”
另一人搁置酒杯,睁眼怒道:“何人下的毒手,究竟是何人害我兄弟!”
店内,有位老者停箸前来探看,漠然摇了摇头:“心脉骤绝,瞳缩而面狰,他是活活惊吓致死。”
“惊吓,这小小店中,他还能看到什么大恐怖不成?”
旁的酒客议论声不绝,全然没有当回事。世间从不缺厄难,只要厄难不落在自己头上,就全然不值得在意。
有人笑道:“莫不是醉得太深,陷入了幻梦,活生生将自己给梦死了?”
死者友人一时大怒,然却是最后一人,将他拉住,一双眼睛缓缓移到角落上的一人。
“二位漫动,可曾记得方才李兄死前的样子?”
“是何样子,某的脸上全是他的唾沫星子!”
“呵,李兄身子所向,目之所望,手之所指,全是那个方向,不若说,全是那人。”
旁人也随着他的话语,将眼神转了过去,另一人道:“张兄如何断言?”
“周兄且看那人,自斟自饮,怠慢了身侧佳人全然不顾。举止古怪自不必说,周兄难道不觉得此人甚为眼熟吗?”
“眼熟,我是断然不见过……张兄是说,李兄猝然而死时所说的那个人?”
他话音不重,却传进每个人耳中。几乎所有人都因此而停杯投箸,望向那人。人若是不在意,看黄金也如粪土,当人在意时,纵使眼前是猛虎,他们也只当是一只花猫。
不试试,总是不会甘心。
冷萧依旧在饮酒,酒已快饮尽,小二却已不再送酒了。他知晓这杯酒走到了尽头,兴致也到了尽头。他的脸上却全无两样,抑或他从未起过兴致。
他搁下二两碎银,饭菜一口未曾碰过,只饮了些酒罢。
他揽起时灵曦,退开了凳子,朝外走去,却是那死者一桌三人,相视一眼拦住了他,一高大,一细弱,一文人。
高大之人似是莽夫,细弱之人似不善武,反是那文人,浑身透着些许危险气息。
文人道:“我等好友被阁下生生吓死,阁下想这样一走了之,我等只怕难以遵从。”
莽汉道:“张兄何必再多说,将这小子料理了便是,不管他是不是那传闻中的夺宝人,也是害死了李兄之人,今日岂能留他性命!”
文人制止道:“倘若他真是那夺宝人,武功自不必说,单凭我等三人,如何能留住他?”
细弱之人叫道:“我们四人相交,亲如兄弟,如今李兄尸骨未寒,难道要眼睁睁看凶手逍遥法外?”
三人唱和间,仿若一台戏。冷萧静静看着,仿佛在经历一件趣事。他两眼朦胧,两耳放空,心中并不排斥,只是他所见所闻,已全然是另一重意境。
有旁的酒客持刀站起,大笑道:“关某生平对此等滥杀无辜的恶棍最是深恶痛绝,倘若三位欠力,关某拔刀相助又有何妨?”
有人大笑:“如此趣事,断不能叫关兄独占!”
“岂可让关兄专美于前!”
掌柜似见惯了如此情景,依旧一下两下拨弄着算盘珠子,小二已钻至桌子底下,瑟缩着。厨子掀开帘子看了一眼,手中仍提着刀,刀刃沾着肉沫,三两息后又放下帘子。
酒客食客皆站起,纷纷亮了兵器,掌柜只在这时淡淡道了一句:“留下一锭银子,店中桌椅任尔等打砸,倘若无视于我,坏一个碗碟,卸一条胳膊;坏一张桌椅,便将命留下。”
有人恼其态度,随手将一个瓷碗掷下,摔得粉碎,拔刀相问:“我不是不讲道理之人,掌柜若道个歉,这碗的价钱我自然十倍偿你,倘若不道歉,我倒要看看掌柜能奈我何?”
掌柜依旧在拨弄算盘珠子,幽幽道:“本店虽然破落,却也不差一个碗的钱。”
他蓦然间抬手一拂,算盘珠子大半飞了出去,如雨点板朝那持刀之人落下。那人两眼一横,挥刀连斩,击落无数,却依旧惨叫一声,长刀落地,一条右臂被几粒横来的算珠生生撕了去。
寂静半晌,有人干笑道:“这一锭不过五十两,我等凑上一凑,也不痛不痒。”
酒客遂各自摸出几块碎银,丢在一起,汇总给了掌柜,掌柜看也不看一眼,却已是收了气势,翻阅着账本。
众人心中稍稍放松,然而即便有此保障,有人依旧先把桌椅抬到了一边,生恐砸坏了将命留下。
那断臂之人含恨离去,失去一臂,一身刀法毁去大半,除非武功绝世之人,终究是无法超脱肉体上的变故。
冷萧被团团围住,他却浑然不在意,只是淡淡道:“我手上没有寒刀,却有六张宝图,对应余下六个宝藏。今日我留你们性命,要你们替我传达一个消息,若想要宝图,以失传已久的药方、药典来换,当然,害人的毒药我没兴趣,我所要的,是救人的良药。”
有人失笑:“此人莫不是被吓傻了,竟还在自说自话!”
然下一霎,那人已从他眼前消失,他只觉得身上没一处不痛,再看所有人已倒在血泊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