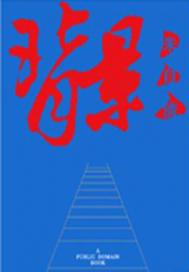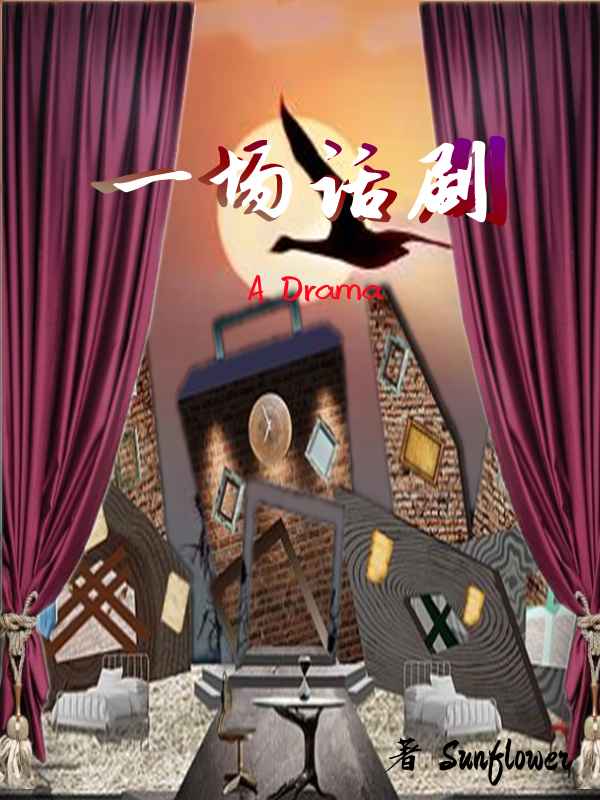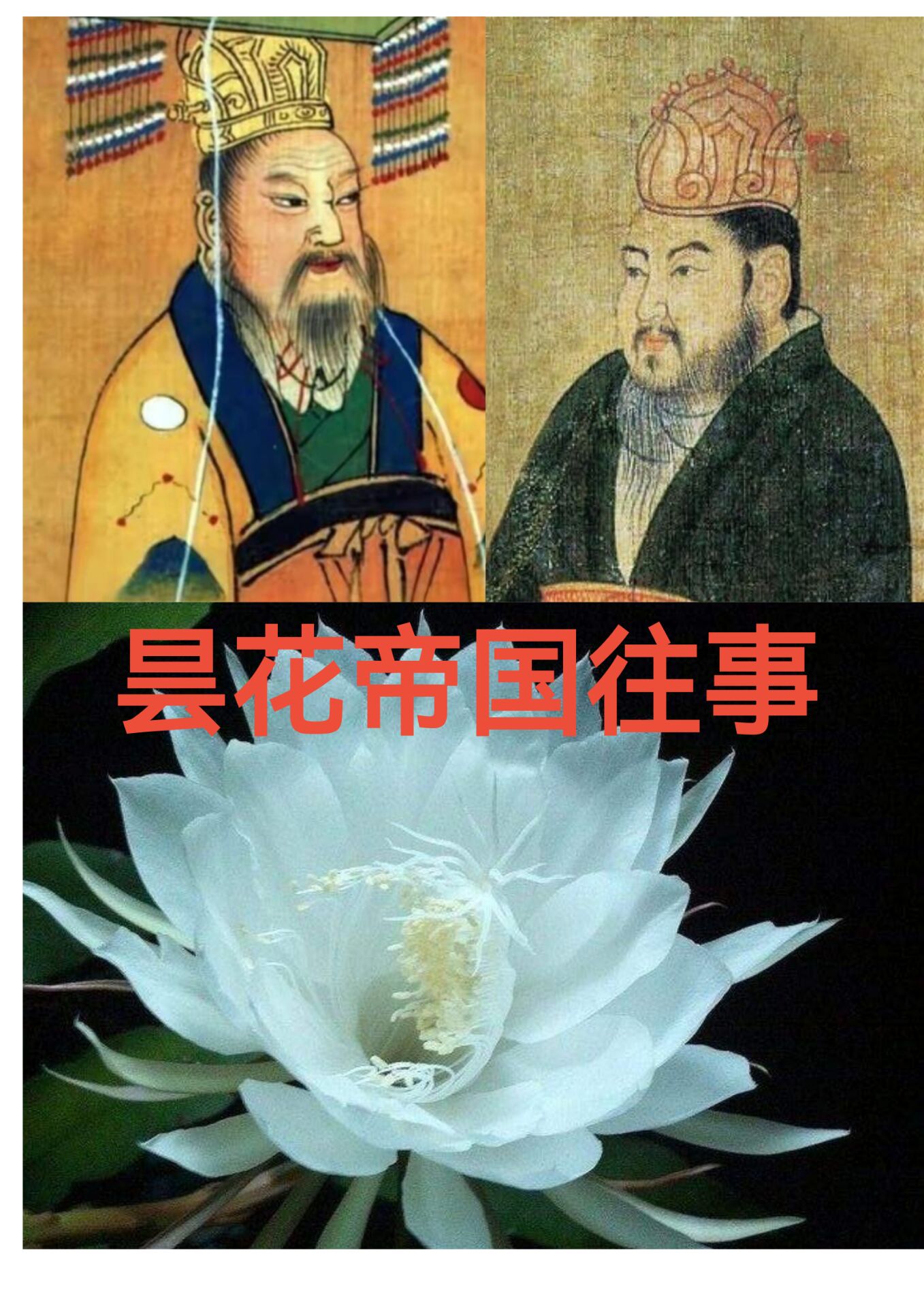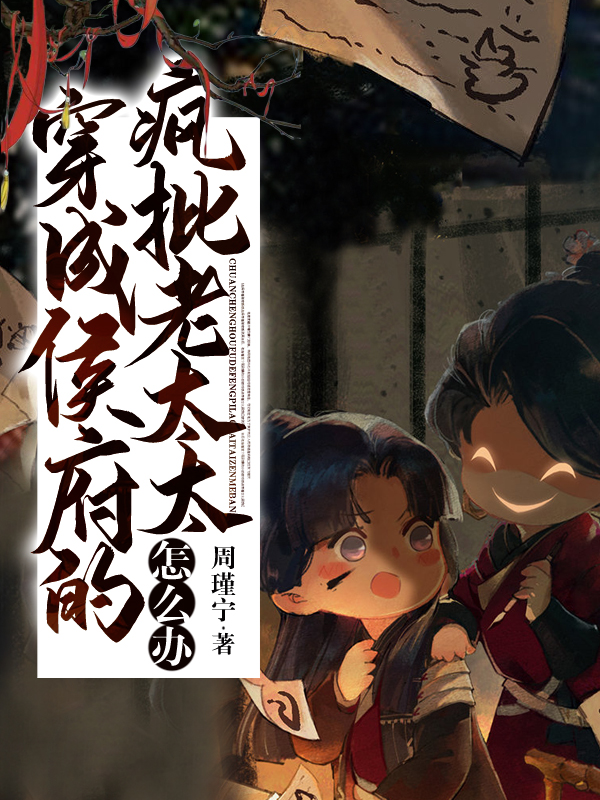记得我们在儿时,总觉得只有通过劳动才能被大人重视起来。周末从寄宿小学归来,倘若双亲吩咐我做一件与劳动有关的事,我那响应的心情也会因此而自豪。有一回正在做饭的母亲让我替她剥一棵葱,我拿起葱来就剥。但葱的层次太多了,而我实在不知剥到哪一层才算是剥好了葱,结果把一棵白生生的大葱给剥没了。母亲看看满簸箕的葱白没有责备我,只给我讲了剥葱的要领。从此家里凡需剥葱时我必定抢在前边,我乐意让母亲看见我学会了剥葱这样一种劳动。
假如我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想既没有人吩咐我剥葱,我也不可能因为掌握了剥葱的要领就兴高采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孩子对生活的判断和对自身价值的评估,自有他们的眼光,他们对剥葱本身嗤之以鼻也说不定。
在从前的一些年代里,我们曾经对“人之初,性本善”争论得昏天黑地,但不管结论如何,“人之初,性不恶”是可以说得过去的。因此孩子才是爹娘掌上的明珠,才是祖国的花朵,才是民族的希望,才是人生大厦未来的栋梁,才是牢固的夫妻关系的柱石,才是一个家庭可以成立的标志。孩子还是什么?是太阳,是春风,是人间一切美好词汇的总和,是一切活得疲惫不堪的成年人梦想回归的状态——不是常听人说嘛:“多么希望我还是个孩子!”即使是在刚刚举行的第二十五届奥运会开幕式上,虽然我们被如多明戈这样的歌坛巨匠富丽、热烈的歌喉所陶醉,但真正令我们怦然心动的,还是那个率领着多明戈们演唱贝多芬《欢乐颂》的金发男孩。当那孩子不加修饰的清纯童音在巴塞罗那的蒙维克体育场响起,有哪一位成人胆敢愧对这圣洁的童声呢?
没有孩子世界便没了希望,没有孩子人类的生存也丧失了意义。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孩子,因了国家控制人口的举措,因了优生优育的必要,因了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意,更因了有些父亲和母亲为了在孩子身上补偿从前他们未曾得到的一切,这些孩子对于家长来说便是那样的举足轻重。于是孩子深知了自己的分量,就不知什么叫做“不行”。他所要的,立刻就有;他说往东,你不能往西;他讨厌你时,你须尽快避开;他沉默时,你便不可喧哗。如此,从前的情形就颠倒了一下:从前是大人喜欢议论谁是他宠爱的孩子;如今孩子可随时挑选哪个大人能够得到他的宠爱。我曾在街头冷饮店门前见到这样一幕情景:一位白发老者手推童车,躬身问车内一三岁左右儿童:“你吃雪糕还是喝汽水?”三岁儿童低垂眼皮,似听非听。白发老者将身子躬得更低些,再次问道:“你吃雪糕还是喝汽水?”三岁儿童把眉头皱起,仍是似听非听。白发老者用了几乎是谄媚的温婉音调第三次问道:“你吃雪糕还是喝汽水?”这次儿童终于开了口,口气之骄蛮、之不耐烦,宛若某些对下属发令的上级。他皱着久未松开的眉头说:“急什么,让我想想呀!”若此时白发老者再不知趣地打断他的“思路”,车内儿童定会瞪眼断喝一声“讨厌”了——这使我想起孩童的以眼睛瞪人之习惯,似乎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也特别发达。有位记者朋友出差数月回到家中,他那未满两岁的女儿就用狠狠瞪他的方式向他表示了“欢迎”,好比某些文学作品里惯常的描述:“××用眼睛狠狠地剜了他一下。”瞪和剜也许还有区别,但瞪和剜都足能引起大人的感慨。这记者叙述时便带出得意的感慨,说如今的孩子到底比我们那时聪明,小小年龄居然已学会利用眼珠传达情绪,简直不可思议,简直成精了!
若在公共场合,瞪人、“剜”人则显出逊色了,因为瞪和“剜”毕竟是无声的,他们愿意弄出点翻天覆地来。有一次乘火车,我与一位学龄前男孩为邻。显然这男孩对于这列火车除载着他和他的父母以外居然还装载着其他人颇为不满,而这些旅客又不曾对他表示出如他父母对他那般的热忱,就更使他倍觉孤独。于是他便决定闹出点什么,于是父母便成了他磨难的对象。他一忽儿光脚在车厢走道上奔跑;一忽儿又返回座位将踩脏的脚丫蹬他母亲的腿;他一忽儿指挥他的父亲下车买烧鸡,父亲买回一只他还要他去再买一只,因为他要吃三个鸡爪;他吃完三个鸡爪便是无数次地要求吃西瓜吃蜜桃吃泡泡糖喝饮料,紧接着就是母亲无数次地陪着他去无数次的厕所。厕所终于去完了,而他一时又想不出别的闹法,只好骑上他父亲的脖子,揪他父亲的头发挖他父亲的鼻子扇他父亲的耳光。当他的父亲半是玩笑半是严肃地问他“你知道我是谁”时,孩子马上回答:“你是大坏蛋!”这样的孩子,若只对自己的父母如此倒还罢了,正所谓周瑜打黄盖——打的愿打,挨的愿挨。自家人好算账,不是吗?可是,大人总不能启发孩子去扇别人的耳光,骂别人是大坏蛋。在别人面前,大人总愿意展示一下孩子的聪明伶俐乃至必要的礼貌。例如碰见熟人,大人多半会启发孩子“叫叔叔”“叫阿姨”之类,至于叫与不叫要看孩子此时此刻的兴致。倘他正逢高兴,也许会大叫一声“叔叔”或者“阿姨”,即便那叫声里充满着心不在焉,这叔叔阿姨也会以高涨的热情来夸赞孩子的乖巧和仁义。可惜下回,还是这叔叔还是这阿姨,还是这孩子还是这孩子父母的启发,孩子则死活不再开尊口。他望着眼前的叔叔阿姨,一副不屑一顾的姿态,接着还会不耐烦地扭动身子并辅以跺脚、摇头。若此刻父母再对他施以启发,他会愤怒地拿眼“剜”起叔叔阿姨(这会儿可真叫剜了),叫着:“就不!就不!”不止一位叔叔阿姨对我谈及他们在这种孩子面前的尴尬。因了这尴尬,再逢这样的孩子,他们便预先识趣地躲开,且惟恐避之不及。
这孩子之一种固然不叫人喜欢,然而这一切又实在怨不得孩子——毕竟人之初,性不恶。他们那过早掌握的以眼珠“剜”人的本领,他们那颐指气使的行为做派,他们那无视他人存在的专横言辞,有哪一样不是从成年人身上学得的呢?我们亦不止一次地看到,有些尚被成年人称为孩子的年轻父母,因了自己手中更幼小的孩子,就认定自己的一生已经圆满;就认定他们之所以还能活下去,完全是因为这手中的孩子。他们甘愿蓬头垢面,衣衫不整,饮食饥一顿饱一顿,工作有一搭无一搭——只要能寸步不离他们的孩子。母性的光辉确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这样的父母在走进厨房时,也决不会劳子女的大驾为他们剥葱。但我仍然怀疑在这种光环笼罩下的孩子,当他们长大成人后,真的能够感激并爱戴他们的父母吗?
假如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平等关系是人类一种美妙的关系,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平等决不意味着让大人变成孩子的奴仆。
在您的孩子面前您是大人,在您的大人面前您是孩子。所有的孩子都是人类的希望,因此您必得有雄心学会同您的孩子一道美好地成长。这样的成长其实需要更多的勇气和智慧,以及正视自己的耐心,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