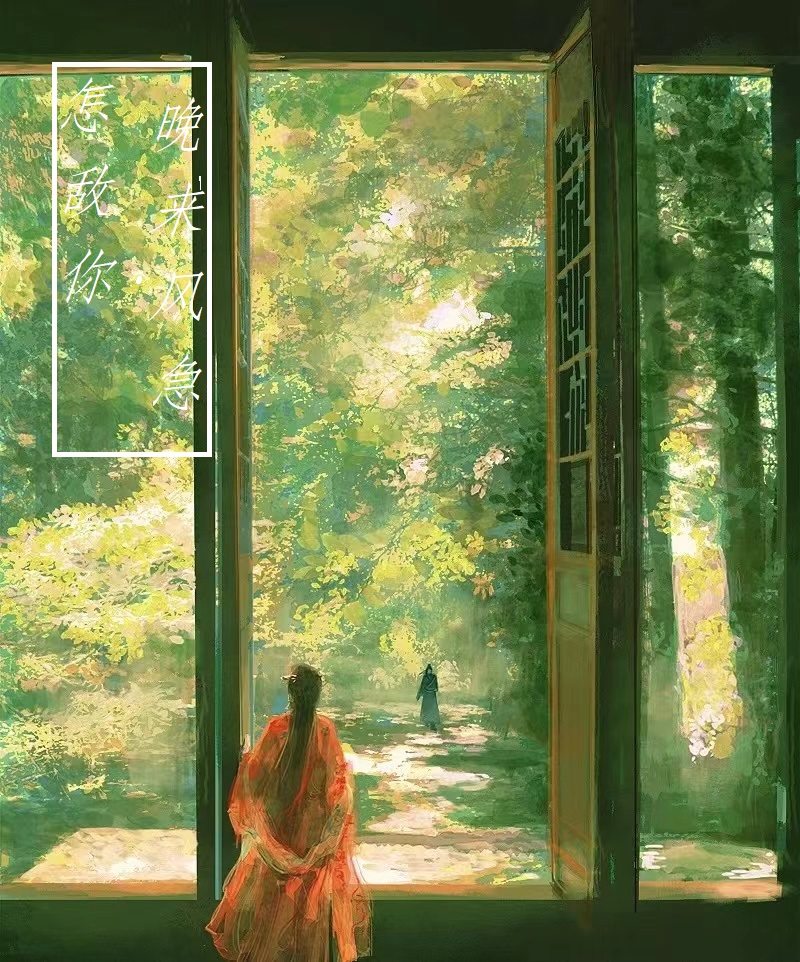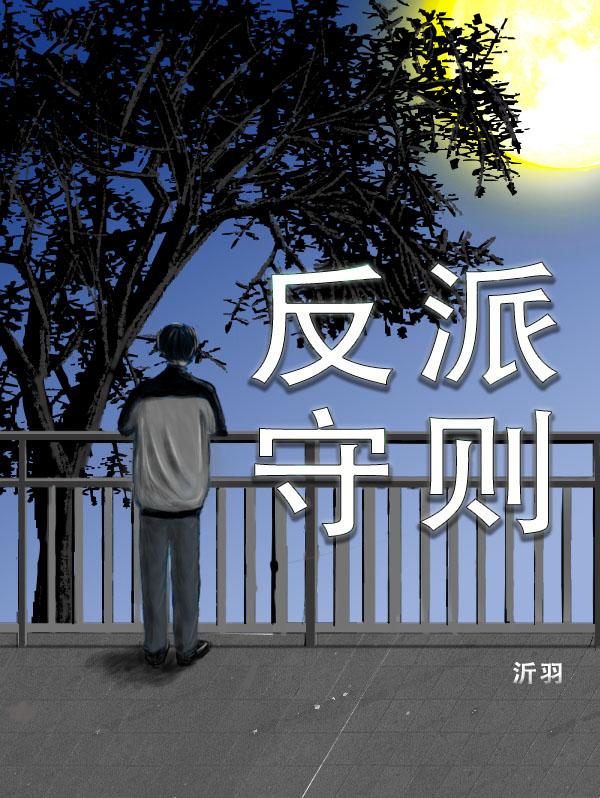十几年前我读中学的时候,离学校不远处有一家军队造纸厂,造纸厂的仓库里堆积着如山的“废书”。“废书”从各处查抄而来,在这里是造纸的原料。我和我的同学如同打洞的小鼠,寻找缝隙把能拖出的书一本本地往外拖。
那些残破的、散发着霉气的书籍按照我们自定的传看条件,鬼祟地在大家手中传递起来:《红字》《金蔷薇》《家》……
对待书我一向是自私的。面对这些“仓库收获”,我没有信守与同学互相传看的诺言,我读过的书便藏起来据为己有。我为它们做各种修补和粘贴,然后就假装没事人儿似的再向同学索要他们手中的书,仿佛根本不曾有过交换的条件。幸而我的同学中有比我大度的,也有对书不以为然的,于是我的手中总有新的获得。
我去农村插队前夕,从熟人家借得一本《第四十一》。在浩瀚的书林之中它至今使我难忘:那个潇洒的红军女战士马柳特卡和眼睛蓝得宛若海水的白军中尉的故事,在我的意识深处开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人生视角,虽然我知道当时它也在被点名批判之列。
我打算把《第四十一》藏起来不再还给那熟人,但我忘记了我面临的对手毕竟不是我那些对书不以为然的同学。这位熟人长者对书竟然比我还认真,不久便开始了他的索书活动,有时竟每日一趟,大有穷追不舍之意。面对我的对手,我不能再装作没事人,也不能轻描淡写地说我丢了他的书。开始我只说没看完,在万般无奈时只好提议用我的一本书与他交换。他拿眼搜索着我那并不富足的小书架,竟然同意了,然后信手抽走了我从造纸厂“拖”出来的《金蔷薇》。我有些后悔,无论如何我是不愿意用《金蔷薇》与他交换的,《金蔷薇》与《第四十一》相比毕竟厚多了。我觉得这已不是交换而是他对我的一种掠夺,我开始懊恼熟人和自己,然而熟人心满意足地走了。
我很快拿出这本昧起来的《第四十一》再次翻看,心情才平静下来,因为它终于光明正大地属于我了。我又窃喜它的分量并不亚于《金蔷薇》,干吗要在乎书的厚薄呢?作者的名字太长我很久才记住,而译者曹靖华先生的名字我却知道,那时我还读过曹老译的盖达尔的一些作品。从书的底页我还了解到这本薄薄的软精装小书是解放后国内发行的第一版:一九五七年,生我的那一年。
“五七”二字颠倒一下就是“七五”,一九七五年我去了农村插队,并且写起小说来。当我发表了一些文字回城之后,常有热情的读者来信鼓励或登门看望。去年冬天就有一位着布鞋、长年在国外任武官的中年军人来到我家,说经常读我的小说,现在是来我所居住的城市锻炼,在驻军某部任代理师长(那个造纸厂就属该驻军),于是就有了见面聊聊的想法。
我请这位师长坐下,觉得他颇具军人风度却又不失温文尔雅,笑容里还有些许朴拙和腼腆。我们的聊天是愉快的,聊了许多我才知道曹靖华先生便是这位师长的父亲,师长名叫曹彭龄,做武官也写散文。
我记得那天是我们所在小区的停电日,几支蜡烛反倒引发了谈天说地的灵感——假如聊天也需要灵感的话。曹彭龄使我又忆起从前我与人换来的那本《第四十一》,在烛光之下我把换书的故事告诉了他。我还告诉他在那样的年代里外国作家的作品通过一位翻译家的再创造,是怎样给了一个青年独特的感受。由此又谈及鲁迅先生曾将翻译家比作为起义的奴隶们偷运军火的人。偷运军火需要胆识和献身的意志。我不能将那个年代的自己比作要起义的奴隶,然而我的确盗用过曹老运给我们的那被封埋的军火。
曹彭龄安静地听着,并不过多地描述曹老为译《第四十一》所蒙受的苦难和各种罪名,更不去炫耀张扬曹老在翻译、介绍苏联文学方面的功绩。他腼腆地笑,只谈中国当代文学和作家。因了对文学的特殊感情,他连哪次出国时碰巧和哪位青年作家同机,都表现出天真的欣喜。告辞时他只希望我把自己的小说集送给他。
我送给曹彭龄一本新近的小说集,他非常仔细地放进他的绿帆布军用挎包——就是随处可见的那种军用挎包。送他下楼后我还发现他是步行而来的,而从他的师部到我家足有四公里吧。我问他出门为什么不要车,他笑笑说他喜欢走路。他背着书包很从容地走进一片黑暗里去了。
不久我收到曹彭龄从北京寄来的一本新版《第四十一》,他在扉页写道:“一九八七年冬在您家做客时,听您说起曾以一册《金蔷薇》与友人悄悄换得一册家父译的《第四十一》,并无比珍爱。我想,家父在天之灵,倘闻此事,也当笑慰的……回京后,觅见家父留存的‘**’后新版,特代他奉赠一册,以谢知音。”扉页下方是曹老的印章。
曹老留在书橱中的这册盖过印章的新版本该不是专为赠予我的吧?是曹老听见了那个久远的换书故事,静等我去索求?我常为此不能自解。对这本译作我到底寻觅了多少年?
我将这新版的《第四十一》看得非常珍贵,更感谢曹彭龄诚挚的心意。原来是他连接了活着的我与谢世的曹老之间的交流,使活着的我对自己从事的事业生出更多的感悟,使辞别我们的文学先辈对他从事过的神圣事业仍然能予以照应。这是一个优秀灵魂对后世的照应。
使文学之树长绿,使本该需要净化的文学更加净化,不浮华颓败,不入误区,使文学更加与时代息息相通,不能没有这照应和感悟。
曹靖华先生辞世一年有余了,《第四十一》的梦绵绵不绝了。
曹彭龄又来信说他正准备去伊拉克。伊拉克——当今地球上的一个热点。与远在伊拉克的武官相比,倒显得我和长眠地下的曹老更近了。
我谨祝武官的“官”运、文运亨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