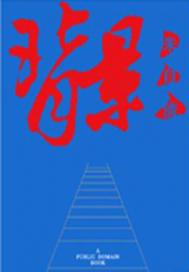不久前,在一个聚会上,我的一位同事又说起了车。一个时期以来,我不止一次或直接、或间接地听这位同事讲起有车的种种好处和开车的种种意义。这位同事已经买了属于自己的车,可他的听众,大多是还没有私家车的群体。有车的人对没车的人讲述买车、开车其实也属正常——难道这不正是一个开口必谈“车事”的时代么?我们的媒体广告,汽车已经在其中占据了多么显赫的比例。谈车早就是一种时尚、一种先锋、一种优越,甚至一种“派”。而我的这位同事,又从自身的职业特点引申开来,说开车不仅可以开阔眼界,提高境界,并且对写小说也会产生积极意义。只可惜,迄今为止,我还没见哪位作家因为买了车开了车而把小说写得比从前更好。倒是这位同事的“车事”,让我想起了自己的“驾车”经历。
从前——三十年前——一九七五年,夏天的时候,我和一些应届高中毕业生作为下乡知识青年,被冀中平原上的一个村子接纳下来,开始了与农民一样的劳动和生活。秋天到来时,我们已经有了些许农事经验,生产队长对我们的劳作能力也基本上心中有数了。一天下午,这位队长派给我一样农活:赶着毛驴车去公社供销社拉化肥。这使我欣喜若狂,与我同行的两个女生也兴奋不已。因为,和大庄稼地里的活计相比,赶驴车又何止是个轻巧活儿呢,那简直是一次奢侈的时髦之旅。生产队的毛驴是头小灰驴,那驴车只是一辆小排子车。驴的秉性比起骡、马,虽然稍显滑头和懒惰,却不暴烈,通常比较好驾驭。就这样,我们赶着小驴车上了路。两个女伴坐进车厢,由我负责驾车。我坐在左侧的车辕上,手持一根细荆条,并不抽打驴的身体,只是在吆喝它时晃几晃以助声威。起步要喊“驾”,调整方向要喊“哦喝”,站住要喊“吁”。差不多,只要学会这三声呼喊,驴车就能够正确地在路上前进。驴车在我简单的吆喝声中不快不慢地走着,车轮下的乡间土路凹凸不平,让我们的身体领略着甘愿承受的轻微颠簸;而夹挤在土路两边的高大的白杨树,在秋风中“嚯啷啷”地响着,威严又安谧。公社离我们的村子五华里,我们都希望这短暂的五里地能够无限延长——因为驾驭的欢乐初次降临到我的头上。我们的虚荣心也叫我们特别乐意被在附近地里干活儿的村人看见,我们乐意看见人们那吃惊的眼神:嗬,女学生也会赶驴车……几乎是一瞬间,公社就到了。我在供销社门前冲小灰驴喊了“吁”,停住车。我的同伴也跳下车,跟我一起进门去买化肥。但我们出门时却发现驴车不见了,原来我忘了把毛驴拴住——或者说我根本就没有拴住它的意识。于是驴自己拉着车扭头就走了,也许它是想独自回家呢,也许它是用这种行为表示对我们的不屑:就你们,连拴车都不知道,还想吆喝我?我们急着在街上找驴车——驴和车可都是生产队的财产啊。幸亏好心的路人帮我们把已经走到出村路上的驴车截了回来,供销社的营业员替我们将化肥装上车,驴车才又开始正确前进。在回村的路上,我们三人不断地指责着那毛驴,指责它的贼头滑脑和不听指挥。驴一声不吭地只顾走路,这就是驴滑头的一面吧,当然它也无法开口用人话与人对答。而驴在想什么就是人永远不知道的了。很久以后我想起我这初次的驾车,仍然能够感受到当初的愉悦,可也觉得我们三个人只顾了享受驾车的奢侈,似乎都缺少了一点驾车人应有的厚道:驴已经在负重前行了,它承载的重量除了化肥,还有我们三个活人,又何必把自己忘记拴驴车的责任推到它身上呢。
我还想到,一九七五年的秋天我驾着驴车的时候,即使用尽想像力,也没去梦想有一天我还可能驾驶汽车。时间再往前推,上世纪六十年代,我的儿童时代,关于汽车的歌谣有这样两句:“小汽车,嘀嘀嘀,里边坐着毛**。”在那个时代的童谣里,小汽车连中国人遥远的梦都不是,在小汽车里坐着的只能是毛**这样的伟人。普通人如我,长大后只坐过另外的一些车:火车、公共汽车、卡车、摩托车、自行车……还有马车、牛车。在乡下的那些日子里,我们到离村很远的地块儿干活儿,收工时累得腰酸腿颤,若能在回村的路上搭一辆村中的牛车,便是莫大的享受了。牛是憨厚温顺的,牛车是缓慢、从容的,车把式的脾气多半也是好的,我们很容易就能蹿上车后尾,坐进车厢,一边歇息着劳累的腿,一边得意着自己的好运气。那是一个不讲速度的时代,虽然火车、飞机都在奔跑和飞翔,但在中国的乡村,牲口车仍然像千百年前一样,是重要的交通和运输工具。一九七五年的中国,自行车也仍然是重要的,是交通工具,更是家庭财产的象征。一则轶事讲的是我的另一位同事,在那个年份里买了一辆产自上海的凤凰二八型锰钢自行车,却舍不得骑,放着又怕受潮,就干脆将它吊在墙上。其老父从乡下来城里看病,每日步行去医院,颇感劳累,请求儿子将墙上的自行车放下来叫他骑一骑,这位儿子便说:“爹呀,您还是骑我吧。”这样,孝顺和实用就都让位于对这份财产的护佑了。在今天,中国人有谁还会奔走相告自己买了一辆自行车,并把自行车挂在墙上呢。
时代在前进,我也竟然有了学习开车的机会。我初次学习驾驶汽车是在一九九○年,那年我在河北山区的一个县里生活、工作了一段时间。一位县政府的司机在拒马河宽阔的河滩里教我开北京吉普“212”。坦率地说,他教得含含混混,我学得糊里糊涂,但我居然把那吉普车开出了河滩,开上了公路。一如我当年驾着驴车,觉得一切都很简单。三天以后我就开着那车去了一趟北京,并邀请县里的几位领导乘坐我开的车。今天想来,这实在是一件于人于己都极不负责的野蛮之事,真是无知者无畏啊!再后来当我真正去学习开车并考取驾照后,才知道当年我开着车不自量力地疯跑着去北京时,我其实并不会开车——虽然,车子在前进,车轮也滚滚。我在还没有资格开车的时候就上了车,不尊重自己,也不尊重他人。
接着,仿佛是忽然之间,中国大地就变成了一个汽车的海洋。不是曾经有人说过,十九世纪超过了以往的一千年么?而中国的近三十年,又一下子超过了以往多少漫长的岁月呢?就在一百年前,一位名叫阿瑟·史密斯的美国传教士,还在《中国乡村生活》一书里写道:即使中国乡村中的士人,也有人坚信西方国家一年有一千天并且天上无论何时都挂着四个月亮。今日的中国的确创造了奇迹。我们用三十年成就了先人千百年不曾想像的事业,千百年不曾有过的现代之梦。
我庆幸我生在今天的中国,我驾驶过驴车,我也有机会去驾驶汽车,甚至我也可以有属于自己的汽车。啊,车轮滚滚,中国人从前在交通上的种种苦难、尴尬和算计好像一股脑儿就被抛在车后了——很多时候我们实在是健忘。还记得许多人当年为了省下三分钱的公共汽车票钱,坚持步行着走向目的地。人问:“您是怎么来的呀?”答曰:“乘11路汽车来的。”就是当年这些快乐而幽默的用“11路汽车”行动的步行者,在今天已经有多少人拥有了自己的私家车啊。我亲眼见过我的一个亲戚,当年住在四合院一个三平方米的小屋里,有一次打开一辆某某牌车子的门,皱着眉头说:后排座空间太窄,空间太窄……更有各种媒体为各种牌子的汽车划分了“阶级”等级:某某车是市民车,某某车是白领车,某某车是小资车,某某车是官员车,某某车是富豪车,某某车是顶级至尊车……以此来引导着购车者的消费和向往,并制造着车与车之间、车主与车主之间微妙而又难耐的矛盾。大排气量的车好像天生可以藐视小排气量的车,而小排气量的车遇见大排气量的车也喜欢故意“别”你那么一下子。当它们的驾驶人共同遭遇自行车和行人时,便又会结成统一战线,异口同声地诅咒自行车和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专门要和开车的人过不去。他们会说:这是对有车族的嫉妒。也许是吧,因为当我不在车上的时候,我也是行人中的一员。当我走在小区安静的路上,我讨厌一辆汽车在我背后突然鸣喇叭——你坐在车里有什么了不起啊,也许我想。我不让路,就叫那车在我的身后磨蹭着走。而当我开车的时候呢,我不是也经常抱怨自行车们的不守规矩么,我也曾在不该鸣喇叭的地段大声地鸣起喇叭,以威吓那个闯红灯的、阻挡了我正常行驶的骑自行车的人。这时我应守的规则上哪儿去了呢?是啊,生活在前进,为什么车上车下的人却变得这么脾气暴躁、火气冲天?还有些时候,我也是乘车的人。我坐在出租车上,发现这个女司机并没有真系安全带,她只是把安全带斜搭在肩上用来应付警察。我说您怎么不系安全带呀?她说“累得慌”。我又发现她变道、转向时从来不打转向灯,就说您怎么不打转向灯啊?她说“累得慌”。她一路和我说着“累得慌”让我心存不悦,虽然在我眼前的车流里,变道不打转向灯的车实在挺多。此时的我作为一个坐车的人,自然又会想到开车人的素质太低什么的。“素质”,这也是近年来我们挂在嘴边的词语了,且多半是用来指责他人的。我还发现为了省油,这女司机常在离路口的红灯还有百米左右时就提前空挡溜车,让我备感不安全。可女司机是个爱说话的人,她向我诉说了很多她的家庭负担和她的累。她的话我大半没记住,只有一个细节很久难忘。她说开车累营养要跟得上,牛奶她是喝不惯的(很多国人的肠胃不能消化牛奶),她每天早晨就喝一包豆奶。她会在每晚睡觉时把豆奶放在自己的肚子上焐热,她的肚子脂肪厚,一夜时间焐热一包豆奶是富富有余的。她早晨喝一包被自己肚子焐热的豆奶,会觉得很精神,也省了家里的煤气。她就那么精神着开她的出租车去了。这时我的不悦似乎又随着女司机的豆奶消失了,这是一个劳动着的人,一个节俭持家的人,我真有资格去和她讨论“素质”吗?如此,莫不是谁都有谁的道理?
那些开着“顶级至尊”车的公民,不是也有落下车窗就冲着大街吐痰的吗?而在我听到的许多关于车的议论中,人们大多是说品牌,说欧洲车和日本车之高低,说钢板的厚度车身的自重,说自动挡和手动挡或“手自一体”,说排气量,说真皮坐椅和天窗,说车内音响和电视,说安全气囊的安全系数……惟独很少听见开车人说开车的规矩,偶尔提及,竟也是说如何用不着去讲那些规矩。
二○○五年的岁末,我是一个乘车的人,我是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我是一个坐“11路”而来的人,我——有时也是一个开车的人。我开着车走在山里一条狭窄的公路上,遭遇着种种不守规则的车。而当我遇到前方的某辆车在变道时打起转向灯时,便立刻觉得自己受到了格外的礼遇。我多么想告诉那辆文明的车:陌生的车啊,我感谢你!在经过一个寂静的村子时,我遇到了一辆拉着柴火的驴车。赶车人不是三十年前的我,而是一个老汉。他跳下车来,紧轰着牲口忙不迭地给我的车让路的样子使我有种受宠若惊之感。这个谦逊的山里老人,他显然还没有对汽车这物件产生敌意,他把它当成这山里的客人了吧——主人应该礼让客人的。在老人积极的避让下,我顺利地通过了狭窄的路。我忽然心生暖意。我在空无一人一车的公路上开着车,一丝不苟地系着安全带,一丝不苟地在该打转向灯时打着转向灯,虽然,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在我的前方和后方并没有车。那我的转向灯是打给谁的呢?我是打给车轮下这清晰可辨的斑马线吧,还有虚线、实线、双黄线……我是打给这抬举着我的条条公路吧,我是打给我本该遵守的规矩吧,我也是打给我手下这跟了我的车吧。当我在空无一人一车的公路上守着自己该守的规矩、限制着自己该受的限制开车时,真正享受到了开车的愉快和自由——没有限制,又哪里来的自由呢?当你接手一辆车的时候,你要给这车什么样的教养,你准备好了吗?我不断地问我。
话题还要回到开头:我的那位有着“谈车瘾”的同事也许犯不上被我讥讽。这同事已年过六十,一个年过六十的中国人能赶上开自己的车,难道不也是一件很可爱的事么?就算是他把自己的买车和开车变成了一个事件而不是一种纯属个人的生活,可中国的朝气,中国人的心气儿,也在其中了。车轮滚滚,势不可当,谁也无法压抑逐渐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各种蓬勃的欲望。问题是,当车轮滚滚向前时,我们该没有丢下人类那些本该具备的种种德性吧?我们有目测前方的雄心,也该有回望心灵的能力。
车轮滚滚,而人海更是茫茫。当车在人的生活中变得那么重要时,每一个人也都更加重要了,即便你还是乘着“11路”来往于人海茫茫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