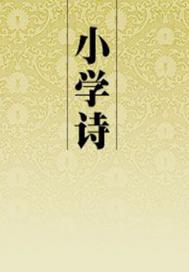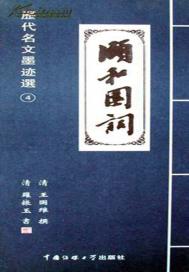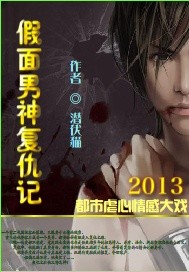一直处于战争阴云下的伊拉克,古迹的保存情况如何?我很想去看一下他们的国家博物馆。
博物馆在地图上标得很醒目,走去一看,只见两个持枪士兵把门,门内荒草离离。上前打听,说是九年来从未开放过。所有展品为防轰炸,都曾经装箱转移,现在为了迎接新世纪,准备重新开放,已整理出一个厅。能否让我们成为首批参观者,必须等一位负责人到来后再决定。
于是,我们就坐在路边的石阶上耐心等待。
院中前方有一尊塑像,好像是一个历史人物,但荒草太深我走不过去,只能猜测他也许是汉谟拉比(Hammurape),也许是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我想不应该是第三个人。这么一想,我站起身来,趁着等待的闲暇搜罗一下自己心中有关两河文明的片断印象。
现在国际学术界都知道的“楔形文字”,证明早在六千多年前,两河下游已有令人瞩目的古文明。但是,大家在习惯上还是愿意再把时间往后推两千多年,从巴比伦王国说起。
不管怎么说,两河文明比中华文明年长很多。太遥远的事我们也顾不过来了,不如取其一段,把两河文明精缩为巴比伦文明。
范畴一精缩,我也就有可能捕捉心中对巴比伦文明最粗浅的印象了。约略是三个方面:一部早熟的法典,一种骇人的残暴,一些奇异的建筑。
先说法典。谁都知道我是在说《汉谟拉比法典》。我猜测博物馆院子里雕像的第一人选为汉谟拉比,正是由于他早在四千多年前就制定了这部完整的法典。法典刻在一个扁圆石柱上,现藏法国巴黎卢浮宫。卢浮宫的藏品实在太多,我去两次都没有绕到展出法典的大厅。倒是读过一些法律史方面的学术著述,依稀知道这部法典包含近三百项条款,在阶级歧视的前提下制定了“以牙还牙”的同等量复仇法,保障了商业利益和社会福利。重要的是,这个法典还在结语中规定了法律的使命。那就是保证社会安定、政治清明、强不凌弱、各得其所,以正义的名义审判案件,使受害者获得公正与平静。想想吧,早在四千多年前就如此明确地触摸到了人类需要法律的最根本理由,真是令人钦佩和吃惊。联想到这片最早进入法制文明的土地,四千年后仍然无法阻止明目张胆的非法行为,真不知脾气急躁的汉谟拉比会不会饮泣九泉。
顺着说说残暴。巴比伦文明一直裹卷着十倍于自身的残暴,许多历史材料不忍卒读。我手边有一份材料记录了亚述一个国王的自述,最没有血腥气了,但读起来仍然让人毛骨悚然:
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我摧毁了埃兰全境。
我在那里的土壤里撒上了盐和荆棘的种子,然后把男女老幼和牲畜全部带走。于是,那里转眼间不再有人声欢笑,只有野兽和荒草。
这里所说的“带走”的人,少数为奴,多数被杀。但我觉得最恐怖的举动还是在土地上撒上盐和荆棘的种子。这是阻止文明再现,而这位国王叙述得那么平静,那么自得。我认为,这种残暴传统,倒是在这片土地上继承下来了,实在让人叹息。
再说说建筑。建筑,在巴比伦王国的时候应该已经十分了得,但缺少详细描述,而到了后巴比伦王国的尼布甲尼撒时代,巴比伦城的建筑肯定是世界一流。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一百多年后考察巴比伦时还亲睹其宏伟,并写入他的著作。建筑中最著名的似乎是那个“空中花园”,用柱群搭建起多层园圃结构,配以精巧的灌溉抽水系统,很早就被称为世界级景观。但是,我对这类建筑兴趣不大,觉得技巧过甚,奢侈过度,总非文明演进的正常形态。
当然,巴比伦文明还向人类贡献了天文学、数学、医药学方面的早期成果,无法一一细述。可以确证的是,法典老了,血泊干了,花园坍了。此后两千多年,波斯人来了,马其顿人来了,阿拉伯人来了,蒙古人来了,土耳其人来了……谁都想在这里重新开创自己的历史,因此都不把巴比伦文明当一回事。只有一些偶然的遗落物,供后世的考古学家拿着放大镜细细寻找。
想到这里,博物馆的负责人来了,允许我们参观。我们进人的是刚布置完毕的伊斯兰厅,对两河文明来说实在太晚了一点。一眼看去,所展物件稀少而简陋,我走了一圈就离开了。一路上看到走廊边很多房间在开会,却没有在新世纪来临之际开馆的确实迹象。
我很难过,心想,这家博物馆究竟收藏了些什么?分明是一屋的空缺,一屋的悲怆,一屋的遗忘。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巴格达,夜宿Rasheed旅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