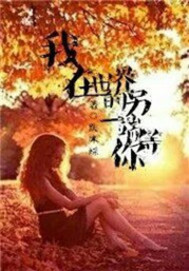刘妈拿了斗篷披在她身上,絮絮叨叨着,“小姐怎么连个外衣也不穿,即使就几步路。但这夜里寒气重,没得回头又生了病。”
沈蔷薇也不说话,缓步走到了偏厅。一路直接去了卧室,里面燃着茉莉香,袅袅缭绕至鼻端,这房里各处装饰的仍如新房一般。绯红的床帐子上绣着百花齐放图,灿若云霞似的一团一簇。
窗棂上还贴着双喜字,里头有一对并头鸳鸯,剪裁的活灵活现,只是孤零零的映在窗子前,好似连一丝喜色也没有。
方语嫣靠坐在床上,正与二姨太热络的说着话。
见了她进来,就蹙起眉头,问:“你来做什么?”
沈蔷薇不紧不慢的坐到了床边,笑意盈盈的看着她,“这不是听说少奶奶病了么,我过来瞧瞧。”
她转顾一旁的孙博谦,问:“孙医生,少奶奶没事吧?”
那孙博谦刚刚为方语嫣检查过,此刻正准备提了药箱出去,闻言就说:“少奶奶身体没有大碍,就是有些气血不足,多加调养就是。”
沈蔷薇便“哦”了一声,便听二姨太和颜悦色的说:“今儿我也是糊涂了,偏信了那小丫鬟的话,只当是蔷薇与你闹不和睦,撺掇着丫鬟给你下药,这才着了急。好在只是虚惊一场,你没事就好。”
方语嫣瞪了沈蔷薇一眼,阴阳怪气的说:“我就琢磨着这事儿不简单,好端端的我怎么就病了。”说过这一句,眼见着孙博谦告辞准备离开,就问:“孙医生,我身体确实没事么?”
孙博谦便点一点头,“少奶奶只需要静心调养就好。”
待到他离开,沈蔷薇方说:“这下少奶奶可以放心了?”
方语嫣却不搭理她,转顾一旁的喜儿,问:“你说云清在我菜盘子里下药,结果一检查却是珍珠粉?”
喜儿正想着别的事,恍然一听,忙就点点头,说:“这事说来奇怪,她如果真存着心要陷害姨奶奶,又何必拿着珍珠粉做手脚?”
沈蔷薇淡淡说:“这原本就是栽赃陷害,谁在乎东西是什么?”
她看向二姨太,“我是不知道她打的什么鬼主意,好在这次我沉冤得雪,只是她毕竟是我的丫鬟,还请二姨娘能够从轻发落她。”
二姨太原本只是过来走个过场,眼见着她们二人还是一副互相对立的阵仗, 再看那方语嫣,依旧是骄矜自傲的样子,不由就放下心来。
她起了身,说:“耽误的太久,我也该回去了。”
沈蔷薇就福了福身子,眼见着二姨太一行人离开,室内的丫鬟也跟着悄没声的走了出去。
沈蔷薇说:“这出戏多亏了少奶奶,不然我还逮不住云清。”
方语嫣骄恣的笑了笑,“事儿也完了,就别再说这些客套的话了。”
沈蔷薇见她眉心微皱,就说:“想必少奶奶也通过这一件事认清了二姨太的嘴脸,日后她少不得还会利用你,少奶奶可别忘了自己的立场。”
“行了,不用你瞎操心。”方语嫣说着,就不耐的挥了挥手。沈蔷薇想着她刚才故意在二姨太面前配合着自己演戏,不由得一笑,就说:“我走了,你休息吧。”
眼见着年关将至,督军府中诸事繁杂,这两天又下了大雪,整个金陵被风雪侵袭,搅得天寒地冻。又是国难当头的时期,无疑是在冰天雪地中覆了层寒霜。
自开战至今已有月余,金陵虽远在千里,依旧是人心惶惶,关于战况的报纸铺天盖地,国内舆论更是褒贬不一。各高校阻止学生活动,对扶桑洋行烧砸掠夺,大喊旗号,示威游行。
这次苏徽意去前线,特意将自己的近身卫戍队伍留在了督军府保护沈蔷薇,前线战事不断,每隔几日,卫戍队长范子承便会将消息汇报给沈蔷薇。
一连着数日,关于战局竟是好坏参半,因着地势与天气的缘故,两方对峙在明阳,苦战几日,彼此伤亡各半,一同陷入了僵局。
沈蔷薇自然悬着心,她整日整夜的睡不好觉,倒好似一闭上眼就能看见炮火连天,尸遍满地。
因着连日的忧心,人也憔悴下来。这日早上,沈蔷薇还没有起床,丫鬟来报说卫戍队长范子承来了,沈蔷薇连忙换过衣服,只觉得心要跳到嗓子眼,一路急行出去,见了范子承忙问:“有什么消息?”
范子承是苏徽意的心腹,谈吐举止与他如出一辙,当即说:“二夫人请放心,七少昨晚已经突围明阳,扶桑招架不住,弃了明阳至陈州一线,前线大捷,七少近日就会回来。”
沈蔷薇这才放了心,坐在沙发上好半天才对范子承道了谢。范子承客气几句,就出了屋子。
待到吃完早饭,刘妈就撺掇着沈蔷薇出去逛逛,沈蔷薇无法,只得带着小竹出了院子,两个人随意转了转,小竹不敢掉以轻心,时刻扶着沈蔷薇,待越过抄手游廊,就听见不远处传来吵嚷的声音。
小竹顺着方向看了一眼,说:“应该是前面的院子传过来的。”
沈蔷薇记得前面的院子并无人住,就问:“那里不是空着的么?”
小竹支支吾吾的说:“之前是没人的,赶上大帅要娶七姨太过门,将这院子给七姨太了。”
沈蔷薇想着韩莞尔即将进门,心没由来的一沉,说:“现在前方战事吃紧,金陵仍旧是歌舞升平的,战士们在前线流血,这些高官权贵却挤破头的过府送礼,恨不得把门槛都踏平了!这个时候娶姨太太怎可太过招摇?到底是舒服日子过得太久了,连人都愚昧了。”
小竹见状,忙悄声说:“姨奶奶,可别再说了,小心隔墙有耳!”
沈蔷薇也无心再提,遥望远处的院子,就见影影绰绰的人围在一起,并不像在打扫,也不知出了什么事。
她正犹疑着要不要过去看看,就见正有丫鬟慌张的自月亮门跑出来,倒像是极度害怕似的,见了她又是吓了一跳,但好在规矩没有乱,草草的行了一礼,磕磕巴巴的说:“给姨奶奶请安了,这会儿我有要事要禀告,先行告退了。”
沈蔷薇见她行色匆匆,神情慌乱,显见是有什么要事。她也无从细问,就恩了一声,那丫鬟得了令,才快速的跑开。
她不知这样的青天白日会出多大的事,只是心中隐有不安,并未上前去一探究竟。
匆匆看了两眼,愈发的心慌,倒不妨自月亮门里涌出一堆穿灰服的听差,他们手里抬着个担架,上面隐约是躺着个人,被白布盖住全身,也不知是男是女,只有一条手臂斜斜的晃荡着,无端的让人头皮发麻。
因着离得不算近,沈蔷薇没有瞧清楚,但乍一细看这景象,也知道是死了人。她只觉得胃里发酸,当即就止不住的作呕。
小竹见状忙扶着她往回走,这一路自是安静无声的。待到回了院子,沈蔷薇已是面色惨白,她倒不是害怕,只是这样的事被她撞见,心中难免犯嘀咕。
刘妈自小竹那里得知了前因后果,不由的叹起来,说:“好好的一个督军府,出的都是些什么事啊,这又不知道牵出多少桩案子来。”她虽念叨了一句,却怕沈蔷薇被吓到,嘱咐院子里的丫鬟不准乱传话。
谁承想临到了外间,二姨太的丫鬟便来了偏房,见了沈蔷薇就说:“姨奶奶,头前死在七姨太院子里的丫鬟是云清,我们二姨太原只是教训了她一顿,便打发她走了。没想到她自己心里想不开,竟就投了井。”
那丫鬟偷眼去看沈蔷薇,见她端坐在沙发上,闻言却是诧异的瞪大了眼睛,小丫鬟就继续说:“依着二太太的性子,这件事原是不必告诉姨奶奶的,但云清毕竟是你的丫鬟,她就这么死了,怎么样都该知会您一声。”
沈蔷薇的脸色极是惨白,像是害怕抑或惊异,只是沉默着不出声。最后还是刘妈应了一声,那丫鬟才离开了。
刘妈转顾沈蔷薇,见她依然沉默着不说话,那脸色如同霜雪一般,只当她是吓得厉害。不由说:“小姐,别想了,哎,这个人有个人的缘法,这就是她的命。”
沈蔷薇目光没什么焦距的看着前方,轻声说:“那时候我就知道云清多半活不了,她做了太多见不得光的事,二姨太不会留她。”
刘妈也知道这深宅旧院多的是这些下作手段,那二姨太是个笑面虎一般的人,能这这督军府里屹立不倒,必是手段狠辣。
她正想着,却见沈蔷薇笑了笑,“二姨太这是在拿云清的死敲打我呢,到了这一步,我也没有必要再忍气吞声。”
刘妈见她极是平静的坐在那,那秀美的脸上褪去往昔稚嫩,眉宇之间更是透出从容不迫来。秀美的脸上映着暖黄色的光晕,这样去看,她的眉梢眼角不见丝毫明媚,仿若寒霜覆雪似的,只余下冷漠来。
外头的冷风呼啦啦飞卷,在室内听得并不真切,便如雨声一般,打的门窗沙沙作响。这室内的一切都是幽静中透着一丝死气的,沈蔷薇靠在沙发上,缓缓合上眼,夜幕便更加的幽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