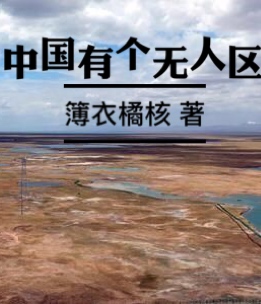几人知道这是存了威胁之意,他们如今被卸了军权,眼下和家人又要受制于人,自是不敢有半分怨言,只得强颜欢笑着。
苏徽意招手唤来林宁,吩咐道:“送各位司令回去休息。”
林宁应了声是,引了几人出去。苏青阳这才坐到了椅子上,拿起桌上的青瓷茶杯把玩起来,淡淡的说:“七弟这招好厉害,既扫清了内患,又稳固了地位,真是一箭双雕。”
苏徽意见他面色惨白,虽说没什么表情,眉宇间却透着几分凄然。就说:“与扶桑这一战,还要仰仗二哥。”
苏青阳闻言便将手中的茶杯放下,点点头一派心不在焉的样子,“好说,我什么时候动身?”
苏徽意勾唇笑笑,“来之前二哥不是已经问过了父亲?”他顿了顿,“父亲虽说年岁渐老,但却依然老谋深算。”他说完,便起身走了出去。
直到了走廊,他才吩咐林宁,“派两个师的兵力往明阳去,再准备专列,送老二过去。”
林宁神色一变,紧随其后说:“七少如此做,不是放虎归山么?”
苏徽意阔步朝前走,军靴踩在地板上杂沓有声,他淡淡的说:“放虎归山也不全无好处,现在南地是内忧外患,他想要造反,也得先扫清了屏障。”
转顾窗外,就见雨幕轻飘飘的,朝阳喷薄而出,染的半边天都是夕阳残血一般。直到了办公室门口,便见侍从队长潘青延等在门口,面上有几分焦灼踌躇,他当即立正行礼,说:“七少,才刚收到密电,夫人现在在三公子那里。”
苏徽意原本正想着战局的事,闻言不由的一怔,转脸看向他,缓了缓才问:“她在老三那里?”
潘青延慎重的点点头,“三公子的密电里说,他会先安置夫人,请七少尽快去接人……”他说完,又说:“七少,现今稳住南地时局要紧,这个时候您不宜往前线去,不如就派我过去。”
他还没有说完,苏徽意已经抬手示意,淡淡的说:“我亲自过去。”他回过头来,“去准备。”
林宁想着眼下时局,不由得与潘青延对视一眼,心内却清楚七少的决定从来不容置喙,便硬着头皮答应了一声。
苏徽意进了办公室,这会儿脑中纷纷杂杂着,便坐到了沙发上,只是疲惫渐消,抱着臂坐了半晌,才慢慢的点了根烟,檐下的雨声渐渐地低微下去,窗子前却氤氲一片,升腾起茫茫的雾气,地上却透着薄薄的暖光,原来太阳逐渐的亮起来,只是隔着雾霭沉沉,恍然间看着,仿若一块晶莹的玉石沉在了潭水里,迷蒙一片。
他默默地抽着烟,那青白的烟雾笼着他,却好似是深深的桎梏,将他捆绑在其中。他从来都是冷静的,可到了这种时候,心中却乱成了一团,剪不断理还乱似的。
落地钟在一摆一摆着,搅得他心跳都快了起来,可是到了此时,他却不能平静的度过每一秒,不由将烟扔在地上,阔步走了出去。
一路直到了楼下,便见林宁走了过来,面上神色略显仓皇,“七少,昌州一线已经停了火车,专列只能到江南。”他顿了顿,“那一代现在都是平家军的人……”
苏徽意脚步不停地朝外走,闻言只淡淡恩了一声,“去安排吧。”
傍晚时分,西风关的天便渐渐地暗下去,这里是南北交织的关口,常年风沙不断,赶上这样的夏日,大地便燥的厉害。远远近近的,只能看到漫漫黄沙笼着小镇,方圆几十里空旷一片,与那一头浩浩荡荡的江水隔着山岳,便好似隔着两个世界。
因着苏子虞带着行军,便将沈蔷薇她们安置在了镇上的民居里,院子不大,好在十分干净,苏子虞又在镇中找了大夫和几个婆子照顾沈蔷薇,她休息了这两日,倒觉得颇安稳,只是肚子渐大,让她行动十分不便。
阮红玉一改往日的矫情,将沈蔷薇照顾的无微不至。两个人经历了一遭,倒变得无话不说。 沈蔷薇一直都悬着心,她想着如若苏子虞告诉了苏徽意,只怕他会不管不顾的来找她,可现在时局混乱,他身为总司令,又有多少双眼睛盯在他身上?
只怕暗地里又有多少人要暗害他,外患如此,身边的人万一也被收买,岂不是腹背受敌?她越想越心慌,又担忧着他的伤势,更是寝食难安。
直到了晚上,苏子虞便来了院子,原本阮红玉正陪着沈蔷薇,但见他神情严肃,自知待在这里不方便,就寻了个理由回了房间。
沈蔷薇正巧有问题要问他,此刻见了他就说:“三公子,你实话告诉我,你把我留在这里,是存了什么心思?”
苏子虞好似知道她的想法一般,笑了笑才说:“你怕什么?如今我与卢御平分道扬镳,不是联军司令了,你还担心我会拿你威胁老七?”
沈蔷薇不妨他大大方方的说出来,只是不知真假,就说:“南地打的不可开交,这个时候如果他到了这里,只怕有心人又会暗害他,不如你将我送回去。”
苏子虞闻言当即笑起来,“你以为老七是什么人?你未免也担心的太过。”他坐到一旁的座椅上,抬眼见她面上神色难辨,就说:“我让老七来接你,是因为我并没有把握可以送你回去。”
沈蔷薇垂下眼,想了想便默认了他的话,现在战事频起,谁能担保这个万一呢?她说:“三公子,那时候我只当你们兄弟阋墙,可没想到眼下这种局势,你待七少倒是坦坦荡荡。”
苏子虞不在意的笑了笑,“那时候我就说过,我谋的不是江山,老七与我意愿相悖,我自然不会做他的绊脚石。”
“你说的不是实话。”沈蔷薇忽而抬起眼,定定的看着他,“那时候先夫人的祭礼,我听老嬷嬷说起过,你和七少幼时的事,现在想想却不简单。如果你们是异母兄弟,大可以像对待老二一样。”
苏子虞没有说话,而是摩挲着手指上的翠玉戒指,隔了半晌才说:“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父亲****,不但家中娶了好几房姨太太,外头也是花天酒地。那时候先夫人已经有了老大这个嫡子,只是他天性疏懒,成日里只喜欢写文弄墨,于谋权上并不上心。而我和老二都是庶子,即便再怎么努力,终是无用。”
他缓了缓,继续平平淡淡的说:“大夫人知道我和老二心机深沉,自幼时便防着我们,生怕我们抢走老大的东西,可凭她一个人如何,也挡不住父亲将一个又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娶回府,她为了稳固家中的地位,便将目光转到了刚怀孕的母亲身上,那时候家里请了位老先生,断定我母亲肚子里怀的是个男胎,夫人便以我母家人性命相要挟,让母亲生下孩子后过继给她。”
“我母亲天性柔和,她为了保护我们,选择了妥协,老七出生后,便过继给了夫人。”
他忍不住冷笑一声,“那时候夫人当真风光,可惜好景不长,没活几年就死了,老七倒是争气,自小就聪慧,父亲爱惜他,即便先夫人去世,依然认他做嫡子,并不许下人告诉他。”
他叹了一声,“仔细想想,他也挺可怜的。二姨太的丫鬟有次将他的身份告诉了他,他倒也沉得住气,只当自己是个嫡子,那时候我怪他冷情薄幸,连自己的亲生母亲都不认,直到了母亲离世,我与他打了一架,才知道他心事挺重的,诸事也看的分明。”
他忽而笑了笑,抬眼看着她,又说:“那时候他年纪尚小,这些事说过便忘了,过了这些许年,从来也没有提过,我想他大抵是忘了吧。”
沈蔷薇这会儿倒像是十分笃定似的,“他没忘,他一定没忘。”她这样说着,忍不住眼眶湿润,“他这个人表面上看着是一回事,心里却是另一回事,我知道他一定没忘。”
苏子虞却不说话了,外头的天愈发的黑沉下去,风沙漫漫,打的旧窗棂呼啦作响。屋里头点了羊油灯,映照出一小片的光晕,可四下里却是暗沉沉的,此刻两人默默无言,时间便显得悠长。
隔了半晌,苏子虞才说:“这些陈年旧事,记住或者忘了有什么重要?左右我不是个好哥哥,这些事儿我忘了就是。”
他忽而轻声笑了笑,“我先走了,你休息吧。”
出去的时候,就见夜幕之上皎月低垂,圆圆的缀在屋檐上头,隐隐的,可见树木枝繁叶茂,任凭冷月幽幽,风沙席卷,夏日的蝉鸣依旧,夜风夹杂着热气,直直的覆上来,倒搅得人呼吸发紧。
可无论怎样的天气,人总要一步一步走出去。这样的情景,即便冷漠如他,也不禁轻轻叹了一声,才快步走出了院子。
沈蔷薇目送他离开,转眼见阮红玉自房中走了出来,她穿着一身素淡的旗袍,朝门口望了望,见寻不到苏子虞的身影,才对着沈蔷薇似叹似伤的说:“其实三公子才是最重情重义的那一个,等日子久了,你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