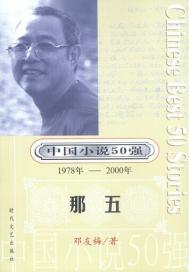椿岗是个狭长形的小镇,夹在濑户内海和一片长满翠竹和杉树的小山之间。它的南端有块凸出的角地,类似半岛,“椿岗曹达株式会社”就建在这半岛上。一连四个长筒形石灰炉,十几只涂了保护色的烟囱,把这秀丽的市镇弄得乌烟瘴气,站在山顶往下看,群山似翡翠,内海如水晶,中间却乱七八糟扔着一堆冒烟起火的垃圾。
早晨六时,随着汽笛声,灰色的、褴褛的人群,躬着腰,夹着饭盒,急急忙忙的一边回答着小学生们的问候,一面挤进黑色厂门,集中到神社前广场上。作广播体操,作“东方遥拜”,背诵“社训”,每逢八日还要低下头来听读“宣战诏书”。然后顺着厂内满是管道、电缆的小路分散到各自的车间去。
“药品部”在最南端,临海并立着两个车间,一个生产“硝酸加里”,一个生产“碳酸镁”。华工们给它起个外号叫“水火二狱”:“硝酸加里”车间除去水池就是水槽,一天的大部分时间不是用胶皮水管浇水抽水,就是用铁锹铁耙在结晶池内搅水,两只脚泡得脱皮,浮肿;“碳酸镁”车间的中心是两座几十米长的隧道式干燥炉和一架粉碎机,华工们推着一车车碳酸镁结晶块入炉出炉,在炉壁的烧烤和热风吹灼下个个皮肤干缩,满脸皱纹,十几二十岁的人就象六七十岁的老头子。碳酸镁粉灰堵塞住每一个毛孔,任凭你用高压空气吹,用热水泡,拿肥皂搓,都清除不净。人们把毛巾叠作三叠,连鼻子带眼都蒙上。还是成天咳嗽,吐出象牙膏似的白色粘块。
“碳酸镁”华工班长是张巨,“硝酸加里”的班长是宋玉珂。
宋玉坷三十来岁,为人斯文、老实。他总收拾得整洁利落,脸上从不胡子拉茬。衣服补得平平正正。在一群邋里邋遢的华工中,他格外透着精神。他对于华工之间宗派纠纷,从不参与,如果请他调解,他却一定尽心。他不顶撞日本舍长、工头,不犯纪律,所以从没挨过打。可是他也不拍日本人马屁,不检举华工中的任何事情,因而也不招中国人骂。人们讲笑话,扯乱弹,他跟着捡笑,却不当主讲。因为他长得漂亮,跟日本女工们一块干活,她们都跟他说笑,他一律应酬,可从不认真。他跟谁也不亲,跟谁也不远。如果说有例外,那就是对虎子处处关照。但这不会引起人们非议。虎子年岁小,他以大哥身分关照他,人们为此对老宋挺敬重。
华工们是日本人用抓、骗、招、买各种办法,从各个地点弄来的。抓的人只管抓,卖的人只管卖,转到劳工协会手中按人头一过数就人钱两清。对于他们的祖宗三代,家庭出身并不过问。劳工协会把这些人送到门司。洗澡消毒。光着屁股排队,这一拨儿上秋田,那一队去山口……各有日本头人领走,与送的人再无关联。谁从哪里来,过去干什么,都不用打听。到了工矿,发个表填上姓名,张三李四,籍贯年龄,随你一写。反正是奴隶,有个名字用来招呼驱使,干得好给饭吃,干不好打鞭子,管那些闲白何用?所以华工们互相之间,也不知道各自的真正面目。比如,人们只知宋玉珂是济南的教员,虎子是乡下的羊倌,谁也不知早在来日本之前他们就有交情。
虎子被抓的当天,被关在火车站外关帝庙里。庙不大,抓来的人不断往里送,不大工夫就挤得坐不开了。日本鬼子就叫大伙都站起来,被抓的人估计不是要枪毙,就是抓劳工。哭爹叫娘的也有,呼天喊地的也有,虎子也呜呜的哭。紧挨他站着的一个人就说:“抓都抓来了,哭顶个啥用。白叫鬼子听了高兴!”
虎子说:“你说的轻巧哩,我打了几天摆子,今天一天没吃饭,这腿软的棉花似的,光打颤站不住咧,我要象你这么壮实,谁哭谁是个孬种。”
那人哦了一声,伸手抱住了虎子说:“这样你好受些不?”
虎子觉得好受多了,可是眼泪更止不住了,不过他没再出声。半夜上了火车,他还挨着这人,闷罐车里比关帝庙还挤,也比关帝庙还黑,虎子就始终没看清这人的模样。天亮后到青岛的大港站打开车门放他们出来,虎子这才看清他,不由得叫了声:
“妈呀,你不是……”
宋玉珂捏了一下他的手。小声说:“千万记住,咱们谁也不认识谁。”
虎子会意,把话咽回去了,并且从此当着人连话都不再跟宋玉珂说,可是心里却纳闷:“歌上都唱着,‘武工队员个个赛猛虎’,这只猛虎怎么落进笼子里来了呢?”——这就是那晚在油房里跟“鬼子同志”说话的人。
上了船,看管的松了,宋玉珂才告诉他。武工队以为日本鬼子抓人,要在附近修据点,特派他打进来弄情报,谁知一来就走不脱了。宋玉珂两手一拍,说:“坏了醋了不是!命里该咱去留留洋!”
宋玉珂原来是个教员,日本军队把小学校烧了,他一跺脚参加了游击队。还当文化教员。他正在申请入党。党支部书记对他说:“首先要在思想上入党,不论人前人后,集体行动还是单独作战,都要以党员标准自觉的要求自己。”这话给他提出个作人的基本原则。给了他在困难时的精神支柱。他想:越是远离祖国、远离组织,越要紧记这句话,不然人在高压下,会蜕化成低等动物。可是他参加革命不太久,马列主义没念过一本半,共产党员和好人的标准他分不大清,他常常只是在认真的作好人。
到椿岗不久,他就与虎子订了两条秘约:一,任何情况下都不暴露他的真正身分;二,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忘了自己是从根据地来的,受过共产党教育。华工里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条件不允许作宣传教育工作,可以不作,但总要洁身自好,保持清白。
宋玉珂串通人给张巨他们留了饭,张巨觉得受恩不报非君子,这天早上上班,他把那一慰问袋大米带进了厂。对宋玉珂说:“哥们儿,今天中午饭咱们凑到一块吃啊,我请客。”
张巨他们走进车间,手中的小物件还没放下,大牙就拉电铃通知出炉了。
这大牙有三十多岁,体格很壮,只是少了半条腿。是台儿庄战役叫中国兵拿大刀片斫下去的。这件事他记了仇,有机会就骂中国人不好。华工们自然也就对他没好脸色。骂他是小山崎。其实他跟山崎不一样,他只是咋咋呼呼,真动手打人的事并不多,山崎有一套系统的军国主义思想,民族压迫观念。大牙没有这些,他就是为自己的腿鸣不平。其实大牙生活很苦,衣不蔽体,吃的东西也比华工好点有限,他一条腿不能干重活,厂方并不把他当头蒜。
这车间另一个日本工人姓村冈,大约二十岁,满结实强壮,可不知有什么门道竟没去服兵役。他没有中国人日本人这个界线,跟华工们既交朋友也打吵子,好起来抱着你膀子走,一翻脸就拉架子摔跤。可是挨了打也不告状,你今天揍了他,明天他又跟你开玩笑,从不记恨。
他最讨厌韩有福,一见面就把大拇指夹在食指和中指缝里朝韩有福鼻子上伸。他见韩有福跟别人一起干活总偷懒耍滑,就故意让陆虎子和他推卸一台车,并对虎子说:“你小孩,少干一点可以,叫他多干!”
近来煤炭供应不足。电压忽高忽低,炉温也不稳定。应当上一炉出的半成品没有按时出来,就两炉挤在一起出来。象一间小房大小的车,一次就出十二车。每车有一百多板干燥了的碳酸镁硬块。这上千板的干料就靠七个华工和一个日本工人由炉内推出,运往粉碎室,把板抽出,把料卸掉。车推进过滤室,把板码成垛、再装上湿料推回炉内,热风滚滚,粉尘飞扬,人们真象在“神曲”所描述的“旋风地狱”里受刑罚。大牙抡着根铁锹把,不断的叫喊:
“快一点,快一点!想挨棍子吗?”
连村冈都忿而不平,他说:“你们中国人该倒霉,为什么当初不把他另一条腿斫断?”
虎子刚还完韩有福五碗赌账,韩有福又撺掇他玩“十点半。”虎子一时心活,竟又输了五碗,为此决心一口气还上账、至死不再赌博。恰好配给烟草,他把一包烟和一本卷烟纸给韩有福顶了三碗饭,昨晚今早一口饭没吃,把账还清了,这时身上就发软,卸一板料,要喘几口气。韩有福抱怨说:“跟你干活真倒了霉,得替你干一半!”
“你放屁,我今天肚子空,多少慢点,平时比你少干了吗?”
华工们就说韩有福:“都是中国人,他个孩子家,饭又让你哄去吃了,比你少干点又算什么?”
“饭是我赢的,我输了不也一样给他吗?”
这时有人轻轻打了口哨。通知“勤劳部”的人到了。刹时鸦雀无声,只听乒乒乓乓卸车的声音,满屋子都被白色粉尘弥漫住,眼都睁不开。“勤劳部”是军方派驻厂内监视工人的部门,有权拘留、拷打工人。他们不时的骑上车到华工们干活地方巡视。韩有福凭直觉那人就在他身后转悠,就把上衣一脱,一次两板两板的往下卸料,一会儿工夫浑身上下就挂满了**,象个长满白毛的猴子。“勤劳部”的巡查员并没理他,拍了一下虎子的肩膀,把他叫到了屋外去。
“小孩,你每天新闻都看吗?”
“看,可是我不认字,光看画。”
“唔,东京被轰炸的照片看见了吧?”
“看见了。”
“怎么想?高兴呢?不高兴呢?”
“我想**可别掉在我头上!”
“你听他们说什么话了?”
“谁?”
“中国人,你的伙伴们。”
“他们说饿的慌,能找到吃的才好!”
“不是,说轰炸的事!”
“没听见!”
“你说蒋介石好,汪精卫好,还是共产党好?”
“兴亚寮没有叫这名字的人呀?是日本人吗?我不认识。”
不,共产党不是一个人……
“先生,我听不懂这么复杂的日语。”
巡查捡起一块碳酸镁,在水泥地上写了“共产党,毛**几个字。嗯?”
“我不认字,你画个图吧!他们什么样?”
巡查想了半天,在地上画了个斧头镰刀图案。
“明白?”
虎子点头说:“明白!这是干燥车的挂勾对吧?这样的不好使,方头的好使……”
“混蛋,滚,猪!臭狗屎!”巡查踢了虎子屁股一脚。把他撵走又把韩有福喊了过来。递给他一支烟:“韩,你干活很好。”用打火机把烟给他点着了。
“谢谢先生。”韩有福琢磨他要拉什么屎。
“听说你有女朋友了,很快乐吧?”
韩有福腿打哆嗦了。极力装出笑容说:“我的朋友很多,男的女的都有!”
“不用害怕,你只要干活好,思想纯正,我不管闲事。”
“……”
“最近战局不大好啊!”巡查叹口气说,“塞班岛玉碎了东京轰炸了,美国飞机常常来!”
“先生,一意一心,圣战必胜!”韩有福一边说一边心里想:“你小子也有害怕的事呀,咱们心里有数吧!”
“对的,日本必胜,我们神风特攻队,一人一机就拼掉美国一艘军舰,美国的军舰有限,我们的武士无数。”
“我完全相信。”
“可是你们的人都相信吗?嗯?没有人说什么坏话吗?”
“没有听见。”
“你注意一点,报告给我,女朋友的事没关系。现在的工作太辛苦了,车间工具仓库需要人,我可以帮忙调你去。”
“我一定努力。”
韩有福心说,你又错打了主意,我老韩为人滑头点儿,可不至于出卖中国人,这点还能把握住。
韩有福回车间,货已卸完了,人们正推着车往过滤室去。他见车子都推过了出料口,没人看见他回来,就抓起自己上衣,急忙溜出车间往海边走,装湿料时,大家合装一台车,多一个人少一个人不容易发现,发现了可以说巡查找他谈话没谈完,乐得抓这个空子去海边打个盹。碰巧还能会一下花枝子。花枝子在海边小铁道上推轱辘马,每到上夜班就和他在那些废管子里幽会。韩有福别的方面机灵,可就是学不好日本话,除去生产上几句必须的话,别的都记不住。花枝子也并不想学中国话,“谈”恋爱这词对他们俩不适用,好在要满足人类天性的需要,谈与不谈并非关键所在。我们祖宗也不是先学会说话再延续后代的。所以到现在韩有福也不知道花枝子家住哪里,有几口人。他丈夫死在南洋群岛,还是死在阿留申。花枝子对他热得象一盆火,把头埋在他胸窝里哭,从牙缝里省下食物送给他。他只是觉得送上门的便宜不捡是傻瓜,她想男人想疯了,愿意倒贴,为什么不干呢。在华工中他不太隐讳这件事,有时候还故意讲他们的事来炫耀。华工们当面也说几句逗趣话:“走桃花运了!”“回国不回国你无所谓了,反正在日本有人疼!”背后不骂他的很少,觉着他给中国人丢了脸。甚至有人指着他鼻子说:“跟野妓一样,无非是翻个过儿罢了。”宋玉珂从不胡言乱语,有一次也正色说:“我替那个日本女人伤心。对你好了一场,你也该有点真心罢?怎么拿她的痴情当笑话说?”韩有福做买卖出身,什么下流地方都到过。听宋玉珂这议论暗暗发笑,觉得这实在是个穷书呆子的见识。
过滤室这时忙得天旋地转。因为一下出了两班的车,不能按常规那样生产了。只得三个人负责装一辆车,推进干燥炉。另三个人在他们进炉时就装另一台车。过滤器出料口要有两个人把料整理好推上皮带运输机,另一个往出料口上放置托板,可是韩有福不见了。不论怎么安排也少一个人手。大牙不敢停下工来去找韩有福,只好自己去放托板,没有干完一车活,他那条好腿既累得支撑不住全身、那条断腿又疼的他龇牙咧嘴,他就破口大骂,骂中国人都是混蛋,都是懒虫,都该杀。大家本已累得够呛,一听他骂全火了,七嘴八舌跟他吵。一吵手脚自然放慢,噼里啪啦几十板碳酸镁全从皮带运输机上滚了下来,堆成了堆。大牙气急,把机器停了,抄起锹把要打人,张巨原没参加吵骂,他心里也在骂韩有福泡蘑菇,见大牙要动武,张巨火了,顺手抄起一条铁管子,拦住大牙。
大牙平日虽也怵张巨一些,但量他不敢动手,举起棒子就朝张巨打来。张巨用铁管一挡,顺手一扫,打在大牙那条好腿上,大牙一下子就跌进水汪汪的碳酸镁堆里。村冈平日虽然中日不分,也恨大牙,现在到了节骨眼上,民族观念就占了上风,从张巨身后扑上去要夺他的铁管。华工们见他动手,吆呼一声就一齐拥了上去,七手八脚把村冈也打倒在地,虎子一看事闹大了,就跑到“石肖酸加里”去报告宋玉珂。听陆虎子上气不接下气的把事儿一说,硝酸加里的几个人不等宋玉珂发话,各拿了一把铁锹,直朝“碳酸镁”来。“硝酸加里”只有一个日本工人,是五十多岁的老头,平日沉默寡言,对华工们不冷不热,这时却抓住宋玉珂的手说:“宋,听我劝告,不要闹出大事来。”
宋玉珂握了一下老工人的手说:“谢谢你!”
宋玉珂赶到“碳酸镁”车间,战斗已经结束。大牙和村冈全被监视在休息室的墙角里。大牙躺在地上,已经只有**的份,满脸是血。村冈脸冲墙坐着,衬衣撕成了破片,一语不发。宋玉珂把张巨拉到一边小声问了几句。张巨连说带骂:“亡国奴当够了。一人作事一人当,决不连累你们,我索性杀了大牙,去自首去。”
宋玉珂说:“你有这份骨气,够条汉子。可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舍这条命。日本快完了,想法坚持到胜利回国这才是正路。大家听我一句话行不行?”
张巨向来胆大气粗,华工中没有他看得起的人,不知为什么跟宋玉珂往一块一站,心里就觉着矮半头。
张巨问:“你说怎么办?”
宋玉珂说:“先把村冈请出来。”
张巨叫人把村冈拉了出来,村冈气哼哼的把脸转向别处。宋玉珂向村冈说:“我劝架来晚了。很对不起。你一直跟我们挺友好,失手打了你,这是误会。张巨,向村冈先生陪个礼吧!”
张巨瞪眼冲宋玉珂喊道:“叫我来这一套?”
宋玉珂挤眼:“听兄弟一句吧!”
张巨冲老宋情面,一不作二不休,索性把上衣脱了下来,披在村冈身上了,大声说:“村冈先生,我跟你没过节,打失手了对不起,请原谅吧!这件衣服我赔你的衬衫。”
村冈还有些悻悻然,但勉强说了句:“真遗憾!”
宋玉珂对张巨说:“全体集合,上勤劳部自首去!”
张巨说:“要去,我一个人去,宁叫一人担……”
“都去!”宋玉珂说,“‘硝酸加里’的人也去,法不责众!”
在人们集合的时候,宋玉珂小声对虎子说:“给石灰炉、碳酸钠的人送个信,如此这般……”
药品部十五个人跑着整齐步子,来到勤劳部门外。山崎正被勤劳部召来开会。马上推门出来问:“正上班的时间,你们上这儿来干什么?”张巨说:“我们来请求处罚!”山崎问:“出了什么事?”
“我们跟大牙打架了!干活的时候,他欺人太甚,我们揍了他!”
山崎一听,火冒三丈,平时敢顶撞日本人一句都要惩罚,今天居然动手打起来了,就挤开中原,上前问道:“谁动手了?上前一步走!”
全体华工都向前迈了一步。
山崎更加暴跳如雷,进屋拿来一把木头战刀,大声问:
“那个先动的手,举起手来!”
全体华工都举了手!
山崎没料到会这样。一怒之下,想冲每人头上都打几木刀。谁料四下一阵跑步声。由碳酸钠、石灰炉、硅酸曹达……跑来了上百名华工。列队在勤劳部门口站定了。勤劳部长亲自出来,看看这气势,把山崎叫进屋去。然后就笑眯眯的问:“怎么档子事啊?”
各部的班长纷纷报告说:“我们按勤劳部的规定,有错误主动报告,请求处罚来了?”
“各位犯了什么错误?”
“征用工守则规定,要互相监视:药品部的人犯了错,我们有失监视之责。”
“很好,大家稍息。”他倒背手来回踱了几步又站住脚说,“有了错误自己来自首,这很好。既这样,我决定不处分你们了。”
“谢谢部长先生,以后也不处分吗?”
“现在前方战士,在浴血苦战。我们要努力生产,这些小事,不必太重视了,以后不重新闹事,当然就不处分了。各位回去劳动吧。”
华工们看已没什么再坚持的,就喊:“立正,敬礼”。队伍也各自走散了。
部长回到屋内,各车间正纷纷来电话请求把华工先放回去生产。机器还在运转,再没有人照看,马上要出事故。大家都恭维部长处理得十分及时和妥善。
部长点燃一支烟,深吸了几口,对全屋的人说:“最近,秋田县的华工发生暴动,把几个对他们太严厉的监管人员杀了。”他看了一眼山崎,山崎立刻立正站起来,他作个手势,让他坐下。
“华工们夺了警察所的枪,拉上山打了几天游击。想和美军俘虏营靠拢,幸好军队赶到才把他们消灭。”
众人齐声喊道:“万岁!”
“可是矿山生产停了!”勤劳部长把烟头扔进烟缸,搓搓手说:“发电取暖要烧煤,烧中国人的尸体是不顶事的。”
“是。”
“查一查,今天的事如果没有政治背景,放过去吧。要杀的是肉牛。耕田的牛农民不杀。山崎先生,希望你以后多听一点我们勤劳部的意见。”
山崎答应了一个“是”字。
部长又说:“山崎先生工作是很出色的,我们一向合作得很好,我们的目标没有差别。”山崎说:“我们劳工协会虽然派我来管理华工的生活,可部长是上级,我一定按您的指示办。”